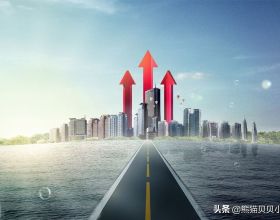高麗王朝國祚長達470餘年,同時期的中國經歷了從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到元明時期的大統一。在如此劇烈變動的時期,高麗王朝如何與中國進行交流自然是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但礙於史料的稀缺,實際研究成果卻並不豐富。其中13—14世紀高麗後期的歷史尤是如此。
高麗後期一直被冠以“元干涉期”之名,韓國貿易史和東亞貿易史相關論著都深受此觀點的束縛,這種刻板印象可能是此前該領域研究多少有些滯後的原因之一。韓國學者李康漢努力擺脫“元干涉期”傳統觀點的桎梏,重新審視該時期的脈絡,試圖帶我們走進一個更為真實,更為生動的高麗後期歷史場景。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13—14世紀高麗和元朝的貿易史》便是其觀點的精華輯錄。
《13—14世紀高麗和元朝的貿易史》
[韓] 李康漢 著
秦菲 李彬彬 譯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茫茫大海並非阻斷交流的屏障
而是貿易往來的通衢大道
內容推介:
高麗與元朝之間的海外貿易,在中文史料中記載較少。此書的最大價值就在於作者主要依據中韓歷史文獻詳細考證,還原元朝時期(包括忽必烈稱元前的蒙古汗國)與朝鮮半島高麗政權間的貿易實況,同時也對元朝時期的東(中國)西(西亞阿拉伯地區乃至歐洲)方之間貿易的盛況有所反映。
在鉤沉史料並另賦新解的基礎上,本書重新探討了高麗後期的海外貿易,從東西方貿易的宏觀格局下闡明元麗之間貿易的作用、貿易轉型狀況、元朝廷和高麗政權各自的政策如何促成元麗貿易的活躍和復興,最終達致長達七十餘年元麗官方和民間貿易交流的全盛時期。
隨著海外貿易愈發興盛,海商群體日益壯大,商人不僅積極開展對外貿易活動,還成為元朝和高麗在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往媒介,承擔著使臣往來、文書傳遞、文化交流等功能;與此同時,泉州也成為東亞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影響輻射到高麗、日本、東南亞和南亞。本書有助於拓寬我們對13-14世紀世紀東北亞貿易史、外交史的瞭解。
早在13世紀60年代前半期,高麗官員就開始作為隨行使臣前往元朝,並以個人名義從事對華貿易。高麗元宗四年(蒙古中統四年,1263年)十二月,朱英亮等官員收受他人賄賂後,私自將17名人員帶到蒙古,而這些人在蒙古境內進行大規模貿易。此事敗露後,高麗將這17名行賄者流放,並沒收170個銀瓶和700斤真絲(絲織物),還沒收朱英亮的個人物資。這一事件充分表明高麗對跟隨使臣團進入蒙古進行貿易的態度。
基於元朝方面的史料可知,在高麗官僚的對元貿易中,受到如此嚴厲處罰的並不少見。元朝頒佈“諸高麗使臣,所帶徒從,來則俱來,去則俱去,輒留中路郡邑買賣者,禁之 ;易馬出界者,禁之。” 等相關法令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當時遠道而來的高麗使臣及其隨行人員進入元朝後所從事的貿易,對中國的民間貿易有所影響。在當時使節規模不小的情況下,這一情況更加嚴重。高麗忠烈王四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高麗國王入元朝時,僅自身隨行人員裁減人數就已達190人左右,而忠烈王十年(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隨行人員的規模達到了1,200名。忠烈王十五年(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十一月,高麗國王、公主、世子一起前往元朝時,因想隨行且請功的人員居多,甚至無法確定隨行人員的規模。忠烈王二十二年(元元貞二年,1296年)九月,國王與公主一起前往元朝時,共帶有隨從官員143人、隨從僕人590人及990匹馬。不難猜測跟隨國王進入元朝的這種大規模使行團在元朝會從事怎樣的活動。
高麗使節團與中原王朝的貿易往來,主要是依託於官方間的便利交通來進行。這是民間層次無法實現,且是在非正常條件下所進行的貿易。真正的貿易應為從高麗派遣官營或者民營船隻,在到達元朝港口支付關稅後進入中國內地開展多種形式的貿易。在這種貿易方式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高麗國王忠烈王開始首次嘗試真正意義上的貿易。
元朝名儒姚燧的《牧庵集》對歷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和江浙行省右丞等官職的史耀(1256—1305年)的《神道碑文》有所記載。此碑文記載了忠烈王派遣的周侍郎為開展貿易,進入元朝港口的相關情況,內容如下:
高麗王遣周侍郎,浮海來商,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曰,“王於屬為福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 惟如令三十稅一。”
從史耀於元元貞元年(1295年)出任江浙行省右丞這一點可以得知,上述記載出現的時間應為元元貞元年(1295年)或之後的幾年內,但並沒有對該記載出現的背景有所介紹。其他史料對於史耀歷任地方官的地區也只是簡單記錄,並沒有明確指出是中國的哪一個港口和哪一個地區。
當時,元朝在杭州、上海、澉浦、溫州、慶元、廣州和泉州七個地區設定了市舶司。因此,筆者認為該記載的背景可能屬於上述地區的其中一個港口。但考慮到與泉州和廣州相比的記載,那這個地方應該是除泉州和廣州之外的其他五個地區,即杭州、上海、澉浦、溫州、慶元中的其中一個港口。但元朝於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將溫州的市舶司併入慶元港,並將杭州的市舶司也合併到稅務中,因此這篇記載的背景可縮小為上海、澉浦、慶元中的其中一個地區。此外,元朝於元貞二年(1296年)把澉浦和上海的市舶司併入慶元市舶提司,隸屬於中書省。基於上面論證可知,這一記載的背景應為慶元港。
換言之,這篇《神道碑文》記載了高麗忠烈王二十一年(元貞元年,1295年)左右,忠烈王向慶元港派遣官方貿易船,試圖進行某種政府層面的貿易。在《高麗史》或《元史》等正史對此卻少有記載,因此上述記載是非常珍貴的史料。
只是高麗國王要想與元朝進行官方貿易,首先需要解決中國港口的高關稅問題。自南宋時期以來,中國港口的高關稅已經固定化。如果不下調稅率的話,即使高麗派出官方貿易船也很難獲得預期收益。
但恰好這一史料顯示,當時元朝對高麗官營船的貨物徵收了相關關稅。更加有趣的是,高麗貿易船和元朝港口負責人之間存在著某種矛盾。
忠烈王是基於什麼樣的判斷,在這個時候派遣官方貿易船呢?如前所述,他想利用鷹坊推進對外貿易的企圖最終化為了泡影。對此,忠烈王改變戰略,開始嘗試其他方式的對外投資。但直到進入13世紀90年代中期,即江南港口關稅稅率比較合理的時候,忠烈王才發現與江南地區開展貿易能有利可圖。
那麼在此前後,以前的高關稅究竟降低了多少呢?元朝的對外貿易政策是怎樣的?
眾所周知,元朝於13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施行市舶行政。因為在南宋沒有附屬於蒙古的情況下,元朝無法利用泉州、福州、明州等江南主要海外貿易港口。在江南歸元朝統治後,元朝根據宋朝慣例開始從各個藩屬國商人那裡徵收財物1/10或1/15的關稅,即開始施行市舶行政。元朝於至元十四年(1277年)開始在泉州、慶元、上海、澉浦等地設定負責市舶行政的官廳—市舶司。至元二十 年(1283年)確定抽分法(關稅法)的同時,規定關稅稅率為1/10或1/15。因此前面《神道碑文》中所描述的軼事,從時間上看應為市舶政策調整後出現的事例。
但在《神道碑文》記載所發生的“是非”之前的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為了禁止商人的各種非法行為,制定了所謂的“市舶抽分雜禁”,這點備受矚目。雖然元朝出臺市舶政策已經過去了十餘年,但違背朝廷政策的做法仍然存在。換言之,行政層面的改革和過去的習慣做法並存。為了解釋以13世紀90年代中期為背景的這一軼事,有必要考慮到這一點。
前面記載中包含著各種事實,最引人注目的為“抽取3/10”(譯者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和“又取1/30”的部分(譯者注: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為稅)。為對這部分進行詳細地解釋,有必要弄清楚兩點。首先,要了解當時元朝的“官方關稅”(也叫抽分、抽解),即第一次關稅。其次,要了解帶有某種“船舶稅”(停泊手續費)概念性質的第二次關稅。
當時,元朝想積極吸引外來商人,因此在將關稅變合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例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外國商人(客船)帶著外國物品來到泉州和福州地區,將這些物品銷售之後來換取泉州和福州地區的土特產,然後前往上海,最終將泉州和福州的土特產賣給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元朝在向他們徵收關稅時要求他們不要選擇“番貨”,即作為外國商品課稅標準的“雙抽”方式, 而應選擇“土產物”,即作為中國商品課稅標準的“單抽”方式。元朝以減少外來客船在元朝境內交易的負擔來吸引更多外商。
元朝努力從政策和制度方面採取措施,讓關稅稅率合理化,從而促進更多外國船舶訪問元朝。如前面所述,元朝於至元二十年(1283年)和至元三十年(1293年)頒佈相關措施。至元二十年(1283年)規定市舶抽分的方法,並決定對海外物資中的精美物品和粗劣物品分別抽取1/10、1/15的[稅金]。至元三十年(1293年)頒佈了市舶抽分雜禁二十三條,提出減輕海外商船的關稅負擔,但如果私藏貨物,將對其進行嚴厲處罰等相關政策。考慮到南宋末期的關稅稅率原本就很高的情況,筆者認為至元二十年(1283年)所頒佈的措施在吸引商人方面產生了不小影響。與此同時,至元三十年(1293年)所頒佈的雜禁措施也有助於進一步推動關稅合理化。
作者簡介
李康漢,韓國首爾大學博士,師從韓國高麗史研究大家盧明鎬教授,研究方向為韓國高麗時代史。曾任仁荷大學BK21東亞韓國學事業團研究員、韓國曆史研究會編輯委員、韓國中世史學會企劃理事,現為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教授、海外韓國學振興事業財團團長。著有《13—14世紀高麗和元朝的貿易史》(2013年),《實學時代的歷史學研究》(合著,2015年)等,在韓國核心期刊《歷史與現實》《韓國史學報》《韓國中世史研究》等發表數十篇論文。
譯者簡介
秦菲,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博士,研究方向為中韓古代關係史、渤海史。
李彬彬,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博士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韓古代關係史、韓國近代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