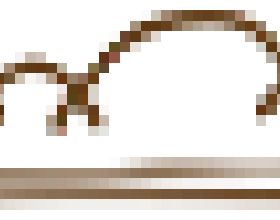在朝鮮戰場上,我軍對指揮權的歸屬是極為看重的,無論是朝方還是蘇方,一旦有染指我軍指揮權的行為,我方都會當場拒絕,這點主要體現在朝鮮戰爭爆發初期,以某金與彭總爭奪志願軍指揮權最為出名。根據“奪權失敗”後我軍在戰場上所獲得一連串勝利,我們當時的確應該慶幸當初未將指揮權交出,不然我們可能在付出極大代價的情況下,可能連獲勝的可能都沒有。而根據蘇聯軍事顧問科切爾金少將撰寫的戰後回憶錄所述,他當時無權干涉志願軍行動,即便是提出相關的軍事計劃,也被一一擱置。
他在回憶錄中表示,志願軍對其非常友好,會傾聽他對戰局的分析和相應的建議,但也僅僅到此。在作戰計劃的擬定階段,無論是蘇聯軍事顧問還是朝方在志司總部的代表,都無法插手。科切爾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還是在於志願軍指揮員對蘇朝雙方顧問及代表的指揮水平不放心,生怕他們將不適合志願軍作戰特點的要求強加給一線作戰部隊。在紅軍時期,共產國際曾指派一個名叫李德的德國人赴華工作。在掌握紅軍指揮權之後,李德便把自己在伏龍芝軍校學到的知識“紙上談兵”地復刻到實戰中。在他的指揮下,紅軍摒棄游擊戰思想,採用蘇式正規戰術,結果就是裝備遠遜於對手的紅軍一敗再敗並損失慘重。而當時在李德身邊工作的正是彭總,這才有了後來彭總在朝鮮堅決抵制蘇朝介入志願軍指揮的佳話。
如果拋開身份和中蘇兩國國力等諸多背景,單獨評價志願軍各級指揮員與蘇朝兩軍各級指揮員的水準,毫無疑問我們都是遙遙領先於他們的。以某金為例,他的指揮水平就算當個連排長都還不夠資格。志願軍剛剛入朝,彭總急於與他對接,交流戰場情況之時,他還在朝鮮北部,中朝邊界附近某個山洞內。對於人民軍所剩兵力,都部署在何地,武器配置及組成時,他都一概不知。而當彭總問及雙方目前態勢和敵軍所處位置時,他也是含糊其辭。萬般無奈之下,彭總只能命令志願軍各部充分利用聯合國軍還不知道志願軍入朝的有利時機,進行穿插滲透作戰。也正因為如此,入朝前期的戰鬥大多都是遭遇戰,然後在一個戰場方向對敵形成包圍,利用夜戰和近戰,敵軍航空兵和炮兵不敢實施攻擊的特點,打贏對方。
在志願軍部隊中,指揮才能強於科切爾金的非常多。我軍歷來的傳統就是戰場升遷,依照作戰表現和品德做出職位上的調整,這是西方國家軍隊中很少存在的。以美軍第八集團軍沃克中將為例,他從西點軍校畢業後就被任命為步兵少尉,參加短暫的墨西哥戰爭後,又去了錫爾堡炮兵學校,軍銜提為少校。在學術理論上,他可能要強於志願軍絕大多數師,軍一級軍官,但這並不能代表他的指揮水平要高於我軍師和軍一級指揮員。在第二次戰役中,他因為疲於跑路,司機駕車避讓不及障礙物,導致他死於車禍。在朝鮮戰爭中,沃克對麥克阿瑟的指令十分貫徹,但他犯了指揮官的大忌,那就是他對手下各部和各國軍隊的作戰能力,人員便稱和火力配置都不瞭解。在一陣又一陣的驚嚇中,他還是死在了朝鮮。
與之相比,我軍指戰員在作戰時,都一定會想方設法摸清前線戰況,就連身居高職的彭總也經常會抵近前線觀察雙方動向,然後做出決定。在每次戰鬥結束或休整時,我軍都會嚴格統計敵方傷亡數字和我方情況,然後逐層上報。憑藉手中所掌握的資訊,指揮部能夠快速判定我方所剩戰力及對方大致情況,這都是十分重要的。誠然,學術理論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戰場實戰經驗和指揮經驗,這恰恰是西方國家軍隊所匱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