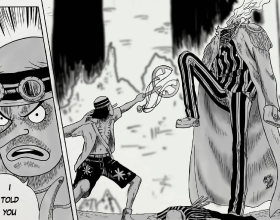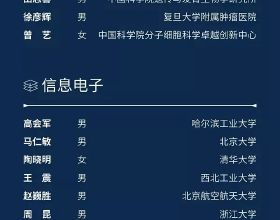文丨路西法爾
去年拿過不少獎的青年導演電影《一江春水》,正式登陸商業院線了,但是該怎樣向觀眾介紹這部影片,卻令媒體著實犯了難。
「女性犯罪電影」、「呼籲女性為自己而活」、「為了愛拼命地活著」……這些絞盡腦汁提煉出的標題和電影本身的關聯其實微乎其微,也從側面說明《一江春水》既不是一部型別片,其主題也不是我們尋常理解的那些口號般的道理。
在總長一百零四分鐘的影片裡,前八十多分鐘都在講述蓉姐與小東兩個相依為命的姐弟平凡而沉重的生活:蓉姐是洗腳城的技師,這所位於小縣城的小店如今生意日漸蕭條,而蓉姐還夢想著供她十九歲的弟弟念上大學。可是小東根本無心去上補習班,一天到晚和叛逆的戀人靜在一起廝混,不願意去想明天。
眼看著生意漸漸做不下去了,洗腳城的技師們開始各尋出路。與蓉姐交好的金花夢想著和自己中學時代暗戀的男同學修成正果,卻發現對方是一個玩弄女性的渣男。最終她嫁給了一個給自己洗腳的男人,儘管這是一段「不倫」的感情。
蓉姐一樣在為將來舉棋不定,洗腳城技師總不是一個可以做一輩子的工作。經常照拂她的田阿姨攛掇她和自己的兒子結婚,甚至許諾將房子留給她;洗腳城的老闆阿強也向她丟擲了橄欖枝,但她發現:這些對自己莫名殷勤的人都是別有所求。
蓉姐辭去了洗腳城的工作,小東令女友意外懷孕了,靜發覺小東並不是所託之人,拿了家裡兩千塊錢不辭而別。兩場變故疊加在一起,令小東漸漸走向成熟:他一邊學習燒菜做飯,一邊送快遞掙錢,他要去找靜。看到小東終於能夠自食其力,蓉姐決定去自首——原來她是一名逃犯,十九年前她失手「打死」了對自己始亂終棄的男人,逃到了遠離故鄉的南方。原來小東並不是她的弟弟,而是親生骨肉……
「一江春水」就是流動不息的生活本身,而生活和戲劇的區別就是有沒有顯明的主導意識。在影片中,導演高啟盛將演員和自身的存在感都降到了最低——每一個鏡頭開始時機位是很麼樣,到結束時機位還是什麼樣,從頭到尾攝影機的機位就沒有動過,鏡頭就像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將生活的原貌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而已。
而演員則竭力避免表演的痕跡,據說在正式開機之前,導演和兩位主演共同生活了幾個月,每個月只給一千元生活費,讓他們逐步進入角色的生活狀態。艱苦地揣摩人物的確有了回報:女主角李妍錫以其酷似《小偷家族》中安藤櫻一般的「零度表演」,在影展上收穫無數讚美。無論是專業評委還是場外觀眾,都覺得她就是蓉姐本人——那個在小縣城隨處可見的,靠著微薄的收入,獨力拉扯著兒子的中年女性。
她不是金光閃閃的女強人,也沒有凌空高蹈的女權理論,蓉姐的強大之處在於對沉重的生活她已經習以為常,她是女性群體「沉默的大多數」的形象。而即使是賢妻良母,也有隱藏在心底深處的慾望——「巧兒我自幼兒許配趙家,我和柱兒不認識我怎能嫁他呀,我的爹在區上已經把親退呀,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蓉姐在片中不時哼唱的《劉巧兒》唱段即是蓉姐的心聲。
如果說這部誕生於於五十年代的評劇有什麼打動了蓉姐這個「八零後」,那就是劉巧兒追求自主的形象尋喚了她。這一過程是無法用「獨立女性」或「為愛拼搏」之類的流行觀念來包裝的,正如劉巧兒和蓉姐的追求也不能完全畫等號,在精神深處驅動蓉姐的是比意識形態更加深沉的東西。
更巧妙的是飾演蓉姐的李妍錫與飾演小東的祝康笠兩位演員之間的化學反應:兩個人的真正關係是母子,卻以姐弟相稱。以姐弟而言,二人的關係未免過度親密,蓉姐對小東的生活大包大攬,也造成了小東精神上的晚熟——如果說這是同居的戀人關係反而更加健康,但二人偏偏有著血緣關係。兩位演員將這種既非姊弟亦非母子的倒錯關係演繹得不著痕跡,直到最後真相大白時才有了水到渠成的感覺。
然而影片結尾處的連續超級反轉也正是全片最大的爭議所在。它是一個歐·亨利式的結尾——蓉姐以為自己殺了人,在逃十九年,當她終於下定決心自首時,才知道當年自己所「殺」的人並沒有死。或許是出於愧疚,對方不想再追究陳年舊事,因此警方對蓉姐不予立案。
一方面,這個從未登場卻直接影響了蓉姐一生的男人放大了影片中的女性生存境遇問題,是對主題的深化;另一方面,連續兩個戲劇感極強反轉也強行打斷了全片娓娓道來的紀實主義風格,將編導存在的痕跡暴露無遺,而這本是影片的大部分時間裡所竭力隱藏的。
自相矛盾的是,高啟盛導演越是試圖抹消鏡頭和表演存在的痕跡,導演本身的存在感就越明顯。1.33:1的畫幅、一動不動的機位,反而成為了貫穿全片的個性簽名,觀眾無法不注意到注意——這是一位對於原生態有著近乎清規戒律般執著的導演。加上前文所提到的,全片唯一的「配樂」全部出自蓉姐自己的哼唱,這不能不讓人聯想起電影史上著名的「道格瑪95」運動。
這場在1995年由拉斯·馮·提爾和托馬斯·凡提伯格所發起的電影原教旨主義運動排斥過度人工雕琢的痕跡,為了使電影更加「純粹」,二人制定了十條帶有清教徒意味的「童貞誓言」,遵守這些飾演拍攝出的作品會被冠以「道格瑪1」、「道格瑪2」、「道格瑪3」……的編號。「不可以使用配樂,如果一定要出現音樂,音源必須出現在攝影場景裡」正是十條誓言中的一條。
細數下來,除了「導演不可以署名」和「必須採用手持攝影」之外,《一江春水》完全符合「道格瑪95」的追求。雖然高啟盛導演說自己是是枝裕和的崇拜者,但他在美學上的追求其實更貼近早期的拉斯·馮·提爾。
「童貞誓言」已經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連規則的制定者拉斯·馮·提爾自己也沒有做到。在拍攝編號「道格瑪1」的《家宴》時,拉斯拉住了窗戶,使用了電影打光,違背了「不能使用特殊燈光」的誓言。到2005年時,已經千瘡百孔的道格瑪95運動煙消雲散,而拉斯也在最新作品《此房是我造》裡玩起了CG特效並把「不可謀殺」的誓言扔到了波羅的海里。
同樣,在《一江春水》裡,觀眾們能感受到導演的紀實主義美學和戲劇衝動不時地發生碰撞:除了影片結尾的超級反轉,最典型的就是靜突然意外懷孕和離家出走,同樣的情節在型別化的青春片裡已經屢見不鮮,二者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儘管導演對於現實有著強烈的渴望,但被攝入鏡頭的現實無論如何不能擺脫導演的主觀印記。也許這說明了:戲劇並不是現實的反面,戲劇只是人類理解現實、結構現實的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