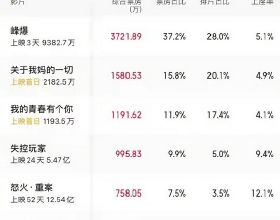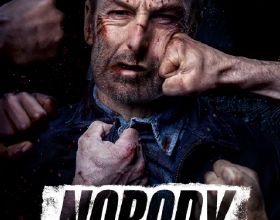遊戲中的一個路人角色(NPC)產生了自我意識,從一個被輕視的小人物逆襲成拯救所有人的英雄,但最後,他還是要留在遊戲中,賽博世界裡的他祝福深愛的女孩在現實中和好朋友“多年友情成愛情”。電影《失控玩家》的結局保守嗎?是的。可整部電影不就是保守主義框架裡的一則童話嗎?它有點新,有點舊,是新酒兌陳釀的一杯雞尾酒。
電影的本分:它不是遊戲,也無法成為遊戲
在各種從遊戲改編或以遊戲為主題的電影裡,電影是很焦慮的,它試圖接入遊戲的世界,然而屢戰屢敗。 《失控玩家》的妙處在於它接納“守舊”作為“翻新”的前提——電影不是遊戲,也無法成為遊戲,但電影可以用電影的方式講“遊戲”這件事。
遊戲產業和社交網路的發展,讓電影進入迭代焦慮。遊戲和網際網路的結合,製造了一個和現實生活平行的線上世界,那是由資料和程式碼組成的虛擬社會。玩家和觀眾是快感不相通的兩個群體。遊戲帶來的快樂在於強調參與感的技能學習和闖關模式,這是虛構故事的情感代入機制無法替代的。電影只能提供給觀眾“想象自己代入”的世界,但觀看的行為無法和虛構的世界產生互動。
並且,真人電影裡虛構的世界有著堅實的物理質感,這和遊戲的視覺風格無法相容。《魔獸世界》《生化危機》《古墓麗影》和《刺客信條》這類直接改編自遊戲的電影,反覆地栽在同一個難題:用電影這種實在的媒介再現資料的虛擬世界,無法繞開虛實之間的悖論。《頭號玩家》部分地緩和了電影和遊戲兩種視覺風格的衝突,導演斯皮爾伯格的應對之道是用碎片化、拼貼式的畫面和剪輯呈現故事裡的現實世界,這種視覺表達和遊戲裡玩家的主觀視角是一致的,碎片的景觀模糊了現實和虛擬的裂痕。
“無視電影和遊戲的視覺裂痕”,或“遮掩電影和遊戲的視覺悖論”,以及,玩家的快樂無法在放映廳裡實現,這種種成為電影在面對遊戲題材時,不能承受的包袱之重,指向一個讓電影人沮喪的結論:讓電影合併遊戲的“迭代”是不可能實現的。

《失控玩家》甩掉“電影更新換代”的包袱,用保守主義的策略面對“遊戲人生”的新命題,它本分地做一部傳統的視覺大片,情境和語境是新的,劇作和視聽的技法是基於傳統的改良。電影開場,男主角“蓋伊”本來是遊戲裡按部就班的小職員,只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玩家女主角“米莉”一眼,命運的齒輪就此轉動。蓋伊對米莉的“看”,電影用直白的剪輯暴露男人的主觀視角,他只能看到米莉的S形身材曲線——這是男性本位對“男性凝視”的調侃,也是某種程度對好萊塢時髦的各種“正確”的挑釁,簡直可以聽到男性主創的心聲:老派有老派的侷限,可我們就是挺傳統的。
“一串游戲中的原始碼成為擁有自我意識的角色”,這個戲劇框架在互聯網遊戲的背景板中展開了經典好萊塢最拿手的“男孩成長故事”:自我覺醒,自我超越,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千穿萬穿,套路不穿。但是不同於電影《刺客信條》和《頭號玩家》,作為“失控玩家”的蓋伊,他不是從現實世界接入遊戲世界,他本來就是遊戲裡的人,同時,故事裡存在著一群“真實世界的玩家”旁觀著這個失控的互聯網遊戲。這種平行視角、平行結構的改良款劇作思路,巧妙地迴避了真人電影和遊戲質感的不協調,它利用遊戲角色、玩家和全知視角的變化,從容地展開多重視覺表達,玩家所在的生活世界、玩家看到的遊戲世界、與遊戲角色自以為身處的“真實世界”,交錯的視覺風格工整地對應“虛構”和“虛擬”兩個世界。創作者這種保守主義的以退為進,其實讓觀眾鬆了口氣:總算,電影就是電影,不用假裝在電影院裡打遊戲。
遊戲對現實的救贖,老調重彈的成人童話
《失控玩家》是一部可愛的電影,主要在於創作者的“性別自覺”。他們沒有與時俱進卻自不量力地代入女性視角塑造大女主,事實上,女主角“米莉”在遊戲內外集合了各種青春期男孩對“女神”“女學霸”的刻板想象,然而有趣的是,男編劇和男導演從男性立場表達了某種幼稚卻真誠的懺悔。
《失控玩家》是意譯的片名,直譯過來,應該是“自由的蓋伊”。蓋伊原本是一堆遊戲裡的程式碼,羞澀的程式設計師創造了他,用0和1的位元組,把自己多年的單相思和暗戀女孩的特點藏進一個遊戲裡的小人物。他本來是個閉環的小程式:在遊戲中每天醒來,穿同一件藍襯衫,去銀行上班,喝同樣的咖啡,經歷迴圈的銀行劫案,也許會被玩家殺死,但第二天又在自己的床上醒來……直到有一天,玩家“米莉”——也就是程式設計師思慕的愛人——看了蓋伊一眼,愛人的“看”激活了蓋伊,他成了能自我學習和不斷升級的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擁有自我意識”“和人工智慧談戀愛”,這些看起來很有Z世代特色的主題,指向古老的“皮格馬利翁”的故事,皮格馬利翁深愛著自己創造的象牙少女,直到有一天,他的凝視讓少女活起來。“自由的蓋伊”是對這個男性凝視傳說的性別翻轉版本,蓋伊就是那個象牙少女。

由男性說出“因為女性的注視而覺醒”,這是很溫柔的童話了。《失控玩家》的特點和弱點都在這裡,與其指責它“終究保守的敘事走向”,不如說,它自始至終是隔著溫柔濾鏡的“天真男孩懺悔童話”,敘事及其構建世界的“當代感”,被古典主義的“情感安撫”給消解了。對比《阿凡達》和《飢餓遊戲》,就能理解《失控玩家》的功虧一簣。在《阿凡達》裡,主角即便接入另一個世界,還是要面對自由和枷鎖的衝突。在《飢餓遊戲》裡,主角意識到,“虛擬中表演的愛情”和“真實生活的愛情”是不能相容的。
這些作品正面強攻了一個苦澀的議題:遊戲/虛擬的世界中不存在人類精神生活的避風港。《失控玩家》恰恰是在迴避這點,現實無能為力的,遊戲可以克服,進一步,遊戲救贖了現實,最終,現實和遊戲雙雙創造命運的童話。於是,圍繞著“資本對人性的掠奪”“社會達爾文主義”等西方社會的困境議題,歸於淺白的低幼童話:如果人類(主要是男孩)能重回童年階段,放棄打打殺殺的遊戲,改玩心平氣和養成系的過家家,世界會變成更好的人間。
問題是,觀眾信嗎?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