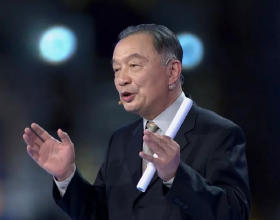晉懷公聽說秦穆公率軍來犯,發兵前去抵禦秦軍。但,此時晉軍之中已經人人皆知秦軍此來,乃是送公子重耳回國,人心所向不知什麼時候起都倒向了重耳一邊——晉國內部,只剩當年扶立晉惠公的呂甥、郄芮他們這一夥人不希望重耳回來——可以這麼說,重耳雖然還沒有回晉國主政,便已基本贏得了晉國大部分的人心。
就在這時,突然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說是小插曲,其實也相當不小。當護送重耳回晉國的隊伍來到黃河邊上時,一直以來跟在重耳身邊的狐偃,突然從身上掏出一塊玉璧交給重耳,對重耳說——自從當年我追隨君上“巡行天下”以來,我對君上犯下的罪過可就多了,這些事我都還記得,更何況君上你呢?現在君上有了秦穆公的支援,我就在這兒向君上請辭,從此咱們一別兩寬吧。
這個情節非常有意思。狐偃是重耳的舅舅,兩個人是甥舅關係,但比起這層親戚關係來,兩個人首先是君臣。從前,重耳帶著他流亡,他們君臣甥舅之間,要相依為命,所以大多時候親戚關係可能會更重些,狐偃和重耳說話交往時,不拘小節的時候也多些。比如前面我們提到的狐偃逆重耳的意願,把重耳灌醉了,從齊國直接拉走,重耳酒醒後生氣要殺了他、要吃了他的肉時,狐偃嬉皮笑臉地和重耳周旋,還說自己的肉又腥又臊不好吃,彼時二人相處時相對來說是比較平等、輕鬆的,但現在一切都不同了,有了秦穆公的支援,人人心裡都明白,晉國國君重耳是當定了。所以,在還沒有過河回到晉國之前,狐偃就開始給重耳打預防針了。不過狐偃這個預防針,可不是他真的怕重耳有朝一日即位為君,對他打擊報復。要知道,他追隨重耳在外十九年了,十九年來對重耳不離不棄,卻在眼看就要成功卻還沒成功時,說要離開——所謂功成身退,他這功還沒成就嚷著要退,這顯然不符合人之常情。所以,我們需要正確認識狐偃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對重耳說這樣的一番話。
這裡有一個細節非常值得注意,狐偃對重耳過去一直是以“子”相稱的,同時他自稱為“犯”(狐偃,字子犯)——“子”也就是“你”,是不昭示身份地位的一個稱呼,但此刻,當狐偃掏出玉璧交給重耳時,他對重耳的的稱呼突然就改為“君”,對自己的稱謂也直接降為了“臣”。這個改變背後,固然是時勢的不同造成的,但也能從中看出,狐偃對自己的身份認定很清醒,他瞬間將自己的身份從舅臣直接轉變成純臣。從前他和重耳之間更多的時候,是先論甥舅再論君臣的,親戚嘛,尤其他還是長輩,那怎麼都好說;可現在他主動遮蔽掉和重耳的這層親戚關係,這其中就有學問了。什麼學問呢?有些話我們作為讀者、外人,單純從史書中留下的文字本身,是看不出蹊蹺來的,尤其是史書只給我們留下這一言半語——我們完全可以僅憑這一句話進行解讀,認為狐偃他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確,表現出一個成熟的政治人物應有的政治清醒,並且他也要藉此考察一下,自己多年來輔佐的這個外甥得勢之後,還能不能繼續輔佐下去,畢竟有些人得志前和得志後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一旦眼前之人得志後睚眥必報,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我們再仔細看看重耳聽了狐偃的話後,是怎麼回覆他的,就能猜想到,當時當地,兩人之間當是湧動著一股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詭異的氣氛。因為聽了狐偃的話後,重耳立刻指著河水發誓說——河神在上,如果我回到晉國後不和舅舅你一條心,就有如此水!說完,重耳就把狐偃剛剛交到他手中的玉璧投入了河中。
有人問為啥重耳要把玉璧扔進河中,因為古人起誓、祭神,都要向神祭奠犧牲、玉帛,祭祀儀式的最後,便是將這些祭神的東西都掩埋起來,有時也會投入祭祀起誓的河水之中。重耳指河水向河神發誓,手邊只有狐偃給他的玉璧,沒有現成的祭祀用牲口,所以自然要將玉璧投入河水中,以示自己所發之誓之鄭重。這是什麼操作?這等於重耳和他的舅舅狐偃之間定了一個盟誓,因為彼時並不是在祭神,那就只能看作是會盟了,因為會盟也要有這樣的儀式。甥舅之間、君臣之間突然要定盟,你說詭異不詭異?而且重耳還特意向狐偃保證,自己必不會辜負了他,這種試探如果是夫妻、情侶、兄弟之間也就罷了,可他們是君臣。
因此,在一旁看到這一切的介子推,雖然人已經上了船,突然冷笑著開了口,他說——是上天選中了公子,可狐偃卻認為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功勞,竟然還和君上作交易,真是沒皮沒臉不知羞臊,我真是不想和這樣的人同列為臣。說完介子推甩開了眾人,自行渡河而去。
這裡交代一下介子推的去向。
介子推離開重耳後,羞憤之情始終未減,因此當他回到家見到自己的母親後,忍不住對他的母親說——(晉)獻公當年有九個兒子,如今就只剩下公子重耳一人了;惠公、懷公不親民和人,所以無論晉國內外,全都背棄了他們,但是上天不會斷絕晉國祭祀的香火的,一定還會給晉國指定新主,讓他來主持晉國的祭祀,這個人除了公子重耳,還會有誰?所以,是上天選中了公子重耳,可有些人(狐偃)卻以為這一切都是他的功勞,不是很顛倒是非嗎?介子推越說越氣,他慷慨激昂地對自己的老孃說,偷人錢財者尚且被稱作盜賊,更何況貪天之功的人呢?可是沒想到在下位者竟然用道義來粉飾他的罪過,而君上竟然也對這種奸惡的行為進行獎賞,上下如此互相矇蔽,他真是難和這些人再相處下去了!
聽了介子推的這番牢騷,他的母親開解他說道——你這嘮嘮叨叨的,是懟誰呢?怨誰呢?你要是不滿,何不也和他們一樣,向君上求取功名富貴呢?
聽到自己的娘竟然這樣說,介子推硬氣地對他的老孃說——我已經認定他們是不對的,卻又去學他們向君上討要功名利祿,那這罪過可就更加一等了,我也就是和你說說,出出怨氣,從此以後我是絕對不會再吃他的俸祿了!
聽介子推這麼說,他娘說道——你光在家裡和我說有什麼用?你去和他們說啊!既然你是這麼想的,你得說了人家才知道啊!不然你想怎麼樣呢?
說?那是不可能的。介子推說——一個人所說的話,便有如這個人身體的花紋,如今我的身體都要退隱了,還哪裡用得著再多此一舉、給他加上花紋?介子推斷然說道——如果我這麼做,就是在求顯達。
介子推的母親聽兒子的意思,是想不告而別,就問道——你說的話,自己保證能做到嗎?如果你能說到做到,我就和你一起去隱居。
介子推是八王吃秤砣——鐵了心了,於是便帶著他的母親,兩人徹底告別過去的一切,退隱而去。
相信有很多人是理解不了介子推的做法的——就算狐偃和重耳邀功,其實也不關他的事,就算錯的是狐偃,甚至包括縱容狐偃的重耳,這又對他有什麼損失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他孃的想法,如果他不滿,大可以像狐偃一樣,也去向重耳邀功嘛,畢竟這十八九年來,狐偃對重耳不離不棄,他介子推又何嘗不是如此!可是,介子推偏要做個怪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狂狷”的“狷”——有所不為。是非對錯,他有一套自己的判斷標準,一旦越線就是碰觸了他的底線,他便萬萬不能妥協。這種精神其實是有悖日常中國人所說的隨和,也就是願意和光同塵的圓滑處世哲學的。可是,這也是中國自古以來一直都存在的另一種更高潔的品格——追求道德的完美、人格的獨立。說得更接地氣點,就是看重大節,在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含糊。所以,我看才能看到介子推見到狐偃的所作所為後便覺得不齒與之同列。這就像《後漢書》中所說的“志士不飲盜泉之水”,《高士傳》中聽說堯要把帝位傳給自己就要去河邊洗耳朵的許由,《世說新語》中不屑與拾金觀車的華歆割席的管寧……古往今來,世上的絕大多數人既沒有這個覺悟,也更做不到像他們這樣立於天地之間。但千百年來,這些故事一直流傳了下來,又證明中國人其實是認可他們的做法的,只不過是高高掛起,做為展覽的那種認可。現實生活中,確實有極少數的人,像他們一樣孤高傲世,但孤高傲世不符合入世的儒家哲學的人生觀態度,所以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取用這種人生態度來指導自己的人生的——除非人生就喜歡碰跟頭,或者像介子推一樣乾脆出世歸隱起來,與俗世紅塵決絕地說再也不見。
上面介子推這段是個插曲,我們言歸正傳,接著說重耳他們回晉國爭位奪權的正篇內容。
大軍渡河,其後一路所向披靡,先圍令狐,再入桑泉,復取臼衰——晉國國內早就倒向了重耳,所以重耳所到之處,根本未遇任何抵抗,紛紛向他投降。
訊息傳到絳城,晉懷公心中十分忐忑,他一面派人率軍去廬柳迎擊重耳,一面出逃到高梁,等待戰爭的結果。
秦穆公派公子子顯(縶)前往晉軍,與晉國出征的大夫商討和平演變事宜。在公子子顯的居間勸說下,事成了,晉軍後退至郇地駐紮。幾天後,狐偃與秦、晉兩軍的大夫便在郇地定下盟誓——晉軍陣前反水徹底歸降了重耳。這幾乎就是塵埃落定的意思,所以第二天,重耳便親自來到郇地檢閱駐紮在此的晉軍。再四天後,重耳一行終於來到了曲沃。
曲沃是當年晉武公的發跡之地,也是整個曲沃桓叔一族的根據地,因此,晉武公死後,他的宗廟——武宮便建在這裡,其後每一代晉國國君即位時,一定都會來武宮朝拜他。所以,來到曲沃後第二天,重耳便去武宮祭拜晉武公,正式即位,是為晉文公——此時距晉文公當年出逃狄國,已經整整十九年過去了。
好了,說到這兒就又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了——重耳現如今多大年紀了?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說法,重耳回到晉國時已經62歲了,出亡19年,則他當年從蒲城離開晉國時是43歲。但是《國語》和《左傳》中卻說,重耳去狄國時,只有17歲,則他回到晉國時的年齡應該是36歲。這兩個年齡跨度實在是太大了,到底要信哪一個呢?
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重耳逃離晉國時,年紀不大。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重耳當年走的時候已經43歲了, 那麼他在晉國時肯定早已成家立業,則當有子嗣,可是無論是《史記》還是《春秋》《左傳》《國語》,重耳結婚生子都是在他逃離晉國後。但如果他是在17歲出逃的,去了狄國後,也到成家的年齡了,所以狄國國君送了他叔隗、季隗兩姐妹。我們知道,重耳在狄國待了12年,如果他從晉國出逃時已經43歲了,則當他決定離開狄國時,應該已經55歲了,一個55歲的老人幾乎已經沒有理由再讓季隗等他25年了——25年後,他如果還活著,都80歲了,那個時代活到70歲都不容易,重耳沒有理由對自己的壽命那麼有自信吧!並且,如果重耳離開狄國時已經55歲了,路上耗費的時間都不算,其後他又在齊國待了5年,則重耳已經60歲了,齊桓公當年給他在齊國安家,將姜氏嫁給他,老夫少妻,不可能感情好到哪裡去。相反,重耳如果當年離開晉國時是17歲,那麼,他和季隗的25年之約,和姜氏的感情也就都能說得通了。
因此,我個人認為,重耳回到晉國時,應該是36歲,而不62歲。
我們再做一個預告,晉文公即位後,只幹了9年,就去逝了。所以他大概應該是死於年富力強的45歲,而不風燭殘年的71歲。在未來的九年裡,晉文公要帶領晉國,走上顛峰,為晉國在接下來的整個春秋時代,幾乎一直居於諸侯的主導地位奠定強大的基礎,想想這是一件多麼厲害的事!
說遠了,雖然離晉文公之死還有九年,但無事則短、有事則長,晉文公即位後事多了去了,所以離九年後,還有很長時間呢。讓我們還是先看看他即位後都做了什麼吧。
首先,晉文公即位後,便派人去高梁殺了晉懷公——晉文公即位之時,晉國群臣都去曲沃參加了他的即位儀式,晉懷公已眾叛親離,所以殺他已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
但是,晉懷公死後,一直擁護晉懷公的呂甥、郄芮卻開始擔心自己之前沒有擁立晉文公,晉文公殺了晉懷公後,接下來就要收拾他們倆了。所謂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於是這倆人就和他們的黨羽聚謀,想要一把火燒了晉文公的宮殿,然後趁機殺了晉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