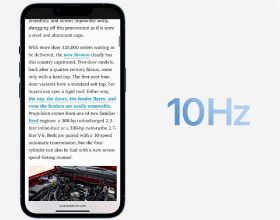“又是一個春光爛漫的季節,蔣緯國去蘇州留園觀賞明媚的春色。他一路走馬觀花,匆匆而行。在一條幽靜的小徑上,一位妙齡女郎在低頭獨行,兩人不期而遇,無意中撞個滿懷。”
青年女郎端坐在椅子上,當她讀到這一段時,視線偷偷向一旁瞥去,只看到那唯一的聽眾,一位老人面帶笑容,似是沉浸其中。
她心神稍緩,把視線拉回到眼前的書中,繼續聲情並茂地讀了下去:
“當兩目交流時,各人身上掛的都是東吳大學的校徽,原來是大學同窗。愛情總是有傳奇色彩的……”
真是美好的相遇啊!女郎心中如此感嘆。
但不待她繼續讀下去,一旁聽著的老人早已忍俊不禁,打斷了她:“哪有這樣的浪漫。初次相逢是在東吳大學生物系主辦的生物標本展覽會上。”
這?女郎尷尬地笑了笑,她與老人繼續讀了書中的內容。
好在剩下的時間,老人都很安靜,雖然女郎中間觀察到她幾次張口,但很快又恢復平靜。直到她讀出這一段話:
“施利聆小姐因一次患病,撒手西歸,留下一個兒子,這孩子也未歸宗姓蔣而姓了施。命運似乎對蔣緯國不公,他又一次品嚐了愛的苦果。”
空氣瞬間沉默,老人在經歷短暫驚詫後,身上是止不住的怒火,而女郎則縮在一旁,縮小存在感,不敢說話。
“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嗎?他們竟這樣不負責任地造謠!”
老人,也就施利聆滿腔憤懣。她不住地在房間裡來回渡步,又停不下自己的埋怨和嘮叨。
自己還活得好好的,怎麼就被這些作者傳成自己早已死去,這可讓遠在另一個城市的蔣緯國的如何作想,會不會他以為自己沒了,就不再想自己了。
不可!施利聆當即抓住躲在一旁的女郎,“我要上訴!”
一紙訴狀,她把《蔣氏家族秘史》一書的4位作者與印刷此書的出版社告上法庭,至此,一樁已被時光掩埋近50年的戀情被挖掘了出來。
而身處輿論中心的女主人公,蔣介石二兒蔣緯國的初戀面對採訪,聲淚俱下,自己一直在等蔣緯國,等了近60年。
為何他還不來兌現諾言?外界這樣造謠他們的往事,他為何還不來指正?
相遇
施利聆是有一樁美好婚姻在的,英俊疼寵她的丈夫,機敏聰慧的幼兒,她自己也是一位風華絕代的佳人,整日混跡在各類太太牌桌,十分得意。
但這一切,都被蔣緯國毀了。
有時候,施利聆也懷疑自己當初的決定。
她是著名“梅黨”首領、國民政府的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的小姨子,這一個認真負責的男子一力承擔了施利聆與其母親的所有生活開銷。
因姐夫的關係,她自幼接受的就是極為豪奢的生活,見識的也是形形色色的演藝人,她與孟小冬同住在一起,與梅蘭芳也有過交集。
因自己容顏嬌俏、身姿婀娜,學起戲劇來也是一日千里,純真良善的性格與美麗的容顏,讓她始終是學校,甚至是蘇州城內有名的嬌小姐。
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女孩,自然也是千嬌百寵,很是任性。
19歲那一年,她受邀去一所中學義演,就在這次義演舞臺上,被另一個少年郎看上。
這個少年家境富裕,自家有多處工廠,還有在上海都很有名氣的染料店。家世相當,男子自己也很爭氣。
他是有名的短跑運動健將程金冠,自小在速度上就已展現出遠超他人的天賦,早在遇到施利聆之前,就已參加過一屆遠東運動會(亞運會前身)。
“北劉南程”(東北劉長春)中的“南程”指的就是他。
這樣一個傲氣的帥小夥,一看到那在戲臺上“咿咿呀呀”的纖細身影、漂亮容顏,就丟了心。
於是,經歷好一番追逐,程金冠終於抱得美人歸。
沒兩年,他們就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婚禮極度豪奢,賓客如雲,一時間,轟動整個上海。
婚後的日子幾乎和婚前沒什麼區別,施利聆依舊享有著婚前的奢華生活,只不過多了丈夫的寵愛,多了更多與名流接觸的機會。
就連她的牌友,都是貴州省主席的妻子、外交部長的妻子那般的人物。
沒有煩心事,生活得意,自然容光煥發。這樣耀眼的她,自然而然被另一個男子盯上了。
一次,施利聆與丈夫去參觀一處展覽,就在閒逛過程中,施利聆察覺到一絲不對,怎麼總是感覺有人在偷偷在看自己。
她猛然回頭時,還能看到另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著急忙慌低頭、躲避的姿態,這不由讓施利聆皺了眉頭。
她湊近丈夫,趴到他耳旁,悄聲道:“後面有人跟著我們,你看是誰?”
程金冠回頭望了望,不以為然:“那是蔣建鎬(蔣緯國的乳名),是我同學。”
說到這裡,他起了八卦欲,又神秘兮兮地告訴妻子:“他就是蔣家二公子!”
“哪一個蔣家?”
“看你,就是蔣介石嘛!”
隨著丈夫的調笑,這件事情也就到此為止,施利聆也把那個奇怪的男子拋之腦後。
又過了一段時間,施利聆在游泳池中又碰到那位蔣家二公子,蔣緯國向她所在的方向潑起一個很大的水花,但是隻引來施利聆奇怪一瞥。
他們仍是沒有說話。
諾言
襄王有意,神女無心。
縱蔣緯國有再多的花花心思,面對著一個對他毫不在意的女子,也不由得傷透了腦筋。
還是他的養母姚冶誠,看出來了這個青年的心思,她稍作打聽,就能把整個事件還原得差不多。
兒子竟然看上了有夫之婦?姚冶城蹙了眉頭,但是一想起一向乖巧的兒子,難得這麼在意一個女子,她就把顧慮拋下。
於是,作為蔣介石的姨太太,她“屈尊紆貴”現身當地一個60歲老人的壽宴上,並在這場壽宴上遇上了施利聆。
初見這位太太,施利聆就在姚冶城的熱情招呼中不知所措。
宴席結束沒幾天,姚冶城就派人來邀請施利聆,說是自己攢了個牌局,還缺一個人。
正好閒適在家的施利聆興奮地坐上了姚冶城派來的車,天真的她滿臉笑容,只當自己又能結識一位權貴夫人。
但是,極為湊巧的是,每次她去蔣公館時,蔣緯國也在,即使暫時沒在,也會匆匆從外頭趕回家。
有僕人走到施利聆身旁,小聲提醒:“四小姐,少爺請你過去。”
少爺自然指的是蔣緯國,而一旁的姚冶城也滿臉曖昧:“去!有人來代你,保證不會輸。”
講罷,她就把施利聆“趕”到蔣緯國身旁。
施利聆滿心忐忑,她緩緩渡步到蔣緯國所在的房間,只看到早已等待著的男子。
出乎她的意料,蔣緯國沒有直接給她表明心意,而是和她談論詩賦,談論戲曲,儼然一副“只要看到你就很欣喜”的模樣,這不由得讓施利聆對他好感見漲。
有時候,姚冶城會約施利聆去看電影,與她們同行的不出意料,也有蔣緯國在。
在電影院中,姚冶城會貼心地坐到一旁,留下施利聆不得不與蔣緯國坐在一起。
正是在這種日復一日的“助攻”中,施利聆淪陷了,她感覺自己又重新有了愛情。
但是,有夫之婦與蔣家公子的戀情,註定不能為外人道也。
任由兩人情愫再多,還是不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施利聆要想和蔣緯國見面,還是必須要透過姚冶城。
於是,幾乎每天,施利聆都會藉口受姚冶城牌局邀請離開家門,從上午十點到晚上十點,她留在蔣公館中,成為蔣緯國的私有物。
時間久了,這兩人之間的事情也被一些人看出苗頭,包括蔣緯國和施利聆丈夫程金冠所在的東吳大學師生們。
唯獨程金冠自己被瞞著。
1936年,世界第11屆奧運會舉行,程金冠憑著優異成績順利取得奧運通行證,但是受制於時局動盪,奧運比賽一事並不被政府看在眼中。
程金冠空有一顆為國爭光的心,卻苦於沒有條件,連去參賽都成一件奢望。
眼看著就要含恨於此,一直關注著施利聆的蔣緯國知道了這事。
他親自騎著摩托,帶著程金冠去了江蘇省省會,然後兩人又去找了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周佛海。
因為蔣家二公子的身份,程金冠一直頭疼不已的問題被輕鬆解決掉,當地政府不僅快速為程辦理各項手續,還一力支付了他出國參賽的所有費用。
當年6月份,程金冠得以坐上“康德浮臺號”郵輪,向當屆奧運會舉辦地柏林進發。
臨行前,程金冠十分激動,對於幫助自己的蔣緯國,他已然把他看做是自己的親兄弟。
不僅如此,他還連連囑託蔣緯國:“我出國後,家裡的妻子和兒子拜託你照應了!”
蔣緯國一口答應,然後把這位“親”兄弟的妻子,照顧到懷了自己的孩子。
有了孩子,兩人總不能再稀裡糊塗地過下去,施利聆不可避免的考慮到更多:這個孩子不能成為私生子。
她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被冠以別的男人的父親的名義,也不願孩子成為一個父不詳亦或者無人接受的私生子。
與程金冠離婚勢在必得。
面對女子下的這個決心,蔣緯國卻一改之前的急躁,勸誡她:“你暫不要和他離婚。”
這話說出去沒幾天,他又滿臉愧疚告訴施利聆,自己要被父親送到德國去學軍事,要好幾年不回國了。
他又複述一遍,要施利聆不要衝動,暫時和程金冠保持夫妻關係,等到自己從德國回來,她再離婚。
不僅如此,他還與女子來了一個5年之約:“等我5年,我回來後再結婚。”
臨行前,蔣緯國怕施利聆對他愛意有動搖,又是接連好多甜言蜜語“你放心,我會始終如一……人變心不變!”
直到施利聆聽得眼淚汪汪,他才志得意滿,踏上與戀人分離的征程。
曝光
這一切,遠在柏林參加奧運會的程金冠自然不得而知。
實際上,他也無暇顧及那麼多。
先是在輪船上晃晃悠悠,折騰的這個從未有過海上游行經歷的男子噁心嘔吐,身體虛弱。
好不容易折騰到了柏林,還沒等他緩過神,就被拉上了奧運比賽的現場,可想而知,成績很是不好。
一直等到程金冠回到家中,心中失落的他,自然沒有看出妻子的異常,而且,疼愛妻子的他還自動合理化妻子的一切行為。
為何妻子懷孕後,姚冶城這個與他們毫不相干的長輩那麼緊張妻子?自然是因為施利聆長相貌美、性格乖巧,得來長輩喜愛。
為何施利聆時常會看著信出神,還總是一個人躲起來寫信,寄信?孕婦懷孕情緒不穩,有異常也是很正常的。
直到過了幾個月,施利聆生下一個兒子。但是對比程金冠的欣喜若狂,施利聆仍是滿腹愁緒。
程金冠不傻,妻子的異常,還有其他人神色不明的樣子,讓他隱隱察覺出,施利聆恐怕出了什麼狀況。
又一天,程金冠趁妻子不注意,偷偷攔下一封寄給她的信,信紙一展開,他當即目眥欲裂。
這封信是蔣緯國寄來的,裡面他不僅親切的叫著施利聆,與她說情話,大篇幅信中內容,竟然是在關心自己那剛出生的二兒子。
這什麼兒子?原是蔣緯國與自己那嬌妻偷情生的見不得光的小子。
闔家歡的場景猶如玻璃被打破,片片碎了下來,直扎得人心臟流血。
但是,對於丈夫的責問,施利聆只是靜坐在一旁,不發一言,不做一句解釋。
捨不得對妻子動手,程金冠流淚痛哭,邊把自己的頭往牆上撞,直撞得滿臉是血,撞得整個人發懵,還不見他停。
看到一向對自己極好的丈夫這樣受折磨,施利聆也於心不忍,她向程金冠道歉,安慰他,請求離婚,統統沒用。
極致的愛化作極致的恨。程金冠收起眼淚,收回對施利聆的所有溫情,從此之後夫妻不是陌路,必要相互折磨著活下去。
他從外帶回家一個歌女,強迫施利聆與他及歌女生活在一起。
在此後的日子裡,他又與施利聆生下兩個兒子,與歌女生下更多孩子。
有時候,還不到5歲的孩子(與蔣緯國的私生子)隱約明白自己與母親的處境,是不被這個家庭接納的隱形人。
“父親”對他的嫌惡,傭人對他的輕蔑,讓這個幼童也心中拘謹,他小心翼翼詢問母親:“我爸爸是誰?我爸爸在哪裡?”
滿腔話語皆梗在喉間,施利聆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痛苦的日子好像沒有盡頭,唯一支撐施利聆的,只有蔣緯國臨行前信誓旦旦的那一句“等我5年”!
然而,5年又5年,蔣緯國始終沒有出現。
直到施利聆透過報紙得知自己那情郎與西北豪門石家小姐成婚的訊息。
她才知道,哦,原來蔣緯國早就背叛了“我們”的約定。
分離
苦苦等待蔣緯國十多年,支撐施利聆的並不只是她的一腔“妄想”,實際上,蔣緯國早就給她寫過信。
信中他說,極恨日本人,不喜戰爭,等到抗戰回來,兒子都上小學了。
這些話自然讓施利聆忍俊不禁。但是蔣緯國所說的重點可不在這。
他表示自己在抗戰期間得了一種病,父親讓他去西北石家休養,調理好了就要與石家小姐石靜宜聯姻。
信收到手沒多久,施利聆就在報紙上,看到蔣、石兩家喜結連理的通知。
但是愛人在信中的表述,讓施利聆對蔣緯國仍舊愛自己這一點深信不疑,她堅信蔣緯國對他的新婚妻子沒有愛情。
果不其然,新婚不過一年,蔣緯國就揹著自己妻子找到了施利聆,要她帶著兒子跟他走。
至於以什麼名分,蔣緯國卻是語焉不詳。
這讓苦苦等了他十年的施利聆自然不甘心,她拒絕了情人的這一請求,想要逼迫出一個名分。
另一邊,得知丈夫去找初戀情人的石靜宜,也在家中大發雷霆。
當初可是蔣緯國殷勤圍著自己轉,追求自己,這剛一上手,新鮮期還沒過,難道就看不上了眼了。
可是蔣緯國自己對外說只愛自己的:“我與小石在西安認識,兩人一見鍾情,這正是我喜愛的物件。”
“戰神敗在愛神腳下,也是一種幸福。”
在情感上早已被慣壞的石靜宜不能接受丈夫與別的女子藕斷絲連,即使那是他的初戀,即使她生下了蔣緯國唯一一個孩子。
她每隔兩天就要來找一次施利聆,大罵她不要臉,威脅她要用炸彈炸她。
有時間興致來了,她也會直接打電話到施利聆家中,透過話筒破口大罵。
她當時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必要置你於死地!”
石靜宜這般“癲狂”的表現,讓施利聆惶恐不已,她自己也是有苦說不出。
她想找蔣緯國,讓他趕緊處理好這事,但是卻見不上人,也聯絡不到,只能從姚冶城那裡得知,那段時間他與石靜宜吵得厲害。
如此在夾縫中“生存”了兩年。
隨著國共鬥爭的日益明朗化,國民政府頹勢難擋,蔣緯國一家也準備逃離大陸。
臨行前,他寫了一封信催促施利聆,邀請施利聆帶著兒子和他一起走,以後與他及石靜宜共同生活在一起。
等了情郎十幾年的施利聆心生猶豫,這時,她姐夫阻攔了她,只說了“豪門難進”。
在經歷一番思索後,施利聆下定決定,再次拒絕蔣緯國的邀請:“決定不能進這個豪門,何況有一隻雌老虎在,必欲置我於死地!”
一個“不”字,再次拉開施利聆與蔣緯國的分離帷幕。
但施利聆再也等不到心上人的第三次邀約了。
空等
與蔣緯國長久分離後,施利聆再也無從得知有關他的任何訊息。
1952年,與施利聆互相折磨十幾年的程金冠也決心放過她,放過彼此,兩人當年就領了離婚證。
施利聆自己一個女人帶著4個兒子(與蔣緯國的兒子以及與前夫的三個兒子)艱難生存,好在還有她的姐姐姐夫,時不時接濟她,才不至於讓生活過於拮据。
後來,姐姐姐夫沒錢,接濟不了妹妹,又有海外親人寄來錢,總歸,施利聆在一波又一波好心人幫助下,磕磕絆絆地把幾個兒子拉扯大。
時間緩緩走到了20世紀90年代,她與蔣緯國分離近50年,等了近60年,這期間,她從未再談過一次戀愛,結過一次婚。
她已等了蔣緯國太久太久,等到青絲成白髮,等到婀娜身姿變為傴僂僵硬,等到嬌美容顏爬滿褶皺,她始終沒收到蔣緯國寄來的一封信。
哪怕是別人捎來的隻言片語,統統沒有。
她帶著兒子找上領導,還找那些可能會與蔣緯國有聯絡的人物,皆被拒絕。
但是她已經90多歲了,她怕自己再也等不到蔣緯國了,施利聆心中仍有希冀,可能是蔣緯國找不到自己,或是一時忘了自己。
沒關係,只要她把他們的故事宣揚出去,以他的重情義的性子,是一定回來找自己負責的。
施利聆找到記者,請求他採訪自己,然後出一本有關自己傳記的書。
她還找上同棟樓的一個電子廠廠長,請求他幫自己寫信並寄信。
一切緊鑼密鼓的進行著,也是正在這時,1995年5月,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發行了《四大家族秘史》之《蔣氏家族秘史》一書。
廠長的女兒因對老人的憐憫與照顧,從書店買了一本書帶回去。
正是在這本書中,施利聆又看到了許多與真相不符的地方。
比如兩人那場並不浪漫的初遇,被書中描述成言情小說中的狗血般的開頭劇情。
比如自己尚在人世,卻被那些出書人徑自定論為“病逝”。書中信誓旦旦說道:“施利聆小姐因一次患病,撒手西歸,留下一個兒子。”
這可讓施利聆慌了神,假如蔣緯國也看了這本書,然後就認定書中所寫的“施利聆病逝”,那她就更不可能等到他了。
焦急之下,施利聆直接把《蔣氏家族秘史》的幾位作者以及出版社給一起告上法庭。
一方面,是為了破除自己已經去世的謠言,另一方面,她希望能透過這樁訴訟案,讓蔣緯國得知她的訊息。
那時候的她,心中念著的依舊是蔣緯國曾經對自己的囑託“等我”。
可惜,她一直沒等到。
1995年8月,她發起訴訟。
1997年2月12月,施利聆躺在床上就永久的閉上了眼睛。
一直到她去世7個多月,這樁名譽訴訟案才有了結果,法院審判結果上清晰寫著:“被告在本判決生效後7日內支付施利聆精神損害賠償費3000元。”
但這一切,施利聆再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