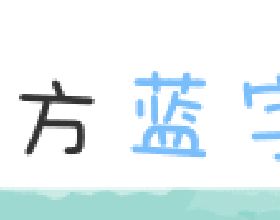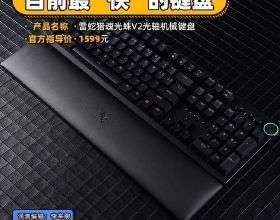一女青年四肢發熱困煩兩月餘,以肘、膝關節以遠為重,自覺勞累後熱煩睏乏尤甚。就診時感頭暈心悸,倦怠乏力,飲食尚可,平時白帶多,少腹墜脹。既往有慢性腹瀉史,脈濡,舌苔黃膩,舌質正紅。
初診以脾胃溼熱內蘊為治,方用蒼朮,黃柏,防己,牛膝,桑枝,苡米,生甘草。三劑。
藥後四肢煩熱不減,帶下反多,少腹墜脹加重,此乃藥證不符,不可囿於黃膩苔屬溼熱之論。蓋脾主四肢、肌肉,而勞累後煩熱尤甚。經雲:“陽氣者,煩勞則張。”勞則氣耗,虛陽張越於外故加重,脾胃氣虛明矣。少腹墜脹、帶多,氣陷於下故也,服苦寒之品徒傷脾氣。
此似屬東垣所謂“脾虛陰火”之證,“惟當以辛甘溫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火則愈……大忌苦寒之藥瀉胃土耳”,遂投以補中益氣湯加味,以甘溫之劑升補脾胃,稍佐苦寒以瀉陰火。
方用:黃芪,當歸,黨參,白朮,陳皮,升麻,柴胡,葛根,澤瀉,炒黃柏,炙甘草。服藥三劑,四肢煩熱頓減,帶下亦減少。前方進退十餘劑,病狀若失,黃苔亦退。東垣謂黃芪、甘草、人參三味,“除溼熱煩熱之聖藥也”,誠為經驗之論。
《脾胃論》為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東垣晚年所著,體現了他所開創的內傷脾胃學說的成就,並系統地提出了“甘溫除熱法 ”。甘溫除熱法是指用甘溫之劑治療發熱的一種治法,其所創制的補中益氣湯就是甘溫除熱法的代表性方劑。從明清至今,後世發展其法,推而廣之,已使這一治法具有了廣義的認識。今天小編就來帶大家認識一下補中益氣的具體應用。
補中益氣湯 黃芪(病甚,勞役熱者一錢) 、甘草(以上各五分,炙),人參(去蘆,三分,有嗽去之),當歸身(三分,酒焙乾,或日干, 以和血脈),橘皮(不去白,二分或三分,以導氣,又能益元 氣,得諸甘藥乃可,若獨用瀉脾胃),升麻(二分或三分,引胃 氣上騰而復其本位,便是行春升之令),柴胡(二分或三分,引 清氣,行少陽之氣上升),白朮(三分,降胃中熱,利腰臍間血)。
李東垣曰:“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面板不任風寒而生寒熱。” 並解釋其病機為“ 陰火上衝,則氣高而喘,為煩熱、為頭痛、為渴,而脈洪。脾胃之氣下流,使谷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榮衛,則不任風寒,乃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
內傷熱中證的機理是據“火與元氣不兩立”的矛盾而開展,陰火勝則元氣削弱,元氣削弱則脾胃虧虛,水谷生化的精氣下陷於腎,因而“陰火得以乘其土位“。 補中益氣湯是被後世推崇備至的“ 甘溫除熱第一方”,方中重用黃芪,補脾而益肺氣,人參、甘草甘溫益氣健脾,白朮苦甘溫健脾燥溼,共收補中益氣之功。橘皮理氣和胃散滯氣,當歸調血和營,使陽生而陰長。甘草兼能清瀉火熱。升麻、柴胡引清氣上升還於脾胃。
升麻、柴胡昇陽之說已成定論,習俗相沿,以至今日。然則升麻、柴胡升清以外仍有它途。《神農本草經》謂:“升麻味甘、平,主解百毒 …… 闢溫疫、 瘴氣、邪氣、蠱毒。”《七略別錄》認為其“ 主中惡腹痛,時氣毒癘,頭痛寒熱,風腫諸痛,喉痛口瘡”,是一味明確的清熱解毒、闢溫退熱藥物。
再以柴胡言,《神農本草經》謂:“ 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七略別錄》指出其“ 除傷寒心下煩熱,諸痰熱結實,胸中邪逆 ……” 《藥性論》認為其“ 主時疾內外熱不解”。總之,金元之前歷來把它作為一味祛邪退熱 、 清火消結藥對待。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補中益氣湯陣壘分明,由黃芪、人參、白朮、當歸等扶正藥物治其本,升麻、柴胡、 甘草等祛邪藥物治其標,同時升麻、柴胡有昇陽作用,是一首溫清並用,標本同治的方劑。李東垣在補中益氣湯後立加減用藥法,原方加五苓散、黃芩、黃連、玄明粉等,更顯示了甘溫除熱之真諦。
喻嘉言云:“脾胃者土也,土雖喜燥,然太燥則草木枯槁,土雖喜潤,然太溼則草木溼爛,以補滋潤之劑,使燥溼相宜,隨證加減耳。”補脾胃者,當使燥溼相宜,醫者選方用藥,當以甘味為主。《內經》指出:“五味入胃,甘先入脾。”又“脾欲甘”。說明甘味是補脾胃之主味。然甘有甘溫甘涼之分。陽不足者治以甘溫,陰不足者則宜甘涼,甘溫可助脾升,甘涼可助胃降。補脾胃當首分陰陽,不可認為補脾必甘溫,補胃皆甘涼,當以辨證論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