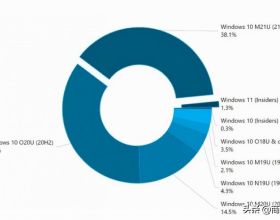作者:孫志軍(敦煌研究院藝術研究部副部長)
敦煌莫高窟初建於公元4世紀,其後歷經1000多年持續不斷的營建,形成了規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群。敦煌石窟開鑿的數量之多、藝術水準之高,歷朝歷代,都備受矚目。1900年,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使得敦煌再度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
去敦煌,成為每個人的心心念念。然而,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風、霜、雨、雪、沙”,使得原本精美絕倫的一幅幅壁畫、一尊尊佛像,或多或少褪去了顏色,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損毀。今天,或許你已經無法看到100多年前呈現在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眼前的全部。近日,我推出《世紀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一書,以“重攝”手法旨在帶領讀者穿越時空,重溫那些倖存的、逝去的、被破壞的遺蹟,感受莫高窟生命脈搏的跳動。
一、揭開寶藏的神秘面紗
沉寂了近千年的敦煌莫高窟,於20世紀初重新迴歸全世界的視野,或許並非偶然。當時,隨著中亞地理考察熱的延續與“東方學”的興起,歐洲各國的探險家、考察團隊,紛紛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來到莫高窟,並最終揭開了一座人類文化寶藏的神秘面紗。他們盜竊、劫掠了莫高窟大量的珍貴文物,與此同時也整理出版了細緻的考古、地理調查資料。單從學術層面看,這些資料具有無法取代的史料價值。
20世紀20年代,中國本土學者開始對莫高窟進行系統性的調查研究。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國民政府提出了建設和開發大西北的相關計劃,這也為中國當時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藝術家打開了考察和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方便之門。在那段風雨如磐的歲月中,這些前輩學者透過文章、壁畫臨本、照片等媒介,為莫高窟的保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儘管在1944年國民政府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之前,莫高窟完全處於無人管理的境地,但也正是這種“來去自由”,為莫高窟留下了豐富的早期影像資料。
在敦煌學勃興的今天,已有專家學者對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發生在莫高窟的攝影個案進行過研究,但卻缺乏一份對這一時期莫高窟攝影活動的清晰、完整的史料輯錄。因此,我嘗試綜合1949年以前有關莫高窟的歷史研究資料、調查報告、公函、畫冊和回憶錄等,以編年的方式梳理了1907—1949年早期探險家、學者和攝影師在莫高窟的拍攝活動。
身處絲綢之路要衝的敦煌,以陽關、玉門關控制東西來往的商旅,而絲綢之路是三條道路“總輳敦煌”,然後經“西域門戶”伊吾、高昌、鄯善,到達中亞和歐洲,這清楚地說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樞紐作用。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南壁,被華爾納盜劫的楊都出金像(區域性)。美國福格博物館藏選自《世紀敦煌》
為了解絲綢之路上不同文明的交流與融合,近幾年我多次參加了敦煌研究院組織的考察團,前往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等國考察古代文明的遺址,特別是與佛教傳播有關的遺址。透過實地考察,我清晰地感受到了不同文明對佛教石窟內部空間營造的影響:胡貌梵相的佛陀隨著絲路的延伸而逐漸中國化,佛塔由簡練的覆缽演變成繁複的密簷式中國塔,套鬥藻井從阿富汗巴米揚經新疆傳到了敦煌……
《世紀敦煌》一書是我從事石窟攝影和敦煌攝影文獻研究30多年的成果之一。這個出版計劃在多年前就形成了,但我勤於拍攝而拙於寫作,以致十年前完成的專案一直拖到現在才付印。
本書正文中的歷史照片幾乎全部由法國西域考古探險團拍攝於1908年,考慮到這些照片的重要性,探險團團長伯希和在100年前就堅持把它們公諸於世。正因如此,今天的我們才能夠透過這些照片,直觀地感受到100多年來莫高窟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原因而發生的變化。同時,也希望透過這些新舊照片的對比,喚起人們的文物保護意識。
二、快門聲響徹洞窟內外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列強在分割完海外殖民地之後,又掀起了中亞和西域探險、考古熱潮;1840年後,各帝國主義國家派遣大批考察團、探險隊來中國考察。
據統計,僅從1840年到1949年間,到達中國西北地區的探險隊就有156批之多,他們在我國西北的考察,既有學術目的,也有政治和軍事目的。正如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所說,考察中國的北部邊疆不僅有很大的科學價值,而且還可以為沙俄侵略中國西北提供資料,用“科學考察來掩蓋考察的政治目的”。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打著各種名義的外國探險隊接連來到了敦煌,他們在進行探險、考古、測繪等活動的同時,也在敦煌拍攝了許多照片,記錄了那一時期敦煌的名勝古蹟、政治圖景、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根據目前的調查,敦煌和莫高窟最早的照片是英國人斯坦因於1907年拍攝的。從1907年至1949年,有16批次來自國內外的個人或團體在莫高窟拍攝了照片,數量有4900餘張,內容廣泛涉及莫高窟的周邊環境、崖面上的洞窟佈局、洞窟內部空間和壁畫彩塑。今天回看這些照片,由於它們記錄了莫高窟較為原始的歷史資訊,為敦煌石窟的保護、石窟考古和營建史研究提供了視覺化的史料。
1907年3月,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率領他的第二次中亞探險隊,經羅布泊前往敦煌。他最初的目的是到敦煌考察古蹟,但在敦煌進行了短暫的考察後,他就明確了此行的目標——考察敦煌的古代長城遺址,考察莫高窟,蒐集藏經洞出土的古代文獻。駐留莫高窟期間,他利用了三清宮住持、道士王圓籙的無知,以極其低廉的價格騙購了24箱藏經洞出土寫本、5箱絹畫和絲織品等珍貴文物、文獻。可以說,對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禍首。但同樣也是斯坦因,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機,快門聲第一次在洞窟內響起。
1908年2月25日,法國西域考古探險團團長伯希和和他的團員們也來到了莫高窟。伯希和探險團在敦煌莫高窟的拍攝是有計劃的,題記、供養人像、有明顯風格的畫面和難以考證內容的壁畫,都是拍攝重點。專業攝影師夏爾·努埃特在短暫的時間裡,以迅速而又銳利的目光,幾乎抓住了莫高窟中所有最有價值的部分,系統地拍攝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伯希和回到法國後,在1914—1924年,花了10年時間,出版了六卷本的《敦煌石窟》,這是第一部關於敦煌莫高窟的大型圖錄,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敦煌石窟藝術。這部圖錄成為早期研究敦煌藝術最主要的影象依據,是當時國際敦煌學界深入瞭解莫高窟的經典之作,其影響力時至今日仍不可小覷。
1910年至1914年,日本西本願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組織了第三次亞洲腹地探險活動。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日本學者,也因此在敦煌和新疆多地對佛教遺蹟進行考察和發掘。
1914年5月,俄國新疆考察隊成立,隊長為奧登堡,成員有畫家兼攝影師杜金,地形測繪師斯米爾諾夫,民族學家龍貝格以及藝術家貝肯伯格,主要研究物件是敦煌莫高窟。1915年1月26日,俄國新疆考察隊啟程回國,他們帶走了在莫高窟測繪的433個洞窟的平剖面圖以及拍攝的2000餘幅照片,還剝走了一些壁畫,拿走了十幾身彩塑,復描了幾百張壁畫,並且做了詳細的文字敘錄,同時也竊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區洞窟中清理發掘出來的多種文物。在當地,他們還收購很多繪畫、經卷等文物。
1924年1月21日,美國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的蘭登·華爾納到達敦煌。次日,他前往莫高窟。華爾納此行的目的,是從東方美術史的角度來考察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在隨後的10天裡,華爾納花了5天時間,用事先準備好的膠布,粘走了大小不等的12塊壁畫。與此同時,他也拍攝了照片。1925年,華爾納率領的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再度來到莫高窟,攝影師理查德·斯達拍攝了13幅照片。在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拍攝的莫高窟照片中,北大像佛頭暴露於室外的照片、第328窟佛龕內南側的供養菩薩搬出洞窟時的照片,都是孤本,具有無與倫比的史料價值。
1934年11月5日,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從安西來到了敦煌莫高窟。根據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記載,他於黃昏時分來到莫高窟,看了一兩個洞窟,第二天,他看了九層樓以北的21個洞窟。在斯文·赫定基金會公佈的斯文·赫定攝影檔案中,他在莫高窟考察期間拍攝了17幅照片,多為莫高窟外觀,其中尚未竣工的九層樓照片是九層樓的首次曝光。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歷史照片也凝結成了一部敦煌的百年曆史。
三、穿越時空參悟文物攝影的真諦
1984年9月,我考進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報到當天,被分配到資料室攝影組學習攝影。從那時到現在,我一直在敦煌莫高窟從事文物攝影工作,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多麼幸運。說起來,我拍照片尤其是文物題材照片的時間算是比較長了。但坦率地說,直到2000年,我才開始逐漸領會文物攝影的真諦。在此之前的十多年,我只是專注於攝影技術的精進,缺乏對文物所蘊含的文化價值的思考。
多年來我還有一個愛好——收集與敦煌莫高窟有關的物件。由於職業的關係,我尤其痴迷與影像相關的東西,敦煌研究院早期的攝影檔案卡片、底片袋、修相臺等,我都收藏,不過最關注的還是敦煌和莫高窟的歷史照片。我很早就有意識地收集敦煌和莫高窟的歷史影像。在二三十年前,莫高窟歷史照片的刊佈還非常有限,我每看到一張沒見過的老照片,就趕緊翻拍下來。那時候,出版物裡的照片畫素大多較差,有些被反覆翻拍的照片基本上看不到細節,比如斯坦因拍攝的藏經洞外觀那張。近十幾年來,隨著網際網路和數字影像技術的發展,收藏於世界各地的敦煌及莫高窟的攝影檔案被越來越多地公佈出來,特別是國際敦煌專案上線後,一些極具價值的敦煌莫高窟的影象如同涓涓細流,在網際網路上不斷出現。就這樣,經過十多年的時間,我逐漸收集了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奧登堡、華爾納、陳萬里、斯文·赫定、巴慎思、石璋如、羅寄梅、李約瑟、艾琳·文森特和約翰·文森特等人拍攝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數千張。
隨著我的攝影藏品不斷充實,我開始有條件系統地研究20世紀前期由斯坦因、努埃特、杜金、羅寄梅等人拍攝的莫高窟。這些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的照片,讓我直觀地瞭解到當時敦煌和莫高窟的面貌——那時的莫高窟一片荒蕪破敗,崖體坍塌,棧道毀壞,洞窟敞開,地上散落著壁畫殘片,甚至有許多洞窟被流沙淹埋,一些洞窟裡砌起了灶臺,盤起了火炕,成了人們的棲身之所,歷經1000多年的神聖殿堂遭到了自然的侵蝕和人為的破壞。
這些照片也使我對石窟的攝影表現有了新的認識,比如斯坦因在遺址場景中安排人物作為比例參照,努埃特對壁面的空間關係處理,羅寄梅富有文人意趣的洞窟空間營造……
隨著對敦煌和莫高窟的認識逐漸深入,這些照片在我的腦海中逐漸拼湊聚會,還原出了一個原生態的、有別於當下的敦煌莫高窟。它既是時間的不斷累加和演變,也是空間的不斷變化更迭,它就像今天流行的AR、VR影象,在我的腦海裡不斷閃現。在這樣的學習中,我想到了用“重攝”的方法來表現莫高窟“彼時與此時”的變遷,為敦煌石窟的歷史、文化、保護研究追溯直觀的歷史資訊。
我仔細分析並多次模擬斯坦因、努埃特等人拍攝的莫高窟的季節、時間、角度、攝影鏡頭視角、底片畫幅比例等拍攝因素,在最近的十多年間,按照他們的拍攝角度對莫高窟的外觀和洞窟內景進行了重攝。結果表明,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莫高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損毀、營建、保護、修復在迴圈往復地發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透過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和斯文·赫定的照片,我們可以直觀地瞭解莫高窟北大像從曾經的無遮無蓋到九層樓的落成,時間跨度上也印證了《重修千佛洞九層樓碑記》中關於修建九層樓的記載。
透過對歷史照片的研究分析,以及對中亞、西亞古代文化遺址的考察,我現在拍照片時思考的問題更多,面對一個洞窟或一處遺址,更加註重去發現它所隱含的文化多樣性,追求在現時觀照“彼時”。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0日12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