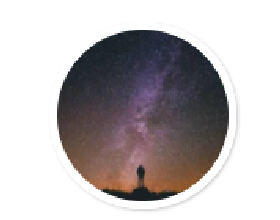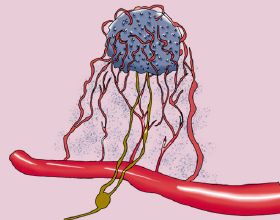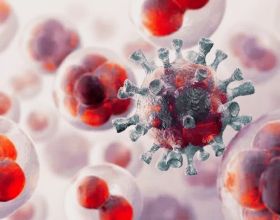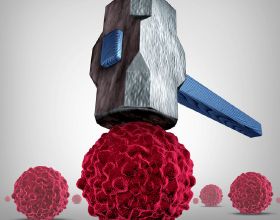1971年,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首次回國進行訪問,這時距離他離開自己的故土外出留學,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六年時間。年近50歲的楊振寧一下飛機,就對接待的工作人員說出自己第一個要見的人的名字。
那個人,就是鄧稼先。
楊振寧與鄧稼先在幼時就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兩人的父親鄧以蟄和楊武之是老鄉,他們經歷相似,後來也同在清華大學執教,私交甚篤。這種感情自然而然讓孩子也彼此相熟。
楊振寧大鄧稼先兩歲,中學時代,兩名少年一起在崇德中學唸書。課餘時間,其他同學總看見他們一起玩耍、學習,形影不離。楊振寧認為年長的自己作為哥哥,當然得對鄧稼先百般關照,他們之間無話不談,也透過談話瞭解對方遠大的理想與胸膛中熾熱的愛國之心。
少年時代的感情總是最為誠懇、真摯、熱烈的,楊振寧與鄧稼先間跨過半個世紀的友誼由此開始,至死不絕。
1950年,在美國留學的鄧稼先拒絕美國政府的留美提議,謝絕同校校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回到祖國。自此,楊振寧、鄧稼先兩位同樣在物理學上做出突出貢獻的老友天各一方。
後來,清華大學為了紀念鄧稼先而演出的話劇《馬蘭花開》中,開場的一幕便著重描述了鄧楊二人的友情:
圓明園的大水法的石碓前,“小楊振寧”在玩耍中無意間發現了一枚子彈,他拾起那枚子彈觀察片刻,拿給身邊玩耍的夥伴“小鄧稼先”看。兩個人結合過去的歷史,都認為這枚子彈是從前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遺留下的。
他們握著這枚子彈,彷彿握住了中華民族從前那段飽浸血與淚、充滿屈辱與傷痛的歷史。“小鄧稼先”向夥伴說:“我長大後要造一枚最厲害的子彈,看誰還敢欺負中國……”
我們無從得知真實的鄧稼先是否親口說出這句話,但我們同樣能夠明白,這的確是鄧稼先最大的心願,他終其一生都在為這句話而奮鬥,他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時間全部灌注於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發。
在那個困難的年代,鄧稼先的力量、許許多多科研人員的力量像一道道光束,匯聚在戈壁灘,匯成了那一朵驚天動地的“蘑菇雲”。
“兩彈元勳”鄧稼先是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開拓者與奠基者,他的功績像一顆星辰,投身於名為“新中國”的銀河綻放光芒。
1924年6月25日,一個男孩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城外的鄧家祖屋中,家人為他取名鄧稼先。
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母親王淑蠲也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們都深知知識的重要性,於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科學知識,並在未來運用自己的學識報效國家。
而鄧稼先在小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出他在唸書上過人的天分,父母為他開蒙時發現他的記憶力驚人,於是決定讓他提前正式讀書。
1929年,只有五歲大的鄧稼先進入北平武定侯小學唸書。在學校中,他雖然年幼,但面對學習極其專注,他的成績在學校裡總是名列前茅,得到眾人稱讚。
12歲那年,他就順利考進北平崇德中學。在學校裡鄧稼先接觸到了英文、數學和物理等科目,這為他日後留學海外、歸國研究都打下了基礎。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少年鄧稼先生活於淪陷後的北平,他上學歸家的途中,經常看見日軍散兵欺壓中國百姓,此情此景,他心中充滿屈辱與怒火,這少年也因此立定了自己的志向。
他要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民族崛起,讓中國強大。
他的父親鄧以蟄教育他:“稼兒,你一定要學科學,學科學能幫助國家,對國家有用的。”
這句囑託被鄧稼先牢牢記在心中。1941年,鄧稼先考進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學習,在學校中,滿懷愛國熱情的鄧稼先經過同學楊德新的介紹加入了“民青”這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他懷揣革命理想,積極響應號召,參加各種學生運動,而同時,他也沒有遺忘自己曾經立下的志願,要為國家而努力學習,鑽研科學知識,在將來做出自己的貢獻。
1946年6月,鄧稼先畢業後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學物理系擔任助教。他那時的想法非常簡單,也就是在研究學術的同時,盡己所能為國家培養更多的科學人才,為我國的科學事業添磚加瓦。
鄧稼先在北京大學的生活十分怡然,說一句“歲月靜好”也不為過。但是這對於他來說還不夠,他看中在當時科學水平更高的美國,決定告別祖國和親人,“師夷長技以制夷”。
1947年,鄧稼先參加赴美研究生考試,順利考中後進入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讀研究生。
鄧稼先的留洋生活十分清苦,他沒有充足的後臺資金作為保障,在最開始沒有獎學金的時候,甚至飯都吃不飽,在飢餓中鑽研學問對鄧稼先來說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那時候鄧稼先與洪朝生一起住過美國老太太的小小閣樓,有一回兩人外出吃飯,點了兩份牛排,鄧稼先看了看自己的那份,又看了看洪朝生的那份,忍不住對他說:“你那份大,我的小。”洪朝生笑起來,將兩人的牛排對換。
但即使是這樣艱難的環境,也沒有影響鄧稼先對於學習的熱情,在1950年,鄧稼先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年僅26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被人稱為“娃娃博士”。
如此成就自然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注意,他們同樣非常需要優秀的科學人才,於是企圖用利益說服鄧稼先留在美國進行研究工作。他們承諾為他安排工作,給他更好的科研條件與更優越的生活條件,這些都是當時的中國還沒有辦法提供的,但是鄧稼先依舊選擇了回到中國。
他從來不曾忘記,自己隻身來到美國,是為了將學習成果帶回祖國,而不是為名為利。個人的物質生活是否優渥對鄧稼先來說並不重要,他要的是見證國家成為科學強國,傲然進入世界強國之列。
1950年8月末,此時距離他獲得博士學位才過去不久,鄧稼先這名離家多年的遊子,已經迫不及待登上輪船,進入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國母親的懷抱。
鄧稼先在當時對急需科學技術人才的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回國後就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擔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工作。
回國後的鄧稼先為了給國家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埋頭工作學習,他的勤奮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在此期間,他先後與人合作發表瞭如《輻射損失對加速器中自由振動的影響》、《β衰變的角關聯》等論文,成為了我國核理論的奠基人之一。
終於,鄧稼先62年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時刻將要來臨,那一天後,他會走出研究院,消失在眾人的視線中,堅定去往渺無人煙的戈壁灘。
鄧稼先在戈壁灘,一抬頭,看見的是萬里碧空,他能感受到自己被祖國的天空、土地所環抱,而他也心甘情願讓自己的生命化為“養分”,幫助國家科學發展。
1958年秋天,錢三強親自找到鄧稼先談話:“國家要做一個‘大炮仗’,這件事必須保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你是否願意參加。”
短短的一句話,鄧稼先的血液卻沸騰了,他的手指因激動而微微顫抖,在錢三強期許的目光下,他毫不猶豫地點頭接受了這項艱鉅的任務。
這一天,終於來臨了。
鄧稼先深知這項研究試驗的重要性,他對此守口如瓶,不曾向任何人提起,好友楊振寧含蓄地詢問過此事,他只回答不知情。
別說楊振寧,哪怕是對自己的妻子,鄧稼先也沒有透露出半點資訊。他向許鹿希說:“我要調動工作,離開很長一段時間。”
許鹿希看他認真而不捨的神情,起初還沒有完全明白“離開很長一段時間”這幾個字裡代表的意思,不以為意地問鄧稼先要去做什麼,能不能給自己信箱的號碼,好方便自己能聯絡到他,緩解夫妻兩地分居的相思之苦。
鄧稼先卻緩慢而堅定地說:“我不能說我要去做什麼,也不能和你通訊。”
許鹿希聽見這話,當時腦子裡就一片空白,她錯愕地睜大眼,隱約有種自己將要失去丈夫的強烈恐慌。這名女子當時不過30歲,是位年輕的太太,兩人的孩子也年幼,怎麼能忍受與父親的離別。
“如果做好這件事,我這一生都很有價值,”鄧稼先看出她的悲傷,心裡也非常難過,他好半天才堅定地向許鹿希講述自己的想法,“就算死了也值得。”
許鹿希在後來回憶起那個夏夜,眼中依舊泛起漣漪,而當時身為年輕妻子的許鹿希更是止不住流淚。她聽出鄧稼先話語裡決絕的態度,也因為“死”這個字眼而擔憂不已,但是她同樣明白,什麼都不願說的鄧稼先要去做的是一件重要的大事。
最後她對丈夫說:“一切都交給我,我支援你。”
可許鹿希沒有想到,自己丈夫這一去,就是二十八年。
許鹿希在老年時一點一點細數自己與丈夫相處的時間,不知不覺淚流滿面。她與鄧稼先的感情非常深厚,他們是少年夫妻,是志同道合、相伴相守的伴侶。
他們初識是在1946年,那時候許鹿希考上了北京大學醫學院,而鄧稼先則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助教,負責教醫學院物理系的實習課。在不苟言笑的大學教授中,年紀輕輕的鄧稼先顯得平易近人,給許鹿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課後,上進勤學的許鹿希為了吃透知識,經常帶著課業內容向鄧稼先請教,鄧稼先對這名勤奮好學的女學生印象也很不錯,兩人在學習交流中接觸愈加頻繁,愛情之花也在細水長流的生活中悄悄綻放。
1953年,許鹿希畢業之後在眾人的祝福下與鄧稼先結為夫妻,在中關村的科學院宿舍,兩人度過了幸福安定的五年。
而在分別後的二十八年裡,鄧稼先也回來過幾次。
鄧稼先回家後,拿懷念的目光滿屋梭巡,他仔細端詳、記憶家中的擺設,但見面的時間短暫到他來不及與許鹿希說上幾句話,警衛員一上來,兩人就再次分別。
1971年的夏天,由於楊振寧抵達上海指名要見鄧稼先,周恩來立即召其回到北京,許鹿希也得以再見一次自己的丈夫。
那一面,許鹿希印象深刻,她是為鄧稼先的變化而吃驚。在她眼中,鄧稼先已經不像年輕時候那樣精神,他的背似乎佝僂了一些,也長出了白頭髮——分別的這段時間裡,許鹿希老了,鄧稼先因為工作,要衰老得更快,但是她不是在朝夕相處中見證對方一點一滴變化,才會在當時錯覺自己的丈夫好像是一夜之間蒼老。
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兩人在一起的最後一年,許鹿希含著眼淚堅守在病重的丈夫身邊,與他像世間所有平凡的夫妻一樣享受人間煙火,也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後一程。
這樣算起來,在兩人長達33年的婚姻生活中,真正在一起的時光,只有短短六年。
許鹿希獨自肩負一整個家庭,她照顧、教養孩子,等候自己的丈夫。兩地分隔並沒有磨損兩人之間的感情,甚至可以說,因為長時間的分別,許鹿希領受到相思的苦楚,也更明白自己是如何深愛著鄧稼先。
與鄧稼先結婚,她永遠不後悔。
而當年告別妻子與兒女的鄧稼先義無反顧去往的,是祖國最荒無人煙的地方,他所進行的,也是偉大的事業。
在最開始的時候,鄧稼先面對的情況就非常艱難。剛組建的九院是一片高粱地,理論部中學習核物理專業的也只有鄧稼先一人。
鄧稼先左右看了看,沒有因為這種情形而喪氣,他擼起袖子,帶領剛出大學的學生們白天自己動手幹體力活,建造研究需要的實驗室和辦公室,等到了晚上,所有人也沒有停止忙碌。他們聚集在一起,聽鄧稼先講解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核物理知識。
在當時的鄧稼先看來,至少有一件事是值得慶幸的,那就是蘇聯政府答應了為中國原子彈的研究提供幫助,他們會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還專門派遣專家來到中國,對我國科學家進行培訓。
但好景不長,中蘇關係惡化,蘇共中央停止了對我國一切的援助,並且撤走了全部專家。蘇聯專家在走之前對鄧稼先他們說道:“中國二十年也別想造出原子彈。”
面對這樣糟糕的情況,黨中央作出決定:中國要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這個任務沉沉地壓在鄧稼先與一眾科研人員肩頭,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點,但研發原子彈本就勢必要走過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
鄧稼先在面對這樣艱難的處境時,流露出一種中國勞動人民特有的品質。
那是一截無論遭受何種苦難都始終挺直地“脊樑”,就像歷史長河中砥礪的巨石,愛國的有志之士們在危難之時總是會挺身而出,完成一個又一個在後人眼中“不可思議”、“奇蹟”的任務,挽救於萬一。可以說,那是炎黃子孫傳承千年的氣節。
鄧稼先接受了任務,看向身邊的人們,心裡在想:那就幹吧,一定要做出原子彈。於是,他帶著那28名新畢業的大學生撲入理論知識的學習中。
鄧稼先選擇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三個課題作為理論組的主攻方向,後來的我們能夠得知,他的選擇是絕對正確的。
在設計原子彈理論模型時,由於我國的科研條件簡陋,連電子計算機都沒有,科研人員就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用計算尺和手搖計算機計算資料,這種細碎的功夫是非常磨人的,但是沒有關係,所有人艱難邁出的每一小步,都在向成功的終點走去。
工作從天亮持續到天黑,但還沒有結束,在沒有太陽的夜晚,他們用燈光代替,爭取到另一個“白天”。科研人員所用過的草稿紙紮成一摞一摞,放進麻袋裡進行儲存,這些草稿紙堆滿了一整個房間。九院的保密室中,存有鄧稼先的筆記本,這些筆記本的數量超過一百本!
在這樣的努力下,鄧稼先與其他人員僅僅用了四年時間就完成了原子彈的總體設計方案,這是一個任何人看來都不可思議的奇蹟。
1962年9月11日,由羅瑞卿審定,二機部給中央打了一個報告,報告名為“兩年規劃”,裡面提出最遲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
就在1964年,我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原子彈爆炸時,先迸射出一陣耀眼的強光,繼而升起一朵“蘑菇雲”。觀看試驗、時年40歲的鄧稼先安靜地注視著這片“蘑菇雲”,眼眶中蓄滿了淚水。
周恩來總理宣佈:“中國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核大國對中國實行核壟斷、核訛詐的歷史從此結束了!”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鄧稼先也沒有停止自己的工作,他領導著科研人員繼續對核武器的研究。
1963年9月,另一個艱鉅的任務交託到鄧稼先的手中。聶榮臻元帥命令鄧稼先、于敏率從前在九院理論部研究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那些人員,完成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任務。
1967年,在經過長時間廢寢忘食的研究工作後,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製和試驗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從原子彈的爆炸到氫彈的爆炸,法國人研究了八年六個月,美國人耗費了七年四個月,英國人努力了四年七個月,蘇聯則花費了四年。而中國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僅僅用了兩年八個月!
而在傲人的功勳之下,核輻射正一點一點蠶食鄧稼先原本健康年輕的身體。1979年,在一次核彈試驗過程中,由於降落傘在半空中突然破裂,導致原子彈從高空墜落後摔裂。
為了避免這次事故帶來的毀滅性後果,鄧稼先不顧個人安危,他獨自一人上前,將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在手中仔細檢查,就是這個舉動,讓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輻射傷害。
在當時,他對別人說:“你們站住,你們進去是沒有用的,也沒有必要進去。”
但是他自己卻義無反顧地展開雙臂,英勇地迎向死亡。
鄧稼先在回到北京後進行身體檢查,檢查結果顯示他的尿液中具有很強的放射性。面對這樣的情況,鄧稼先對自己剩餘的時光更加“珍惜”,他要利用這些時間,儘可能地為國家做出貢獻。
於是鄧稼先帶病堅持工作,直到1985年被確診為直腸癌。那時的他躺在病床上,卻對自己的死期沒有半點悲傷、恐懼,他十分平靜地向著身邊的妻子許鹿希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
他的好友楊振寧在知道這件事後,在1986年兩次進行探望。鄧稼先看見楊振寧,眼睛都明亮了許多,他打起精神,與楊振寧說話。
楊振寧看著他深陷病痛,不忍地問道:“稼先,你得了多少獎金,才願意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啊!”
鄧稼先聲音輕飄飄,卻是笑著回答:“一共二十塊,原子彈得了十塊錢,氫彈又得了十塊錢。”
臨別之前,他甚至起身,與好友在醫院的走廊上合影。鄧稼先是笑著的,他早就能坦然面對死亡,楊振寧心中卻十分悲痛,他希望能挽留住鄧稼先,於是在回到美國後,楊振寧用盡了所有的辦法,找到一種在當時還沒有上市的用於治療癌症的藥物,請人送往北京。
但是醫療工作者的努力、鄧稼先親朋好友的努力、鄧稼先的努力以及中央的努力,都沒能阻止死亡的逼近。
在生命的盡頭,鄧稼先強忍病痛,用盡最後的力氣,與于敏合作完成了一份關於中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他像一支燃燒至盡頭的蠟燭,心滿意足地留下那些光芒,在妻子許鹿希的懷中停止了呼吸。
鄧稼先這一生,無所謂虛名,無所謂利益,他走過亂世風雨,經歷國土淪陷之屈辱,也看過新中國碧空下那一抹翻飛的紅色旗幟。他在這面旗幟下,平靜從容地將自己奉獻給腳下的這片大地,只為了未來那個不受脅迫的強大祖國。
他的光輝被世人銘記,他的精神由後人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