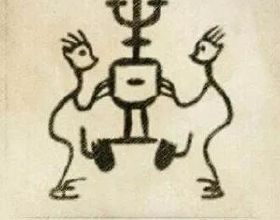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重慶衛指揮使戴鼎第四次築城,在舊城牆基礎上修建象徵“九宮八卦”的九開八閉共十七座城門,其中洪崖門為閉門(以前為開門),歷來是軍事要塞。這裡曾經發生一次慘烈的戰事,史載汪惟正於至元八年(1271)與兩川行樞密院合兵圍攻重慶,奪取洪崖門。
洪崖門這一帶陡坡,從嘉陵江邊至山崖頂淪白路,近80米高,進深只有30多米,洪崖門下懸崖是一個天然石窟,相傳古代有神仙居住而得名洪崖洞。
一
老重慶有許多詩情畫意的地方,洪崖洞便是其中之一。多年來,那些密密麻麻的吊腳樓,搭建在鋼筋混凝土的陰影裡,遮去了它舊日的容貌。這裡有一處美景叫“洪岸滴翠”,它曾經是山城的一張名片,巴渝十二景之一。
第一次見到洪崖洞,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
那時就讀於市中區西來寺小學的一名學童,正處於“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頑皮期,放學後既無狗可屠,也無鳥窩可掏,喜歡與同學走街串巷,尋找新奇。無意間,一頭闖入了洪崖洞。
記憶中是一個春日的午後,和小夥伴連蹦帶跳,從滄白路邊的臺階直衝而下,鑽進一條臨江的巷道,驀然接觸到難以想象的貧困棚戶區。
這裡說是一條街,兩旁也有房屋,但那街道上鋪的青石板已被磨出幾道凹槽,那些房屋不過是用竹杆、篾席搭建的棚屋。每間屋裡都散發著一股黴臭味,門前屋後堆滿了廢紙、酒瓶、牙膏皮、豬骨頭和爛布襟襟,那是這些住戶賴以維生的寶貝,囤集著準備送往廢品收購站。幾個老大爺、老太太咳著嗆著,用不停發顫的手忙著糊火柴盒,他們一天的溫飽繫於此。這種景象與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與在教科書上讀到的課文可是大相徑庭啊。
他們是些什麼人呢?後來才知道,他們大多是從農村進城的“盲流”,即流民,連戶口也沒有。
那條街叫紙鹽河街,瀕臨鎮江寺碼頭,千里嘉陵江在這裡即將匯入長江。
但是小孩子不關心這一切,步過石板橋,兩側的叢竹綠意盎然,青蔥滴翠,倔強的藤蔓,早已爬上高高的峭壁。就在這時,洪崖洞映入眼簾。那洞不在現在的地方,而是位於嘉陵江索道站下面。
洪崖洞洞口寬敞,約有兩人高,左右有條石砌成的石柱,洞內沒有作任何修整,石壁犬牙交錯。我們壯著膽子前行了一段路,前方漆漆然深不可測,洪崖本身猶如一扇大門,阻隔了市街上襲來的車囂人聲,四周岑寂,一切似乎都靜止了,唯有不知從何傳來滴水聲,響成一片無法闡釋的心語。受不得驚嚇,我們趕緊跑出洞來。
說來也奇怪,正因為有這麼一個神秘的大洞,後來又來過多次。
到了暮春時候,便喜歡看那一坡明明暗暗的綠,想到變幻莫測的森林。
夏日的傍晚,一場豪雨過後暑氣頓消,棚屋中的居民擺出桌椅,納涼閒話。袒胸露腹的漢子,用篾巴扇揮趕著蠓蚊;吃苦耐勞的婆姨,拎著衣物在江邊上用木棒錘打。
入秋,站在洪崖洞前望江,就見幾艘帆船在嘉陵江中走著走著就不見了,一會兒又在長江那邊露出來,只是船影已小了一半。
冬天江水淺,我們就可以花四分錢坐木划子過江去,然後原船返回來。滿江都是造紙廠排出的白色泡沫,像雪一樣。
童年時光就如同不諳茶道的人品茶,還沒咂出滋味,便倏然而去。“文化大革命”奄忽多年,在人們求生存的鬥爭中,洪崖洞被人們完全遺忘了。當踏上工作崗位,沒想到又回到這一帶,再次睹洞,已是輾轉人生旅途,多了幾分滄桑感。而洪崖洞呢,歷經風風雨雨,遍綴苔蘚橫披老藤,顯得更加衰落了些。
後來由於工作性質,有機會接觸歷史老人和一些史料,在故紙上做一番凝視,頗有心得。
清人徐大椿雲:“一生哪有真閒日,百歲應多未了緣。”絕對的閒日,哪個朝代,哪個人都不可得。但若能忙裡偷閒,或車船馬上,或理髮如廁,讀它幾頁,日久也能讀成幾本“閒書”。於是深入史料,居然有所得,多少了解到洪崖洞的由來,可供談資。
二
關於洪崖洞,清代以前無人記述。
最先注目洪崖洞者,系巴縣鄉賢劉慈,此公乃康熙四十一年舉人,留下第一首以《洪崖洞》為題的詩作:
華陽紀勝曾略聞,古洞尋幽尚未窮。怪石縱橫看作虎,枯藤屈曲掛如虹。崖懸瀑布飛晴雪,柳浣沙堤繫泊篷。仰面千家臨畫堞,蕩胸半嶺入蒼穹。地偏市遠塵難至,橋轉溪迴路忽通。石擁神龍爭見躍,天開鬼斧闢鴻蒙。滴珠泉湧洪崖下,更洗亭欹冷翠中。寶蓋飛揚來賓客,雲車飄渺接仙翁。勝遊雜遝有時盡,此地蕭條萬古空。惟有嘉陵江色在,一灣斜帶夕陽紅。
原來,在康熙四十六年間,巴縣(今重慶市前身)始設城內二十九坊,附城廓十五廂,今滄白路一帶即為昔日之洪崖坊,城牆外為洪崖廂。洪崖洞剛好在城牆下端,以地名為洞名也。
正式將洪崖洞列為“巴渝十二景”者,則是河南盧氏縣人王爾鑑,雍正八年進士,初官山東濟寧州知州,乾隆十六年貶四川巴縣知縣。
以文人學者身份而從政者,鮮有不沉溺政潮,頹然以終者。但王爾鑑雖遭下貶,卻並未沉淪。他在辦公之餘徵文考獻,晨夕把卷,追述掌故,創修了《巴縣誌》,即重慶最早最詳細的地方誌,給後人留下寶貴文獻。
其《巴縣誌》載:“城西雉堞下有洞曰洪崖,覆以巨石,其下嵌空,飛瀑時至,亦名滴水崖。有元豐時蘇軾、任仲儀、黃庭堅題刻。嘉泰中,成繪於中起吏隱亭,洪偲又起輕紅亭焉。”
吏隱亭、輕紅亭古老亦未見到,只能憑想象去猜測這兩處名亭的模樣。那迎客的大致是宋神宗元豐年間的一溜長廊,外加紅色的窈窕楹柱,一直通往洞前。上面用灰瓦遮翳,以避風雨,兩旁擱置條凳,供行人歇息。而倚崖築堂,面北五楹,窗明几淨,更宜談藝會文。亭外,溪流如飛天墜花,濺人衣裳,虹影款款,近得可以觸控。
王爾鑑《小記》曰:“洪崖洞在洪崖廂,懸城石壁千仞,洞可容數百人,上刻‘洪崖洞’三大篆字,詩數章,漫滅不可讀。城內諸水,逾堞抹崖而下,夏秋如瀑布,冬春溜滴,匯為小池入江。石臺疊翠,池水翻瀾,夕陽返照,五色陸離,莫可名狀。至若漁舟唱晚,響答崖音,又空色之別趣也。”
由此看來,飛瀑時至的洪崖洞是很有些背景的,紙鹽河街上曾走過許多詩人,蘇東坡、黃庭堅連袂而去,任仲儀行吟而來。即便是故址殘桓,名士蓍英的遺韻也是令人咀嚼不盡。
據此,王爾鑑將舊傳巴渝八景汰三增七,共為十二景,並各為小記。後跋雲:“洪崖滴翠一景,看似無著,而碧苔映水,俯嵌江波夕照,飛霞倒明崖溜,亦未可意為更換。至孔殿秋香,桂盛也,何地無桂?覺林曉鍾,清遠也,何地無鍾?北鎮金沙,形勝也,渝州襟帶江上,處處沙明日襯,何取一隅之形。餘故以字水宵燈、縉嶺雲霞、歌樂靈音三景易之。更有海棠煙雨、華鎣雪霽、雲篆風清、桶井峽猿,皆別具幽趣,空靈不著色相,遂並增為十二景。噫,血水之靈,其許我乎?於是新舊略加顛次,而各為之記。”
王爾鑑所作《洪崖滴翠》一首,流傳至今:
洪崖肩許拍,古洞象難求。攜得一樽酒,來看五色浮。
珠飛高岸落,翠湧大江流。掩映斜陽裡,波光點石頭。
稍後又有定遠知縣周紹縉、奉節知縣姜會照、舉人周開豐、川東道張九鎰、重慶知府王夢庚諸公,均詠《巴渝十二景》,內含《洪崖滴翠》。
就這樣,洪崖洞得以傳名,凡文人騷客過渝必遊此地,且多有唱和。
三
清末民初,戰亂頻仍,洪崖洞日漸譭棄,成為乞丐王國的大本營。
彼時,重慶已是長江上游的大碼頭,西南物資交流的集散地,人口劇增,市政建設卻跟不上趟。由於洪崖洞臨江,且地勢低窪,上半城的下水道均被匯聚到此處,導致不僅不再滴翠,而是裹著汙穢之物的下水道的總瀉口,成年臭氣熏天,連巡夜的更夫也不願路過這個死角。
一幫無家可歸的乞丐趁機鑽進天生的洪崖洞,作為群居的處所,他們乞討的地盤大致為上自臨江門,下迄千廝門一帶城內外街巷。
傳說中丐幫的頭頭姓馬,人稱馬三爺,是個惡丐,也就是胡攪蠻纏的乞丐,毛澤東筆下的流氓無產者。有一次,馬三爺去大陽溝菜市場討肉,與屠戶發生口角,他操起屠刀自砍自頭,刀陷額上,血流如注,一聲不哼,也不倒地耍賴。菜市場的屠戶哪裡見過這種章法?全都驚得呆了。說時遲,那時快,馬三爺毀了屠戶的秤桿,搶一塊十來斤重的豬肉壓在刀上,揚長而去。
難道馬三爺只是偶爾為之麼?非也。隔三差五,但凡口中無味,他仍是要來討肉吃,大陽溝的肉販誰敢阻他?迫不得已,乃由管理主持屠宰業的屠幫公會出面講和,規定菜市場全體屠戶輪流月供馬三爺鮮肉若干,馬三爺因而名聲大振,晉升城內數一數二的乞丐頭,以洪崖洞為據點,廣納徒眾,依附袍哥、保甲長,成為當地一霸。
洪崖洞丐幫的規矩如何?局外人當然不得而知,只知道洞內窩鋪分有等級,用疊架狗頭骨來表示,狗頭骨越多,等級越高,這與傳說中的討飯口袋上打補丁示品級的丐幫規矩不同。他們敬奉的祖師是晉時範丹,所謂“石崇富豪範丹窮”,有骨氣,值得崇敬。表示權力的打狗棍稱“紅棍”,但這些都不設位供奉。
上世紀20年代,洪崖洞丐幫的頭頭姓李,不知是馬三爺第幾代傳人,他平日坐享貢獻,不親自出馬,然而逢年過節,他則要親到大戶人家打抽豐。四十多歲的李某眼微盲,頗魁悟,布衣布鞋,衣衫整潔,不持打狗棍。他照例是站在大戶門外,手執紅帖高呼:“大德紳糧,叫化頭向你叩喜!”
大戶則照例令下人送兩個銀元,道一聲:“辛苦!”彼此客氣相安。
有面子的大戶人家,與丐幫保持這種和諧很有必要,可保無惡討者上門或假死假傷訛詐、小偷小摸之患。
聽故老講,李某在洪崖洞內有妻妾子女,自養豬、雞、鴨,豬還養得很肥。千廝門一帶的小酒館每天供他好酒,再加上小乞丐的納貢,生活優裕。
1929年重慶建市,第一任市長潘文華市長任內,千廝門外蔡家灣一帶突發一場大火,燒燬千家,老城牆高不可越,因此燒死的人不少。洪崖洞亦遭災,大火封洞,乞丐死者甚眾,李某也在劫難逃。火災次日,民團從洞中拖出若干具半焦屍體,其中便有李某及其家人,丐幫王朝因此瓦解。事後地方人士認為因蔡家灣無城門,火封道路才燒死多人,便由紳商捐助,修建了現棉花街的新城門。從此原有17個城門的重慶城多了一座新城門,沿用至今,是鮮為人知的掌故。
後來抗戰爆發,外省來人甚多,各種新乞丐也增多,也還有鑽進洪崖洞居住者。日本飛機轟炸重慶,洪崖洞洞口坍塌,以磚柱撐持。
歲月不居,古洞垂垂老矣,但也正是這種年邁,它才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歷史。
四
建國初期,西南軍政委員會駐重慶,也曾有人如杜鵑啼血,奔走呼號,提議修復“洪崖滴翠”等景觀,為山城增色。無奈此後“階級鬥爭”的罡風鼓盪勁吹,誰都難以討一個逍遙,多不願與“封、資、修”的東西沾邊。
洪崖洞的居民,跟全中國的老百姓一樣,是世界上最善良最體貼最忠誠最有耐心的了,市政當局能恩准他們在破破爛爛的吊腳樓住下去,他們已是心滿意足。即便發生洪災,江水漫上了通向老碼頭的臺階,他們也只是悄悄然遷到高處暫避一時,洪水一退又搬入老巢,照樣過日子。
如此這般,洪崖洞哪能不衰落。
所幸者,近年來房地產市場重新熱鬧起來,政府已決心使住房建設成為新的增長點,帶動新一輪經濟增長。與此同時,重慶市黨政領導,決心借西部大開發之機,把本埠建設成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
正是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洪崖洞迎來了重生之機。一位獨具慧眼的開發商看中了這裡,斥巨資打造洪崖洞,塔吊叼起成捆的鋼筋,載重卡車運來成千上萬噸水泥。我們又聽到久違的鑿石聲,叮叮噹噹地將皇恩和抗爭刻進青石,一筆一畫如流動的血脈,讓往事栩栩如生;將盛世和荒年刻進青石,點點鉤鉤如遙遠的急風暴雨,讓來者聽到回聲。
經過一年多的修建,一群仿古建築已經拔地而起,初具規模。但見樓閣錯落龍鳳翱翔,幽房曲室玉欄朱楯,軒窗掩映牖戶自通,金碧輝煌耀人耳目。更有金虯伏於棟下,石獸蹲於戶旁,壁砌生光,工巧之極。
我的天!難道這就是川東民居的代表作——吊腳樓的現代版麼?太漂亮了,活脫是一處人間天宮。
這是記憶使設計師創造了輝煌的“洪崖洞”工程——明清仿古建築麼?
不錯,一定是記憶使然。明有鄭和下西洋,清有最大的領土版圖。那時,中國的能工巧匠手藝已然登峰造極,中國的財富積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點。那時,不是中國夢想趕超世界,而是整個世界都夢想著趕上中國。
但無論是什麼,我們都欣慰,中國社會終於從荒誕中升騰起理性的光輝。
當初那些清雅純粹的詩人和道不盡的雅事,都隨著他們的背影漸行漸遠,在歷史的遠方化為一片蒼茫,這不由得讓我們感嘆人生的短暫和擦肩而過的遺憾。幸而洪崖洞正在復活,先賢們如高天長風般不衰不竭的墨跡,隨著歲月的久遠凝固成為永恆,被我們視為風範而摩挲不已。
從這層意義上講,“房屋一直修到山頂上去”洪崖洞雕塑,則可以說是一種精神的象徵,一種曾激盪過“巴山楚水淒涼地”,一種曾激盪過巴蜀兒女的精神象徵。如今這種精神經過歲月的風霜,已濃縮成了一顆顆不屈的雄心,滿腔報國的熱血和寧願苦幹、不願苦熬的形象,必將如長明燈一般閃耀在世人的心中。
空洞西城池,洪崖何代名。常懸微溜下,直入內江清。
苔翠晴逾潤,金波晚更瀠。留題人未遠,高詠謝宣城。
這首題為《洪崖滴翠》的律詩,是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周開豐所作,他曾官至福建龍巖州州同,後應聘到重慶東川書院講學。東川書院在滄白路,越過馬路便是洪崖洞,近也。
我偏愛這類古詩,乃是因為它總使我浮想起許多景仰的人物來,包括王爾鑑。世事紛紜,人情冷暖,清者自清,濁者猶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