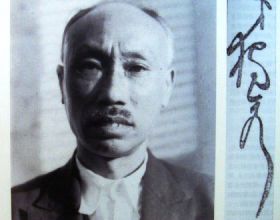祖父在世的時候,每天都要喝兩盅。祖父的“喝兩盅”是真的喝兩盅,五錢的杯子,一頓飯兩杯,一天喝兩回。除了過年以外,無論是家裡來了許久未見的客人還是小輩們“花言巧語”地勸說,祖父都不會打破自己的規矩。有時候大家勸得過了分,沒了大小,祖父也不著惱,就那麼笑眯眯地盯著你,被酒勁衝得面紅耳赤的人立馬猶如清風拂面,清醒過來,悻悻地放棄了勸酒,急忙找那貪杯之人倉促的碰一下,一口乾掉,緩解尷尬。
祖父不是沒有酒量。我曾在過年的家庭聚會上見識過祖父喝酒的神威,一瓶白酒倒三杯,一口一杯,喝完舔舔嘴唇喊祖母:“老婆子,再給我拿一瓶,我和孩子們慢慢喝。”叔伯父親倒是沒什麼反應,我們幾個孫子孫女著實驚掉了下巴:原來,祖父是深藏不漏的酒神。
祖父每天限制自己喝酒的量,不是為了養生之類高大上的理由,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他,之所以不敢放開了喝,完全是因為窮。儘管他的幾個兒子都考上了大學,進了城,立了足,成為了捧著鐵飯碗的城裡人,可大家都拿著死工資,都有一大家子人要養活,酒,尤其是瓶裝酒,那屬於奢侈品。
習慣了節儉的農村人要面子,或者說,他們除了面子能維持體面以外,再無它物可緩解內心深處的自卑。父輩兒們給祖父買酒,即便是手頭再拮据,也得買瓶裝酒。一是他們覺得老父親苦了一輩子,孩子出息了,應該好好孝敬;二是在村裡人看來,能進城上班的農村人,那就算是告別了土地,他們要是給老父親買回來散裝酒,就是不孝、就是忘了本、就是看不起自己出生的地方。這個理由有些不講理,可不管是祖父也好,叔伯父親也罷,都相當認可,令人無語。
作為跟著祖父母生活的我,知道祖父平時在家根本不捨得喝瓶裝酒。他每天喝的,都是自己做賊般去供銷社買的散裝酒,回來後再灌進空酒瓶,自欺欺人地抿著喝,彷彿這散裝酒只要進了瓶子,味道都變得不一樣一般。
兒子們買回來的瓶裝酒,祖父也不會吝嗇地放置不喝,但凡家裡來了客人,或者村裡的老爺子們在村口聚會,祖父都會囑咐我:“去,給爺爺把那紙箱箱裡的酒拿出來。”此語唯有我和祖母能聽懂,紙箱箱裡的酒是沒開封的瓶裝酒,不似木頭櫃子上那瓶,完全出自祖父個人的灌裝。
自打村裡通了電視以後,祖父最愛看的便是關於白酒的廣告,也因此生出了一個願望,嘗一嘗醬香型的白酒,且固執地認為,醬香白酒就得喝茅臺鎮的。老家地處塞外壩上,與貴州相隔千山萬水,在物流不方便的當時,買一瓶茅臺鎮的醬香型白酒是極不容易的事情。市裡面倒是有賣的,可那令人咋舌的價格抵消了父親的孝心,祖父對此毫不在意,他講話,願望就得是很難實現的,容易實現的願望,沒意思。
直到父親下崗自己做起了小生意,祖父終於喝上了醬香白酒。那瓶白酒,是父親請客時下了狠心買來的,沒曾想,酒桌上見過大場面的客戶僅僅是喝了一杯,就又要了一瓶紅酒,說是要養生。
看著客戶碩大的肚腩,父親心中暗自腹誹:都這模樣了還要養生,要養生你別喝酒啊。當然,父親的小心思不會表現出來,他強笑著陪著客戶喝著違心的酒,臨走時,把還剩半瓶的醬香白酒裝進了包中,假裝沒看到客戶略顯鄙夷的眼神。
半瓶酒,父親不捨得喝,興高采烈地把它拿回了老家,讓祖父嘗一嘗。祖父沒有嫌棄酒只剩了半瓶,趕緊下炕去洗了洗從來不洗的酒杯,倒上一杯喝了一口。一口酒下肚,祖父皺起了眉頭:“咋這味兒啊?這麼貴的酒也不好喝啊。”祖父撂下酒杯不再喝,全然不顧父親幽怨的眼神。
祖父不愛喝的醬香酒,淪落成了他向同村老夥計們炫耀的物品。一頓飯沒吃完,祖父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把我拎下了炕,讓我抱著酒瓶和他出去,臨出門口時,往兜裡踹了一把花生米。父親和祖母相視一笑,沒言語,繼續低頭吃飯。
我不樂意地跟著祖父走到了村口,那裡是全村人的聚集地,也是村中傳播資訊最快的地方。祖父大咧咧地走進人群,找塊石頭一坐,背靠著土牆對我說:“把酒拿出來,給你這些長輩們嚐嚐。”
一群老頭一人嚐了一口,酒便見了底。祖父拿著空酒瓶使勁兒晃晃,把最後一滴滴到舌頭上,然後掏出花生米給大家分著吃。老爺子們七嘴八舌地說著:“這就是醬香酒?這味兒咋不一樣呢?”祖父一臉傲然的神態:“你們懂啥?醬香酒就這個味兒,這玩意兒得細品。”我在一旁偷笑著:“您老還說別人?剛才自己不也喝不慣嗎?”
炫耀一通後,祖父在眾人羨慕的眼光中踱步回家,走的時候沒忘記拿起空酒瓶,回去擺在了家中最顯眼的大紅木櫃上,一擺多年。
近三十年過去,祖父早已離開了我們,父親也到了退休的年紀。做了幾十年小買賣的父親,沒能讓家裡大富大貴,卻也吃喝不愁。只不過,現在的父親很少去外面應酬喝酒,據他自己說,已經厭煩了那些討厭的酒局,那些酒局上喝的不是酒,是虛偽,那些酒醉的不是人,是人心。
如今的父親,喝酒更喜歡在家裡喝,喊上幾個處了一輩子的老朋友,一碟花生米,一碟鹹菜,幾顆鹹蛋便能喝上半天。他不似祖父般喝不了醬香白酒的味道,反而喝酒只喝醬香酒。作為他的兒子,我自然而然地承擔起了給父親買酒的責任,不是父親買不起,而是他覺著,兒子買來的酒比自己買的酒喝起來香甜。
給父親買酒是令我發愁的事情。買太貴的吧,買不起,買便宜的吧,醬香酒就沒便宜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了茅臺鎮金樽酒廠出產的醬香型白酒,價格適中,味道綿軟悠長,買了幾瓶回去給父親品嚐,父親捏著酒盅抿了幾口,點點頭:“相當不錯,以後就它了。”
既然父親認可,金樽酒廠的醬香酒就成了他的“專供”。幸好我除了上班外還做點副業,要不以父親的酒量,我供起來真心有點吃力。
父親似乎覺察到了什麼,有事沒事就給我孩子塞些錢,說是留著給他上學用,以前喝酒兩天一瓶,現在也學起了祖父,自己控制起了酒量。若是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時候,僅倒上一杯,有個酒味兒即可。唯有和老哥們聚會時,父親才不會扣扣索索,金樽酒一拿兩三瓶,喝光為止。
幾位常和父親喝酒的叔叔經常調笑父親,知道你有個好兒子,咱老也老了,咋這麼愛顯擺呢?父親聽了也不生氣,端著酒杯,把酒咂的聲響。沒過多久,父親的小酒局無論是誰請客,都變成了金樽酒廠出品的醬香酒,雖然價格有高有低,可老幾位喝得那叫一個香,到了他們這個歲數,酒,順口就行,喝酒的人,一定要對才可。
曾經滴酒不沾的我,有時也會陪著老父親喝幾盅,漸漸地,我也喝出了味道:或許,醬香酒真正的含義不是它的香氣,而是那在歲月中流動的酒水和凝固的情,亦或許,它的那種味道,才叫做家,叫做傳承。
原創不易,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