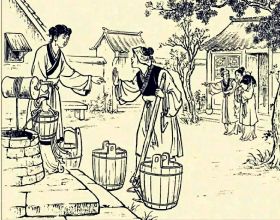大理寺正卿朱老爺,最近稱病告退,回原籍養老。
這朱老爺在官場上並未受過挫折,最後混得了一個好名聲,全身而退,真是不容易啊。然而,人都有不如意之處,朱老爺還鄉後,接二連三貼出告示,聘請家庭塾師。告示說,小兒冥頑,無論何人,只要能教他讀得四書五經,即為朱家恩人,當以薄產半數為謝。
俗話說,瘦死駱駝比驢大,朱老爺縱然是清官,那產業也少不了的。於是,眾多有學問沒學問的紛紛登門應聘,然而,兩年過去,卻不曾有人掙得這份讓人眼熱的財產。
這一天,朱老爺正在書房悶坐,家院來報,說有位年輕人自告奮勇,要教公子讀書,如不達目的,分文不取。朱老爺立即吩咐客廳奉茶。
來人也就二十出頭的光景,彬彬有禮,像個有學問的樣子,未及品茶,先是急切地詢問:“學生仇森,斗膽應聘,深知老爺張榜招賢,此事必大難。願先知道公子狀況,如森力不能及,則即刻告辭,絕對不做誤人庸醫。”
朱老爺聽了這話,不由對年輕人刮目相看了,他欠了欠身:“不瞞先生,老夫晚年得子,本來寄予無限希望,為他取名聰兒,也知老夫用心。聰兒幼時,出奇地聰明伶俐,哪想六歲那年,騎馬玩耍,不慎從馬上跌下,從此成了痴呆,說過的話,轉眼就忘。前幾任塾師,各施妙方,最後均落得前功盡棄。如今聰兒年已十六,老夫按禮給他完婚,妻子甚是賢惠,怎奈犬子不懂男女之事,現在老夫一家陷入尷尬境地,一方面幾代書香門第,卻出此劣種,惹人笑話,二來也誤了媳婦青春,愧對親家……”
仇森想了想,又請求:“不知可否面見少夫人,問一些瑣事嗎?可讓她隔簾答話,老爺在旁監聽……”
朱老爺笑了:“用人不疑。見先生年輕穩重,一日為聰兒之師,即終生為他父親,避之何為?倒是老夫不便在場。也罷,讓丫環梅香作陪吧。”
朱老爺退避時,那仇森神色嚴肅,衝他作了一個長揖。
不大工夫,美貌無比的少夫人在丫環的攙扶下步入客廳,先生抬眼一看,驚為天人。少夫人已經知道了仇先生有意教少爺讀書的事,先自深深一福。仇先生也只是向少夫人問了些無關緊要的生活細事,隨後說,願在這兒先教半年試試。
仇先生便在朱府住了下來,每天教少爺朱聰讀書。但這少爺雖然聽話,本性卻愚昧無比,教過的東西,轉眼就忘記,真所謂左耳朵聽,右耳朵冒;有時,老夫人也悄悄去書館察看,但見仇先生教識字竟不如扯閒篇的工夫多,又經常見先生與她兒媳婦閒話,心裡便不自在,私下裡對老爺說:“我看這仇先生沒有什麼特異本事,卻愛與兒媳搭話,是不是醉翁之不在酒啊,可別弄出不好聽的來。”
老爺正色道:“既然聘人為師,就該給予信任。你我若能教化這頑固兒子,何必四處求人?如今好歹有承擔的,你又說三道四,此不合老夫人品。”夫人登時無話可說。
轉眼到了中秋。先生說家遠不回去過節,朱老爺便設宴款待他。兩人對酒,說了好多知心話。
仇先生說,少爺這腦子肯定有病,只是沒人能治罷了。
老爺說,京城太醫良多,卻個個束手無策,你我又有什麼辦法?
仇先生道,人家太醫位高祿厚,名聲比金錢重要得多,公子非虎狼之藥,不能醫治;萬一投了猛藥,公子有個閃失,誰擔得了責任,所以無人肯靠前。
老爺長嘆一聲:“若是愚昧終生,不但誤我,且誤兒媳,容他披這張人皮何用,不如我明天一刀殺了他!”
“老爺當真捨得?”仇先生試探道。
“老夫雖不才,亦為過當朝二品,豈能信口開河?”此時,朱老爺已現醉態,仇先生急忙讓丫環扶老爺回去休息。
這邊仇先生又獨飲了數杯烈酒,吩咐丫環,速請少爺去書館,我要連夜教導於他。先生回他的房間寫下一封書信,放在桌上,接著,去了書館。少爺已在那裡等候了。先生教了他一陣,少爺哪裡聽得進去?惹得先生火起,罵道:“我沒想到在你這蠢才身上耗去半年光陰,此番無功而退,何面目見天下人?罷罷罷,我豁出一命,超脫於你吧!”嗖地一聲,抽出他平時掛在壁上練武用的刀,直奔少爺。
這朱聰不曉得說理,卻也知道害怕,轉身就逃,畢竟腦子有病之人,腳下不利索,幾步就被仇先生追上,不用刀鋒,卻掉轉刀身,用刀背奮力去腦後一擊,就聽“哎呀”一聲,那少爺重重地摔在了地下!
先生髮怒時,早有書僮發現狀態不對勁,飛跑去將老爺請了來。朱老爺遠遠地看見仇先生行兇,卻示意書僮不必驚呼,他也只是冷冷地觀看,及至少爺倒地,他才走近前來。
仇先生扶起少爺看了一下,喃喃道:“就在此一舉了。”抬頭看老爺站在跟前,他說道:“快找人扶他進房中休息,令少夫人通宵守視,見有什麼變故,快快告訴於我。”說罷,拉著朱老爺:“剛才之酒,並未盡興,東翁可否再陪學生一杯?”
朱老爺說:“敢不從命。”便吩咐廚中上菜。
兩人一直吃到東方發白,這時,只見少夫人的貼身丫環幾乎是跑著來報:“老爺,先生,少夫人說,少爺夜半醒來,講話思路清晰,與平時判若兩人,請問先生到底是怎麼回事。”
先生長出了一口氣:“東翁,我都嚇出汗來了。”說著連連給老爺道喜,“少爺從此可以讀書了!學生寢處有書信一封,著人取呈老爺吧。”
果不其然,少爺從昏睡中醒來後,與先前判若兩人,教他詩書,過目成誦,至年底,已經抵得常人苦讀二三年功夫了。兩年後,中了秀才,仇森先生名聲大震,求人託臉要拜他為師的不計其數,仇先生一個也不收。
朱少爺二十二歲那年中舉。朱老爺喜出望外,設盛宴慶賀,把本族和鄉親中有頭臉的全請了來,奉仇先生上座。仇先生在酒席中提出自己所學已盡,請少爺另拜良師,他要辭館回家了。
朱老爺捧出一本帳本,正色道:“當初老夫有言在先,有能教得犬子讀書者,即以半數家財相贈。今聰兒不獨讀書,且已成器,當著眾鄉親的面,老夫若是食言,何以為人!家中財產,悉數登入,請先生半數之上,更隨意取之。”
仇先生淡淡地說:“學生本來沒打錢財的主意。東翁不想知道我是哪個嗎?”
“異常之人,必有異術。老夫只相信先生為異人,其它的,先生該說,早就說了;不該說,老夫縱然想知道,也是徒勞。”
“東翁真是高人,不愧受萬民敬仰者。”仇先生道,“實不相瞞,我乃東翁仇家,本名高祥,仇森,諧音‘仇深’也。家父高建,官至提督,被誣謀反,老爺不經詳查,不容申訴便判斬刑,並累及全家。不才僥倖逃出,發誓復仇。這次進府,就是想看老爺笑話的,不想被老爺感動。”
高祥說,他原想,朱老爺不過一酷吏,他兒子痴呆,應當是報應,進府來就是想看看少爺究竟痴呆成什麼樣了,也算是一種快慰吧。然而,老爺不但給予信任,還讓他單獨與少夫人談話……
“既然讓子為先生之徒,就等於送給你當兒子,老夫自然深信先生人品。”
“所以學生為東翁大義所動。”高祥道,“學生避難深山,得異人傳授,精通換心之術,能使朽木變良才。我在教書過程中,經常閒聊,無非是觀察公子病情。可以推知,他是兒時從馬上摔下,壞了記憶。此法有二,一是換心,抽取智慧人之心血,注入公子心血中,獻血者毫髮無損,而公子七竅頓開,然而心血難得;二是猛擊其後腦,或可恢復記憶,但風險過多,稍有偏差,不但無濟於病,且有人命之虞。所以學生留下那封信,實為遺囑。那夜舉刀砸下時若有人一喊,則學生分心,可能功虧一簣。”
“我當時覺得,老夫生此痴兒,不如無有,治不好,砸死也罷,省得自己下不了手。”
“學生也擔心失手,因此,留下遺囑,學生若出了事,立即自裁,我兒也算聰明,便送與老爺為繼……”
朱老爺很感慨,他殺高提督,乃是皇上之意,他安敢不從?而高祥舍父仇而救他兒子,此情真比天地!
“學生在老爺府中一年,已探明老爺是個清官,而先父之冤,原本不怪老爺。先父和老爺一樣,都是皇上手中的棋子,他將你往哪兒放,誰也換不得位置的。所以,我知道,嶽元帥之死,未必罪在秦檜,都是那混帳的高宗皇帝呀。”說罷,衝眾人拱手,回寢處收拾行裝。
族中有人攔住高祥:“適才先生所言心血難得,我族中難道沒有智慧者嗎?”
高祥搖搖頭:“智慧者多矣,可惜心正者沒有,在公子患病期間,大家都幸災樂禍,背後議論紛紛,只關心朱老爺百年後,哪個能分得他的財產呢。這樣的心術,怎麼可能為公子所用?”
一句話,把在場的族人說得啞口無言!
(作者:顧文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