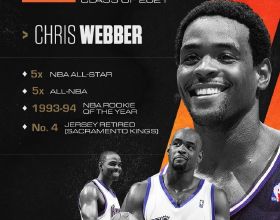秋季是愛鳥人士等候勺嘴鷸的最好時機,每年,它們都會準時出現在東海沿岸,為越冬遷徙做準備。
勺嘴鷸是一種“自帶飯勺”的小鳥:覓食的時候,勺嘴鷸就用它的“飯勺”在淺水處左右咂嘴掃動,過濾出它可以食用的海生小動物。在鬆軟的泥地裡,這把“飯勺”也可以翻動泥土,找到昆蟲幼蟲等食物。
這也是一種極危動物,現在全球僅剩不足500只。這樣憨態可掬的小鳥,又是怎麼被逼上“絕路”的?
為了保護鳥,科學家們開始“偷蛋”
勺嘴鷸在春、秋兩個遷徙季節,勺嘴鷸都會在東海完成換羽、休息、覓食,補充能量準備越洋過冬。它的遷徙路線十分固定,每年都會從俄羅斯東北部楚科奇半島凍土層地帶上的繁殖地出發,抵達中國南部和東南亞的溼地越冬。
但在勺嘴鷸的遷徙路線上,它們的越冬休息地上正在被不斷破壞:亞洲最大的海上風電場聳立在灘塗地上,金屬加工廠、化學品工廠等廢水廢氣正在汙染海灘環境,各種工程船隻想要將灘塗和淺海填成堅實的陸地。根據科學家推測,如果繼續放任發展,2070年,勺嘴鷸將損失至少57%的棲息地。
越來越少的棲息地幾乎把勺嘴鷸逼上了絕境,為了保護勺嘴鷸,經過科學評估後,從2011年開始科學家們開始了“方舟計劃”和“偷蛋計劃”。
俄羅斯遠東是勺嘴鷸主要的繁殖地,在2011年到2012年間,科學家們在那裡搜尋勺嘴鷸的蛋,並將它們帶到英國一個保護區的人工環境下進行孵化,這些勺嘴鷸會繼續在保護區內生活,而它們生育的下一代,會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送回野外的繁殖地繼續繁衍生活,這就是勺嘴鷸的“方舟計劃”。

2012年在英國保護區成功孵化的勺嘴鷸雛鳥 ,圖源:thefeaturedcreature.com
“偷蛋計劃”聽起來似乎更加離譜,它一共有四個步驟:“偷走”勺嘴鷸的蛋,帶回恆溫箱中孵化,在繁殖地搭建的鳥舍中養大雛鳥,雛鳥可以飛行之後放歸。而在被偷走蛋以後,野外的勺嘴鷸還會繼續產卵,不會影響正常繁殖。

勺嘴鷸27是“偷蛋計劃”中誕生的寶寶,Pavel Tomkovich拍攝
在“方舟計劃”和“偷蛋計劃”實施之後,研究人員也進行了後續的追蹤,他們發現,人工環境下孵化和飼養的勺嘴鷸雛鳥,存活率顯著提升。同時,研究者和觀鳥愛好者也在遷徙路線沿途發現“偷鳥計劃”中勺嘴鷸的後代,這也證明了這項保護計劃的成果。
但勺嘴鷸種群數量的增長,並不僅僅是靠愛鳥人士的保護就能實現的,如果棲息地生態環境無法得到恢復,它們依然面臨著滅絕的威脅。

覓食中的勺嘴鷸,圖源:Kajornyot Wildlife Photography
與勺嘴鷸相同,遺鷗的生存環境也在不斷地遭受威脅。
遺鷗在一百多年前被發現之後,直到1971年才被正式確定為獨立物種。它的個頭比鴿子大一點,在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打扮”,冬天一身雪白,夏天則會戴起“黑頭巾”。
鳥類學家一直試圖尋找遺鷗的繁殖地,1990年,他們終於在桃力廟-阿拉善灣海子發現遺鷗繁殖群。經過多年保護,1998年遺鷗的數量達到巔峰,有3600多巢,比最初發現時增加了將近4倍,在2002年,桃力廟-阿拉善灣海子又被列入《國際重要溼地名錄》。
但好景不長,因為降水減少,加上上游攔水工程的影響,桃力廟-阿拉善灣海子的水域面積開始逐年下降,2008年甚至一度乾涸,而在保護區內,旅遊業也一度嚴重影響了遺鷗的生存活動,這裡再也不是遺鷗的天堂,2016年遺鷗保護區內再也不見遺鷗。
而河北省康保縣又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2014年,首都師範大學北京溼地研究中心專家洪劍明教授及其團隊發現有大量遺鷗棲息在康巴諾爾湖國家溼地公園。在那裡,遺鷗繁殖的湖心島也曾經遭受過汙染的威脅,發現問題之後,洪劍明建議當地業局墊高和修復湖心島。
墊高後的湖心島也呈現出最佳生境,2016年,一共有3100巢遺鷗在康巴諾爾湖國家溼地公園繁殖,成為當年全球最大的遺鷗繁殖地。
不僅是專業人士,當地的居民也是遺鷗保護的主力軍,每當他們發現傷病的遺鷗,都會送到康保的遺鷗保護協會里進行救治。
儘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鳥類監測保護的行列,但仍然有許多野生鳥類的生活受到威脅,白頭硬尾鳥就是其中之一。
消失的唐老鴨
白頭硬尾鴨主要棲息在新疆烏魯木齊的白鳥湖,白鳥湖也是因為它而得名的。白頭硬尾鴨是矮胖型褐色鴨,在繁殖期,雄鴨的嘴巴會變成天藍色,據說它還是唐老鴨的原型。
曾經白頭硬尾鴨在國內還是迷鳥一樣的存在,人們只觀測到零星幾隻飛鳥,一直到2007年,新疆觀鳥會張耀東教授發現了白頭硬尾鴨種群,當時的種群數量是45只,但2018年年初,只剩下4只白頭硬尾鴨生活在白鳥湖中,盜獵者和環境汙染是造成種群銳減的兩大威脅。
2016年,白鳥湖民間志願巡護隊從盜獵者手裡搶救下了8枚白頭硬尾鴨蛋,當時的巡護隊隊長巖蜥為這些小生命購置了孵化箱,採取人工孵化的辦法,最終孵化出了3只小鴨。第一隻破殼而出的小鴨個頭最小,巖蜥形容“就像醜小鴨一樣”,他為小鴨子取名叫“希望”。
白頭硬尾鴨是群居型水鳥,在4天人工餵養後,巖蜥帶著小鴨子們回到了白鳥湖邊,讓它們尋找自己的家族。
放生後第2天,有2只小鴨順利融入鴨群,有1只小鴨卻不見了蹤影,巖蜥和巡護隊員沿著白鳥湖巡查,希望能找到小鴨,卻在一處排汙口發現了掉隊小鴨的屍體。經過清潔,巡護隊員認出了這隻小鴨就是“希望”,解剖後發現,希望的腸道里沾滿了油汙。最後,巖蜥把“希望”做成了標本。
“希望”不是巖蜥做過的唯一一件白頭硬尾鴨標本。
2017年5月7日,白鳥湖邊剛剛舉辦完一場白頭硬尾鴨保護的科普活動,巖蜥和他的團隊在白鳥湖邊例行巡邏,結果在岸邊蘆葦叢中發現了一隻死去的白頭硬尾鴨。
在檢查後發現,這隻白頭硬尾鴨頭部被一顆鋼珠擊中,是明顯的打鳥行為,可以判定為蓄意捕殺。巡護隊員們將這隻死去的白頭硬尾鴨取名為“小七”,以此紀念它死去的日子。為了更好地儲存它,巖蜥現場解剖了“小七”,回家後將它製成了標本。
流浪狗和冬遊人群也是影響白頭硬尾鴨生活的因素,為了更好地保護這些小動物,白鳥湖邊圍上了護欄,也貼上了許多宣傳標,也不斷有志願者加入白鳥湖的巡護隊中。曾經有一名在湖中游泳的小夥子被勸阻之後,也加入了志願者團隊一起保護白頭硬尾鴨。
在白頭硬尾鴨之外,巖蜥和他的巡護隊也在關注著當地的野生動物們,每當他們發現動物的死亡,巖蜥都會將它們的屍體製成標本保留下來,便於大眾更好地保護和研究,“這就是所謂的賦予生命價值吧。”
“它們是我的神話”
和巖蜥一樣,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鳥類保護的行列。
陳正平從小在海南儋州灣長大,他曾經是個商人,做著海鮮生意,最鼎盛的時候,一年的收入超過百萬。
儋州灣的大片灘塗是水鳥的天堂,也是候鳥遷徙的主要棲息地之一。但隨著水產養殖產業的興起,為了建造更多的養殖塘,紅樹林被不斷砍伐,陳正平野見證了儋州灣的環境的變化,“儋州灣的魚少了,灘塗上再撿不到一桶桶的魚蝦。連原先飛來飛去的鳥,也幾乎消失了。”
陳正平希望自己能出點力,恢復儋州灣的生態,2010年他應聘成為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專職護林員,2019年他又加入SEE任鳥飛在儋州灣開展的公益專案,開始關注鳥類保護。
為了監測鳥類,陳正平會帶上望遠鏡、相機等裝置,靠著水和乾糧在灘塗邊守上一整天。他是第一個在海南拍下白肩雕的人,也曾經在這裡看到過勺嘴鷸。2021年,陳正平還在儋州灣監測到23只瀕危水鳥黑臉琵鷺,這種鳥類目前全球僅存5000只左右,而在儋州灣觀察到的黑臉琵鷺卻在逐年增加。
在拍攝之外,陳正平也會用手機app為發現的鳥類做記錄,在app上儋州灣的地圖上被打滿了密密麻麻的小點,上面標註了他觀測到的鳥類和數量。今年是儋州灣候鳥數量最多的一年,“今年的鳥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比我小時候都多。”
觀測到珍稀鳥類是所有愛鳥人士的夢想。廈門雎鳥生態的成員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夢幻時刻”。
2019年一次乘船出海調查中,成員們在一群大鳳頭燕鷗中發現了中華鳳頭燕鷗。中華鳳頭燕鷗是一種“神話之鳥”,它是一種極危物種,現在僅存百餘隻,自從1863年被正式命名以來,人們對中華鳳頭燕鷗的觀察記錄屈指可數,變幻莫測的行蹤令其更顯神秘。
對於這次經歷,廈門雎鳥生態的成員YY感嘆:“它們是我的神話。”
觀鳥正在成為一種大眾愛好,也是大眾參與鳥類保護的一種途徑之一。波斯頓蕨是廈門雎鳩生態的一位調查志願者,她常常會帶著兒子一起去灘塗邊觀鳥,觀鳥給了這位年輕母親許多的生活體悟,她也開始反思,人類需要那麼多的物質來填充慾望嗎:
“水鳥們也很遷就,沿海土地正在不斷被開發利用,周圍塵土飛揚、機器轟鳴是常態,有時候會有十幾臺挖掘機在旁邊工作。遇到鹽田施工,它們就密密麻麻擠在田埂上。遇到灘塗消失,就在填海之後的沉降區勉強棲居。
水鳥的數量正在銳減,到處都有填海工程。毫無疑問,人類渴望更多的生活空間和更高的生活標準,但孔子早就說過,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也是可以過得快樂的。那麼,我們是否也該反思一下,人類無窮無盡的慾望,是不是需要稍加剋制?”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了觀鳥的隊伍,有些人是因為熱愛,有些人是因為好奇,不管是因為何種原因,大家都在為鳥類的保護貢獻一份力量。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一點點力所能及的事。
勺嘴鷸全球不足500只,中華鳳頭燕鷗的成年也僅剩不到150只,但它們仍然可以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片大地上。
,或者點選,一起來守護它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