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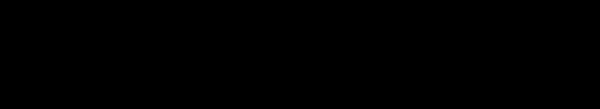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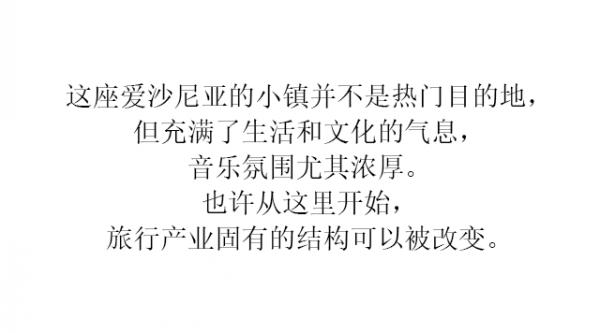
若是前往還沒被遊客擠滿的小國的內陸地區旅行,人們通常會想到寧靜祥和的田園風光和當地人好奇的目光。但偶爾,也會遇到一座充滿活力的小鎮。那裡沒有大都市的車水馬龍,但有美食、文化和有趣的人,彷彿所有樂趣都只為你而生。這樣的小城就是值得你特地繞道而去的地方。維爾揚迪,一個位於愛沙尼亞南部、離拉脫維亞邊境不遠的小鎮,就是這樣的地方。
新冠疫情爆發前,我去了那裡旅行。即便在當時,愛沙尼亞也不在大多數旅行者的必到名單上。雖然維爾揚迪每年夏季會接待大量遊客,但相比於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肯定相去甚遠。疫情蔓延後,遊客也幾乎都不來了。但去年夏天,這裡掀起了一股國內旅遊熱。

愛沙尼亞的維爾揚迪未必出現在大家的旅行清單上,卻是讓人感覺不枉此行的那種小鎮。你可以稍作停留,去帕拉湖(Lake Paala)暢泳一番。
安妮卡·維曼(Annika Vihmann)在愛沙尼亞傳統音樂中心(Estonian Traditional Music Center)工作,她說:“維爾揚迪某些酒店在夏季會迎來創紀錄的入住率,這讓酒店能捱過一年裡的其他時間。”她還認為,這場疫情讓人們有時間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進一步催生了創業熱情——當地湧現了新的咖啡館和商店。
目前,愛沙尼亞已對歐盟及其白名單上的國家的遊客開放,這些國家的來訪者即使未接種疫苗也能入境。而只要有簽證,任何國家接種過疫苗的遊客都可以進入該國。
隨著旅行業復甦,航空公司正忙著增加飛往羅馬、雅典、巴黎、馬德里等熱門目的地的航班。但若想終結疫情前備受指責的“過度旅遊”,那麼到訪像維爾揚迪這樣的地方,或許是一個新的開始——這種地方通常比較偏僻,旅行體驗也更加悠閒和舒適。
因為身在塔林的朋友提前介紹過維爾揚迪的情況,所以飛抵塔林後,我就立馬從寬敞、舒服的倫納特·梅里塔林機場(Lennart Meri Airport)跳上了最近一班電車,沿著電車延長線來到中央車站,順利搭上了南下的火車。一路上,我們經過了延綿數公里的白樺林和沉睡的小鎮,兩個小時後來到了這條線路的終點站,小小的維爾揚迪車站。
1991年前,愛沙尼亞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近幾年,這個國家已全心全意地融入了歐洲,還推出了許多有前瞻性的舉措,如電子居留計劃、居民享受免費公共交通等。儘管受到鄰國影響頗大,但這個國家依然顯得與眾不同。從食物到森林,許多方面都有北歐的感覺。但從一些建築中,仍能看到代表集體記憶的蘇聯元素,比如大部分蘇聯城鎮中常見的灰色、陰鬱的公寓樓。此外,當地語言與芬蘭語關係緊密(這意味著,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聽不懂的)。
我在愛沙尼亞感覺到意想不到的輕鬆自在,也感受到當地的年輕與活力。這個國家在尋找自我定義時容納了許多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與鄰近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相比,當地物價可能不到前者的一半,這意味著同等預算下能做的事更多。
富有經典波羅的海風情的老城區是維爾揚迪的核心區域,一排排木屋處於不同的翻新或衰敗狀態,有的被漆成粉色,有的則保留了原木色。鵝卵石街道旁矗立著風格各異的大型建築,從裝飾藝術風格到瑞士木屋應有盡有。對愛沙尼亞而言,這樣的城市形態並不尋常,因為當地屬於丘陵地帶。老城區之外是連綿起伏的綠色山丘,然後有一條長長的斜坡通向位於城市東南邊的維爾揚迪湖,在溫暖的月份,湖畔是很流行的去處。
維爾揚迪湖很大,湖邊的高地上有一座古堡遺址。那是小鎮的主要景點,每年會舉辦有多場演出的民謠音樂節。音樂節在暫停一年後,於7月22日至25日重啟。
為期4天的音樂節裡,常住人口僅17000人的小鎮將迎來超過一倍的人流量。今年,每日活動人數上限被控制為5000人。不過,藝術節並非鎮上唯一的活動。塔爾圖大學(Tartu University)下屬的文化學院除了開設木工、編織等傳統藝術和手工藝學位,還提供音樂課程。學院裡有供舞臺表演的國家級劇院,烏格拉劇院(Ugala)。這座劇院頗有首都城市劇院的氣派。巨大的室外圓形劇場(所有重要的音樂節活動都在這裡舉辦)則是城中的另一個表演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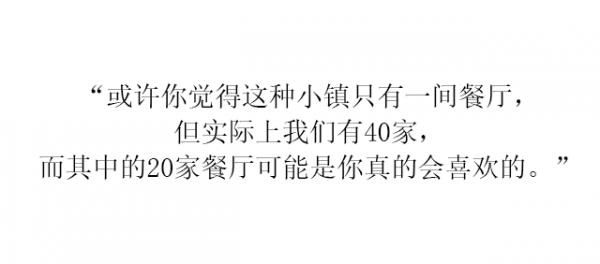
上述舉措都在促進文化教育產業的迴圈再生。儘管小鎮面積不大、位置偏僻,但仍讓人感覺是一個文化中心。隨著越來越多的創意人士從塔林攜家人來此定居,逐漸產生了雪球效應。馬丁·布里斯托爾(Martin Bristol)是一名愛沙尼亞工匠,住在小鎮以北約1小時車程的另一個座名為埃斯納(Esna)的小城。他說:“或許你覺得這種小鎮只有一間餐廳,但實際上我們有40家,而其中的20家餐廳可能是你真的會喜歡的。”
這是一座可愛的小鎮,來訪者不妨就隨意逛逛,或許能偶遇意外的小驚喜。溫馨卻也熱鬧的Roheline Maja咖啡館靠近老城區,我在此品嚐到了此生最美味的肉桂麵包。我和店主卡麗·奧尼(Kaari Onni)(她用新鮮的有機肉桂和雞蛋做麵包,丈夫來自新澤西州;兩人育有6個孩子,都在學音樂)聊天的時候,看見一個拿著小提琴的年輕女孩走了過來。她站在離我們大約3米遠的地方,開始拉起了小提琴。隨後,我們還聽到了更多的音樂,比如從街上傳來的笛聲。奧尼解釋說,孩子們有時候會站在店前演奏,希望能得到一個肉桂麵包,但現如今,我覺得他們似乎僅僅是為了演奏而演奏。

在Roheline Maja咖啡館,大家都知道孩子們會在店外靠演奏樂器來贏得肉桂麵包。
在鎮上的第二天,我和愛沙尼亞傳統音樂中心的執行長塔爾莫·努爾馬(Tarmo Noormaa)共進午餐,維爾揚迪的大部分音樂活動都由該中心策劃。音樂中心在一處廢墟旁的一棟翻新過的老建築裡,那棟建築曾是個搖搖欲墜的伏特加酒倉庫。該中心全年無休,每年會舉辦150場音樂會,旗下還在經營一座音樂圖書館和其他事業。音樂節的成功,離不開努爾馬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努力。他們讓音樂成為了小鎮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讓年輕人也參與了進來。
“我覺得,這是維爾揚迪的一個成功事例,”努爾馬告訴我,“我們的大部分觀眾都是年輕人,他們創造了濃濃的音樂氛圍。真希望年輕的音樂家們能深入藝術之中,在把傳統音樂帶到當下的同時,又不會失去以往的歷史根基。”
維爾揚迪的文化生活還不止如此,當地還有座奇妙的以長居於此的市民保羅·康達斯(Paul Kondas)命名的Kondase Keskus藝術館。館內陳列著許多愛沙尼亞外來者或非科班藝術家的作品。保羅·康達斯本人在1985年去世前,悄悄創作了大量畫作並只與他的密友們分享。博物館主廳擺放著他的部分作品(其他幾個房間用來舉辦愛沙尼亞國內外的巡迴展),從中很快就能覺察到他刻意保持低調的原因:許多作品都暗藏著尖銳的政治諷刺意味,但往往經過了巧妙的修飾。
維爾揚迪市中心幾乎看不到蘇聯式的公寓樓,對當地來說不失為一大幸事。位於核心地帶的唯一一棟大型蘇聯建築是以前的黨部。這是一座粗野主義的建築,就在Kondas Keskus藝術館所在街道的街尾,造型醜陋但挺有意思,不過後來被拆掉了。
某晚,我去了當地頗受歡迎的Mulks葡萄酒吧。老闆威廉·瓦里克(Villem Varik)還在運營一個由小鎮和文化學院聯合發起的創意產業中心,旨在為藝術和傳統文化創造創業機會。自疫情爆發以來,該中心一直處於暫停狀態,但瓦里克仍是鎮上藝術活動的核心人物。

Mulks葡萄酒吧也供應產自愛沙尼亞和世界各地的各種手工啤酒。
Mulks酒吧供應葡萄酒、乳酪和烤肉,還有小鎮上最棒的手工啤酒。手工啤酒行業正在愛沙尼亞蓬勃發展。瓦里克迫不及待地帶我上樓參觀當地首傢俬人畫廊Rüki Galerii。畫廊於2019年開業。他說:“作為一個社群,我認為我們做得相當不錯。我們正在轉型,計劃從私人企業獲得更多投資,來資助我們的創業者。”
第二天,我想去探索一下小鎮以外的地方。聽說有個叫安德烈·安斯佩爾(Andres Ansper)的塔林商人雖然事業成功,但經歷過種種磨難後,決定遷居於此。他選擇在位於城南的魯迪自然公園(Loodi Nature Park)裡一箇舊穀倉安定下來。從此,他穿上工作服,留起大鬍子,開始用木頭製作風格獨特的燈罩等物件,最後把那裡變成了“世界上最孤獨的燈具店”(The Loneliest Lamp Shop in the World)。如果有顧客碰巧路過,都會被領著爬上舊樓梯(意料之中的事,穀倉前身也是一個伏特加酒倉庫)。上樓後,你會看到幾十個形狀大小各異的木製燈具,有的被掛在椽子上,或被安裝在牆上。我被一個很薄的木碗所吸引,碗身經過拋光後,看起來很像瓷器。安斯佩爾笑著對我說:“這個碗名叫‘功能性的邊緣’。”說著,他把碗穩穩地放在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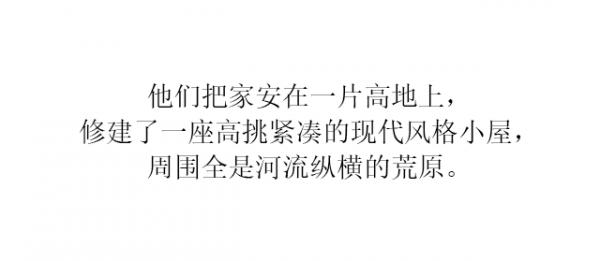
但今天,我的終極目的地是位於小鎮以西的蘇馬國家公園(Soomaa National Park),還計劃好要在園內尋覓不尋常的地方過夜。雷內·瓦爾納(Rene Valner)和瑪麗爾·尤西(Mariell Jussi)在公園裡提供名為“Karuskose”的獨木舟和皮划艇體驗服務。他們把家安在一片高地上,修建了一座高挑緊湊的現代風格小屋,周圍全是河流縱橫的荒原。訪客可以像我一樣在那裡留宿,而每當發大水時,也可作為一個備用的避難所。這座公園是熊、狼和各種鳥類的家園,但特別的是,園內經常會受到洪水的侵襲。洪水來襲時,這對夫婦家的底層會變成一座小湖。若遇上隆冬時節,則會變成一座溜冰場。我穿過搖搖晃晃的繩橋來到他們家,發現樓身半腰處標有一條藍線,記錄著他們所見過的最高洪水水位。不過,這些險情似乎都未能困擾這對夫婦。

蘇馬國家公園位於維爾揚迪西邊,遊客有機會在寧靜的傍晚時分去河上划船。
瓦爾納邀我去河上划了一會兒獨木舟,大約20分鐘後,我們遇到了公園裡著名的“漂浮桑拿”(floating sauna)——這是愛沙尼亞藝術學院的學生創作的暑期專案。學生們在簡易木船上用桑拿房代替了客艙,整艘船可隨波漂浮,任何發現它的人都能免費使用。隨後,尤西建議我騎腳踏車沿小路到不遠處的泥炭沼澤地探險。我穿過鬆樹林,騎上了一座小山坡,發現獨自置身於呼嘯風聲中。面前是廣闊無垠的平原,上面有一些零星小水池和大樹。我順著小木道來到一個藍色的小觀景臺,想著這裡應該是唯一有人類出沒的地方。這一片原始風光,和佛羅里達州大沼澤地的部分割槽域非常相似。
當晚,我們回到Karuskose嘗試了本地傳統的煙燻桑拿。這是一天的尾聲,也為我的愛沙尼亞之行畫上了句號。這種桑拿與普通的不太一樣,它由明火加熱,但沒有煙囪,這意味著房間裡會煙霧瀰漫。人們入屋前,他們會讓煙霧先散出來。整個體驗過程很簡單:進屋坐一會兒,然後出來把沾滿煙塵的身體浸入河裡,喝點啤酒,接著再不斷重複這套流程。我們站在戶外,迎面吹來一陣涼風,而此時,我還看到了一對大鳥。定睛一看原來是鶴,它們在落地後發出幾聲響亮的尖叫聲,在田野上不停迴盪。
兩位主人說,煙霧可以淨化空氣。好好在煙霧桑拿房裡待上一會兒,可以洗滌你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