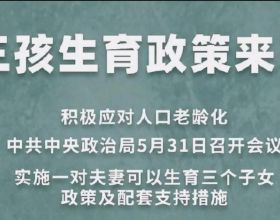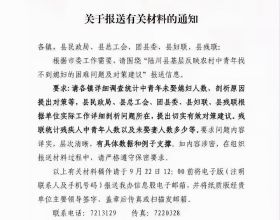小敏
每位在西藏當過兵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是青春的回憶,那是熱血男兒的風采!他們是平凡的人,他們是父母的孩子,他們的存在是我們的安全感。他們的每一天我們難以想象,然而,他們將所有的熱愛撒向生命禁區以及邊關界碑。
我認識一位一級軍士長,40多歲,在高原已經24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地方,在路上,在路上,似乎他一直在路上,戰車是他最親密的伴侶,他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獻給了它,陪伴戰車的日子比陪伴愛人的時間還長,還多。戰車轟鳴,老兵就精神抖擻,似乎戰車就是他命中註定的緣!
一雙手不知脫過多少層皮,也不知寫下了多少本技術資料,最高光時刻,駕駛他的基準車帶隊完美透過天安門,老兵說:“沒感覺多麼激動,就是完成了自己應該完成的任務。”24年奔波,日以繼夜的攻關,已經讓他的身體達到了極限,身體狀況並不好,可是他依然選擇留在了雪域高原。他說,他要繼續當個好兵!
一位西藏老兵有很嚴重的痛風,最嚴重的時候只能坐輪椅。每次疼痛起來都很要命,但他只要稍微有點好轉,馬上就坐不住,他說他閒不住,他喜歡走在高原冰山上的感覺,他更喜歡在高原上挑戰極限,走到哪裡,哪裡都是他熱愛的風景。
20多年的軍旅,想家,想念孩子,也想念愛人,每次孩子在電話裡喊爸爸是他最脆弱的時候,忍不住流下男兒淚。可是工作總要有人做啊,抱著這樣的想法,堅持了一年又一年,其中的酸甜苦辣,都成為了肩章上的責任。
記得有一次,我問一位從河北入伍西藏的老兵,他今年應該40多歲了吧,我問他:“今年找物件嗎?給我買喜糖吃啊,”他說:“糖可以給你買,但是物件今年不考慮。”我說:“你父母不催你啊,那麼大了,”他說:“以前經常催,但是現在不管了,我真的身不由己。”一句身不由己,莫名感覺酸酸的,澀澀的。
有一次他告訴我:“我要去邊境了,你再祝福我一次吧,怎麼滴也得祝福我平安歸隊啊!”聽到這句話,我居然都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我不知道那是怎樣的境遇,我只知道那一路不會好走。所以我經常愛說:“祝福西藏,祝福你,”這是我最真心的話,是我想說一輩子的話。
西藏軍人特有的標籤,是高原紅,還有高原病,我認識的西藏老兵或多或少的都有高原病,而老兵們告訴我,他們的很多位戰友都因為高原病過早的離開了這個世界,而高原病對人體的傷害是長久的,無法修復的。
清楚地記得一位退役老兵朋友圈的一段話,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又走一位,都是英年早逝,都是西藏退役軍人,生命如此脆弱,只因高原環境下十多年、幾十年的奉獻,那裡被世人稱為天堂,但願從天堂回來的戰友們在人間的時間延長一些,只為沉重的家庭責任!
都說艱苦的地方鍛鍊人,磨礪人。那建在雪山尖上的邊防哨所,四周都是垂直的懸崖峭壁,每年大雪封山八個月,用水靠天,物資靠背,是哨所官兵們生活真實寫照。這裡一年只有雪季和雨季,六級以上大風300天,連鳥都飛不過,草都不長,因此稱為“雲中哨所。”那是多少人夢都夢不到的地方,可一代代官兵駐守在那裡無怨無悔。
而在崗巴邊防營,查果拉塔克遜等哨所均構築在海拔4870--5300米,空氣含氧量不足內地40%,年平均氣溫-4攝氏度,最低氣溫-40度,每年有200多天刮8級以上大風,動植物都無法存活。在這樣的地方,躺著就是奉獻,可是崗巴營的同志們硬是在生命禁區唱響嘹亮的崗巴營之歌,成為響噹噹的戍邊模範英雄連。
高原軍人有一句口頭禪:“髮際線在一寸一寸地往上移,但是我一定會守好祖國的邊防線。”一位年輕的西藏軍人瞞著父母走向了洞朗,這一去,就徹底地失去了聯絡。而沒有訊息的父母每天都像熱鍋上的螞蟻,只能固執地相信,沒有訊息就是最好的訊息。
而當他迴歸給父母報平安時,卻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淚水,那是虧欠,亦是聽到父母聲音的情不自禁。我說:“你害怕嗎?”他說:“真沒什麼可怕的,反正總要有人去。”說得那麼雲淡風輕,我聽的百感交集。
很多時候我在想,邊關一定有永不褪色的色彩,那迷彩青春,熱血軍人,都是最美的啊。西藏海拔高,而西藏軍人的使命更高;他們站立在國門,他們就是移動的界碑。他們的青春與壯志那麼親密的和祖國聯絡在一起。
無論今天多麼日新月異,還有很多人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負重前行,而他們的故事正是國家記憶裡最深重的一部分,他們選擇到那裡,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他們沒想太多,他們只想把屬於祖國的國土守好。
千里熱血邊關,遍地英雄屹立。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裡的高山流水都以同樣的善意圓滿著千年的寓言,而我們不應該忘記,在我們愉快地生活和工作背後,那些在邊關,在哨位,為我們抵擋黑暗的人,是他們,才有這盛世繁華,是他們,才有我們從容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