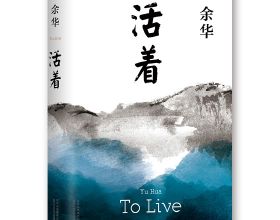“打仗太驚險了,每一天都驚險。槍炮一響,你都不知道你今天能不能活下來。”說起抗美援朝那一段戰爭歲月,這名老戰士身形筆直,絲毫沒有佝僂。
他叫鄧長會,今年86歲,他曾是中國人民志願軍11軍33師99團的一名通訊兵。“通訊兵是首長的千里眼、順風耳,在打仗的時候,通訊不能斷,要隨時給首長傳遞資訊,還要傳達首長的指示。”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鄧長會多次冒著炮火接通被敵軍炸斷的電話線,最終英勇負傷,雙眼致盲。
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1週年之際,鄧長會向記者回憶起過去的崢嶸歲月,他臉上的神情時而堅毅,時而激動,時而悲傷,時而自豪。
在講述完自己的戰場經歷後,鄧長會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指著面前的攝像機問:“你們這個是要播新聞出去嗎?”在得到記者的肯定答覆後,鄧長會清了清嗓子,正襟危坐,對著攝像機說:“我還有個哥哥,叫做鄧長義,他也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在戰場上聯絡不上了,至今還是失蹤人員。”他頓了頓,“如果有人聽過他的訊息,可以通知我,再遠,我都會把哥哥接回來。”
多次冒著槍林彈雨接通電話線
遭到敵軍毒氣彈襲擊後雙目失明
1952年冬天,來自四川廣元的鄧長會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作為一名通訊兵,上傳下達是他的主要工作。那時的他揹著電話線,掛著電話機,架設團指揮所到前線部隊的通訊線路,“如果炮彈把電話線炸斷了一截,我們還要及時去接通,半點耽誤不得。”鄧長會說,“戰場上通訊不能斷,打仗就是要搶每分每秒,前面的離開了指揮就不行。”
說起自己遭遇的最驚險時刻,鄧長會情緒有些激動:“當時我們在一個被稱作‘老鷹嘴’的地方,離上甘嶺不遠。當時前方的電話線被炮彈炸斷了,我和戰友要透過敵人的封鎖區去把線接起來。”鄧長會說,敵人不斷用機槍掃射封鎖區,他們只能先埋伏,等到敵軍的子彈耗盡,換子彈的空隙,拼命跑過去,“跑慢了就要挨槍子,當時就是什麼都不敢想一直衝。和我一起的戰友就跑慢了,腿被子彈打斷了。”
跑過封鎖區的鄧長會最終將電話線接好,成功傳達了指示。“當時其實什麼都沒想,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敵人的子彈會不會打中你,敵人飛機丟的炮彈會不會炸死你,你能做的就是往前衝,保證完成任務。”就這樣,鄧長會多次在槍林彈雨中接通電話線,保障了通訊暢通。
意外發生在1953年5月,鄧長會在一次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遭到敵軍毒氣彈襲擊,雙目失明。“一陣煙之後,有人嗆得說不出話來,有人眼睛看不到。我就是當時看不到了,透過治療好轉了一陣子,後面又復發,就失明瞭。”
停戰歸國後,失明的鄧長會來到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如今的他,說起過去的故事並沒有傷感,也並不為自己失去光明而哀嘆,反而是為在戰場上保障通訊暢通而自豪。“我完成了交給我的任務,這是軍人最大的光榮。”
三兄弟一起上戰場
二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失蹤
在戰場上圓滿完成任務的鄧長會說,自己在戰場上沒有遺憾,但在戰場下卻有一個遺憾。“我想知道我二哥的訊息,哪怕是遺骨,我也想知道他在哪。”
鄧長會一共有5個兄弟姐妹,其中有三兄弟都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二哥鄧長義,三哥鄧長禮,我是最小的。他們倆在1951年就到了朝鮮,我是1952年底才去的。”在戰場上的三兄弟未曾見面,只通過書信往來,“後來寄給二哥的信就沒有迴音了,失去聯絡了。我當時心裡就想,糟了。”
回國後的鄧長會和三哥重聚,卻始終沒有二哥的訊息。“三哥積勞成疾,1967年因病去世了。”鄧長會說,這些年來,他和三哥一直都想聽到二哥的訊息,但三哥在去世前也沒能實現這個心願,“二哥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失蹤人員,我們只知道他的信箱,知道他是偵察連的偵察兵,具體是哪個部隊的也不知道。”
說到這裡,鄧長會語氣有些哽咽,“我們連也有幾個失蹤的戰友,大家都把他的衣服、帽子等物資保管起來,給他們的家人留個念想。但我和二哥不在一個部隊,也不知道他的物資有沒有人保管,有沒有東西可以給我留個念想。”
說到這裡,坐在鄧長會旁的老伴也點點頭:“這麼多年來,每次有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回國的新聞,他都會開啟收音機仔仔細細地聽,看能不能聽到他二哥的名字。”他老伴說,其實鄧長會心裡也清楚,這些烈士遺骸裡多半沒有二哥,“他二哥應該是在朝鮮戰場上,沒有到過韓國。”
鄧長會聽聞此言,嘆了口氣,接過話頭:“我心裡清楚,但是我總是想,萬一呢,萬一就有二哥呢。”鄧長會說,“我在收音機裡聽到,有人透過歸國遺骸認親了,每次聽到這些新聞,我都在想,下一個會不會是我二哥。”
採訪的最後,鄧長會仍然坐得筆直,儘管他看不見,但他仍然對著眼前的攝像機,似乎想和屏幕後的人交流:“我二哥叫鄧長義,我現在仍然期待有一天可以聽到他的訊息。如果可以,我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領回家鄉,將他安葬。”
紅星新聞記者 彭驚 攝影記者 呂國應
編輯 官莉
(下載紅星新聞,報料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