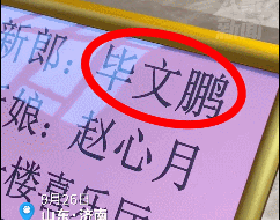被稱為死亡工程的虎頭要塞
九一八事變後,我國東北大部分地區淪為日本殖民地。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繼而染指蘇聯,日軍在我國境沿線的山隘要地大修營壘工事、軍事基地和軍用公路。修築如此大規模的軍事工程,每年都要投入幾十萬勞工。
七七事變以前,勞工主要由日偽當局透過抓捕青壯年、強徵偽滿報國隊、誘招關內農民等手段招集來的。侵華戰爭全面鋪開之後,大量戰俘被從各地押運到東北,成為修築軍事工事的“特殊工人”。
虎頭要塞, 就是日軍動用了10餘萬中國勞工,歷時6年,耗資數億元修築的。
位於完達山餘脈的虎頭鎮是黑龍江省虎林市的一個邊陲小鎮,地方雖然不大,卻有著相當重要的戰略位置。這裡是我國東北邊境最容易登陸的地帶,隔江相對的伊曼市就是蘇聯遠東最大的軍事要衝。日軍侵佔東北後,即將此視為軍事要地,駐紮重兵嚴防蘇軍進入,並秘密修建大規模的地下要塞,企圖使之成為進攻蘇聯的橋頭堡。
由於虎頭要塞的分佈範圍廣、工事規模龐大、軍事設施齊全、結構複雜、防禦堅固、攻擊力強,被日軍吹噓為“永久要塞”和“東方的馬其諾防線”
在機械化程度相當低下的情況下,在嚴寒與崇山峻嶺中修築工事,是極其危險的事情。勞工們除了被惡劣的環境折磨致死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被日軍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可以說,要塞就是用中國同胞的白骨堆積出來的。
施工是在對外嚴密封鎖訊息的情況下進行的。
要塞邊緣有日軍用紅色油漆畫出的警戒線,警戒線附近的路口都有持槍日軍士兵把守,無論是裡邊的人往外逃,還是外邊的人誤入進到裡邊,只要被抓住就別想活命。
勞工們悲慘的生活
李來慶和高保生既是抗日戰場上的戰友,又是同一批被俘進入濟南新華院戰俘集中營的難友,在新華院艱難的度過了幾個月的時間,他們又被日本兵押上火車,送往虎頭鎮。幾個月度日如年的受虐生活,大家被折磨得體質已大不如前。
他們哪裡能想得到,前腳出的是狼窩,後腳進的是虎口。
大鐵櫃似的火車車廂內擁擠不堪、昏暗無比,上百人擠在一節車廂裡,吃喝拉撒睡全在裡面,空氣汙濁可想而知。
戰火硝煙中火車走得很慢,走走停停,車門一直沒有開啟過。小小的車窗早已被釘死了,只有車門的縫隙處能吹進縷縷清風,人們就輪流扒著門縫呼吸幾口新鮮空氣。
雖然每人發了幾個發黴的窩頭路上吃,可是沒有水喝,肚子餓得咕咕叫,窩頭卻噎在嗓子眼裡咽不下去。人們不但缺水,還缺氧,乾渴,憋悶,嘴唇乾裂了,眼窩塌陷了,臉色煞白看不出一絲血色。
幾天之後,情況變得越來越糟,有的人昏厥過去,有的人變得狂躁起來,喉嚨沙啞地胡言亂語著。身體本就虛弱的幾個人實在撐不下去,一個個悄無聲息地撒手人寰了。
活人可以坐著,死人只能躺著,為了給死去的難友騰出地方,人們只好更緊湊地擠在一起。 車廂的那邊是並排停放的幾具屍體,這邊是瀕臨死亡的活人。
昏昏沉沉地不知熬過了多少天,車門終於打開了,明亮的陽光晃得人們好一陣子睜不開眼。 拖著腫脹麻木的雙腿跳下車,只覺得風硬硬的,吹在身上有種刺骨的寒意。
李來慶俯在高寶生耳旁悄悄地說:“看來我們這是到了關外。”
在這裡,他們又被轉送到大卡車上。
大卡車在山路上繞來繞去地顛簸著,最後把他們送到了一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的地方。 山坡上除了一排排簡易的大工棚外,就是數不清的鐵絲網和崗樓。
到這裡的人都被颳去了右邊的眉毛,有了這樣明顯的記號,即便逃出去也會很快就被抓回來。
沒過幾天,大家就發現這裡的狀況一點也不比新華院集中營好。二百多人住在一個四面透風的大工棚裡,吃的不是發黴的高粱米飯,就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窩頭,沒有菜,只有鹹鹽豆和清湯,一年四季都是喝生水,鬧肚子是常事。
在我國境內,虎頭鎮是每天迎來第一縷陽光的地方,通常早晨四點鐘天就亮了。可是就在這太陽昇起最早的地方,“特殊工人”們卻難得見到陽光。
每天天還不亮,手執木棒的監工就將大家轟起來去上工,誰的動作稍微慢一點,木棒就掄到身上了。開山挖洞打洋灰都是高強度的體力活,從清晨開始一直要幹到晚上九點才收工。
來回的路上人們的眼睛都要被蒙起來,許多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身處哪裡,乾的是什麼工程。
正值冬季,氣溫在零下三十多攝氏度,山洞裡更是陰冷潮溼。一套麻袋片般的單衣如何能夠抵禦北國的風霜。大家只好就地取材,將水泥袋拆開挖個洞套在身上,再用草繩捆住,雙腿也用水泥袋一層層地裹上,紙袋雖然起不到保暖的作用,但多少可以擋住一點寒氣。
在皮鞭、棍棒、洋刀的威逼下,人們只有強咬著牙日復一日地幹著。
身上沒有禦寒的棉服,肚裡缺少產生熱量的食物,飢寒交迫且勞累不堪,嚴重的營養不良導致各臟器幾近衰竭,疾病、飢餓、寒冷、勞累都是致命的殺手,有的人幹著活就一頭栽倒再也起不來了,有的人則在睡夢中悄悄告別了這苦難的人生。
最兇殘的殺手當然非日本人莫屬,隨時都有可能剝奪勞工的生命。土建工程中最重的活兒就是打洋灰,人到中年的張繼德已經連續打了好幾天,虎口被震得又紅又腫。
這天下午,他實在太累了,剛直起腰來喘口氣,不巧被巡視到此的日本監工逮個正著。他氣勢洶洶地走過來,二話沒說抽出長長的東洋刀,衝著張繼德的頭用力砍了過去。
猝不及防的張繼德身子晃了晃,“撲通”一聲倒在地上,一個無辜的受難者,就這樣轉瞬之間成了刀下鬼。
殺人不眨眼的監工用腳踢著地上的屍體,惡狠狠地威脅眾人道:“誰要再敢偷懶,就像他一樣死啦死啦的有!”
在侵略者眼中,中國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殺個人就如同捻死一隻螞蟻,根本算不上什麼大事。
身體在虛弱也不敢去的“病號房”
在這裡一連數日的腹瀉將高寶生折磨得都脫了形,渾身沒有一點力氣,兩條腿更是軟軟的,走起路來就像踩著棉花似的。吃早飯時,李來慶見他的臉蠟黃蠟黃的,怕他幹活兒時撐不住,就勸道:“你病成這樣怎麼幹得了活,乾脆別去了,我給你請個病假,睡一天緩緩興許能好點。”
高寶生有氣無力地說:“不用了,我能堅持,真要被送去病號房可就慘了。”
李來慶稍加思索又說:“這樣吧,幹活時你跟在我身後,監工不在身邊時你就歇會兒,我給你打掩護。”
這裡的“病號房”與新華院的“病棟”如出一轍,一個蓆棚裡住著500多病號,不但病得不到醫治, 還每天只給一碗能照見人影的高粱米稀湯,幾天下來病不死也餓死了。因此,但凡能拿得動鐵鍬的,誰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病號。
每天早晨,看守都要到病號房來檢查一遍, 檢查的方法很簡單,把躺著的人逐個用腳踢一遍, 凡僵硬不動的便是斷了氣的。每天從這裡拖出去的屍體至少三四具,多時能有七八具。
活著得不到溫飽的人們,死後也得不到安葬,不是被拋入草甸子裡,就是被丟棄於荒山野林中,任由野狗餓狼撕咬啃噬。
源源不斷的屍體,招致大批的餓狼聚集於此。每到夜晚,此起彼伏的號叫聲讓人毛骨悚然。這些狼甚至等不到天黑,就成群結隊肆無忌憚地跑來。野狗更是吃人吃紅了眼,甚至一見到單獨行走的人就往上撲,一直追出去老遠才罷休。
九死一生,逃出魔掌
工程接近完工,日軍開始有計劃地分批屠殺“人證”,不僅“特殊工人”,就連普通勞工也難逃厄運。儘管劊子手自以為做得非常隱蔽,但是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眼見身邊的人一天天地在減少,人們開始有所警覺了。
這天,李來慶悄悄與高寶生商量:“我看這情況有點不對勁,與其等死不如試著逃跑,也許還有機會!”
“早晚是個死,乾脆試它一把。”高寶生激動地說道。
他們又串聯了幾個人,大家商定明天一早就行動,上工的路上瞅準機會一起往冰封的江面上衝。
第二天上工,趁著天還不亮,李來慶悄悄扯下矇眼布,快走到江邊時大聲咳嗽了兩聲。聽到約好的訊號,十幾個人一起扯掉了矇眼布,撒腿就朝江面跑去。他們跑出一段路後, 幾個日本兵才反應過來,急忙端起槍來射擊。子彈嗖嗖地飛過來,不時有人倒下,其他的人不敢停下來,只能更加拼命地往前跑。因為大家知道即便停下來,也救不了倒下的同伴,只能是白白送死。
這次有六個人成功地逃到了對岸的蘇聯,其中就有高寶生。有幾個人死在了烏蘇里江的冰面上,李來慶和另一個難友受了傷, 被日本人抓回去慘遭殺害。
工程竣工後殺人滅口
不久,要塞工程全部完成,日軍舉行竣工宴會,將所有戰俘和勞工都集中在猛虎山西麓一處叫猛虎谷的窪地裡,說是“皇軍要舉行完工酒宴,好好犒勞大家”。
有幾個人感覺到有些不妙,懷疑鬼子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就想方設法躲進工棚不出來,結果硬是被搜出來強拉至現場。
會餐進行中,突然幾挺重機槍從不同方向衝著人群掃射。一些人倒下了,其餘的人驚恐地丟下碗筷四下逃散。然而東奔西跑,人們怎麼也衝不出火力圈,很快就紛紛被擊倒在地,死的死,傷的傷。宴會場變成血腥的屠殺場,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為了掩蓋這斬盡殺絕的罪惡,日本守備隊動用了大量的人力,以最快的速度將窪地填平,消除了所有的痕跡。
究竟有多少中國同胞被強制從事修築虎頭要塞,又有多少被折磨致死或被集體槍殺,由於這一切都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很難得出準確的數字。但根據後來多方調查,人員至少在10萬人以上。
這樣的“死亡工程”並非虎頭要塞專屬,漠河棲林集的秘密軍事陣地,呼瑪縣河南屯的盤旋地道,哈爾濱平房細菌研究中心的主體建築等,這一系列軍事工程在竣工後無一例外地都是集體屠殺。 只不過屠殺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用機槍射、有的用毒氣燻、有的被活埋于山間、有的則被沉入到江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日軍吹噓為“東方馬其諾”的虎頭工事,成了這些侵略者的最後墳墓。經過17天的激烈戰鬥,蘇聯紅軍摧毀了這座“永久要塞”,全殲盤踞於此的日本守備軍,使這裡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