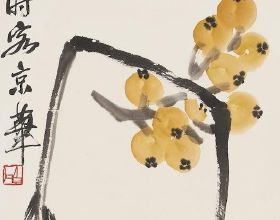文/韓府
兩三天前,與東旺的愛人約好,週三我們幾位好友一起到新開放的大同美術館看東旺的畫展《時代肖像》,今天上午,我們如約相會,榮幸地隨東旺的愛人張宏芳女士親近了展廳中的每一幅畫作。
第一次知道東旺是在畫家王金鐘案上的一冊書裡,我不但看到了那逼真得讓人驚訝的大白菜,而且看到了無數讓我震撼的面孔,看到了許許多多讓我一見難忘的手——有生命的活著的手……今天,我提早來了半個小時,剛走進大廳,還遠在幾百米之外,東旺肖像身邊的那四五張臉孔就撲面而來,這哪裡是畫?完全就是活生生的人!因為來早了,我就獨自先把東旺畫作的整個展廳巡視了一遍,待宏芳女士帶我們參觀的時候,我正好把自己之前的解讀做一個印證。十分欣慰的是,我真得讀懂了東旺:那個小手胖嘟嘟的男孩兒就是他們的兒子,那個文靜可愛的女孩就是他們的女兒,那個胸前圍了個綠頭巾的長髮小夥子果然就是一個心中藏了藝術夢的農民的兒子,更不用說那個嘴角、眉梢流露出幾分威嚴的老者就是宏芳的父親、東旺的丈人。我自以為讀懂了東旺,所以,從一開始我就像對一位老同學、熟朋友一樣,直呼他的名字,而不是稱他為大師、先生或教授,我覺得他就是與我心心相印的一位熟透了的好友,就是我的一位好哥們兒,那麼熟悉,無須客套。我們只需一個眼神就能會心,甚至從一開始就是莫逆的。這不是狂妄,也不是高攀。
白菜 60X50CM 布面油畫 2006年
區域性
忻東旺作品《少年》
每個人都有解讀東旺畫作的權力。
但讀出的內容則必然彼此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然而這都無妨,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原作太豐富了,而我們開掘提煉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每個人心中都可以有一個忻東旺。
一邊走,一邊聽宏芳老師向我們介紹東旺,介紹每一幅畫的背景,介紹畫中人物的身份和境遇。面前這位端莊優雅的女主人,她的語氣是那樣的平和,表情是那樣的平靜,這太好了,正是我所期待的感覺,我不希望看到她的哽咽乃至淚水,因為我一直覺得東旺並沒有離開,他就在我們身邊靜靜地注視著,每當我們讀懂了讀對了,他的眉宇間就會漾出不易察覺的喜悅。
和當年讀畫冊時一樣,這次我依然注意到,東旺的畫第一打動我的是人物的臉,無論是清澈抑或渾濁的眼睛,還是沒有剃乾淨的幾根白鬍子茬兒,甚至只是一個斑,都讓我覺得它們是一個生命體上的一部分,即它們是活的。第二讓我驚歎的是他把人物的手畫得那樣精準傳神,歷來有畫諺說“畫人難畫手”,東旺筆下的手絕對是人的第二張臉,那上面滿載著人物的全部資訊,他的閱歷、他的身份、他的審美、他的愛好、他的體力,他的一切——那手是有表情有語言的。不必說那些突起的青筋、粗糙的老繭、陳年的傷疤、老年斑,只是一瓣指甲,厚的、薄的、精心修過的、有意留長的、潔白無瑕的、深藏黑垢的……就能那樣精準地傳達出豐富的資訊。
除了為數不多的幾幅靜物,比如梨和著名的大白菜外,佔絕對多數的還是人物。我以為,東旺最關心的是人,是身邊活生生的人,尤其是下層民眾,又尤其是農民。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於是便有了筆下的農民、農民工、小賣部老闆、闖世界的青年、穿了制服的保安,也有了他們身邊的菸蒂、地下的炒鍋、睡衣上的鑰匙鏈、大拇指甲裡面的黑垢……被他定格在一瞬間的畫作背後是一段或長或短的生命履歷和千差萬別的生活瑣屑。東旺的畫有進深,有厚度,有份量,有千滋百味,畫只是通向一段生命歷程的一個入口,他畫的是生命,是生活,是人物的命運和際遇,在畫面的後面竟然是一個黑洞般廣大深邃的世界……東旺的畫之所以打動人,除了藝術手段的高超外,更主要的在於他讀懂了人物的內心,讀懂了他筆下人物的心靈路程:他們經歷的困苦、磨難、屈辱、無奈。正如畫家本人在《父子》一畫的說明文字中所說:“畫村裡的人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就是他們每個人的任何表情資訊我都可能捕捉得到,而且是心領神會。”
展廳入口 郝昆峰 攝
於是,表面上看,他和別的畫家一樣,定格了人物的某個瞬間,但事實上,別人畫上的人物和畫板一樣是扁平的一塊相。而東旺的畫則不同,他的畫是立體的,有縱深,有厚度;他的畫有味道的,柴米油鹽的味道無不充斥其中;他的畫有聲音的,人物心底的嘆息、哀怨、牢騷、吶喊,無奈……瀰漫其間。作為一位藝術天才,東旺的神經一定是超級敏感的,他能從火車站湧動的民工潮預感到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的每幅畫無不是那個時代的忠實記錄,所以,這次展覽名稱定得非常好,《時代肖像——忻東旺藝術作品展》。是的,他的畫是那個時代的記錄,他在第一時間敏捷地記錄了那個時代。對時代的記錄他也依然著眼在人物,在畫室裡,在街頭上,在蒼蠅店裡,在火車站廣場上,東旺發現了他們,並且讀出了他們的心路和命運。在《身份——賣畫布的老李》一畫的說明文字中,東旺點破了:“雖說笑是令人愉快的,但老李的笑容卻充滿了酸楚。”相隔幾十年後,我以為我也讀懂了:我面對的不是一張塗了油彩的薄薄的紙,而是一段沉甸甸的充滿艱辛、不乏苦澀和辛酸,偶爾也會有幾分甜蜜的人生;是活生生的境遇,是起伏不定、難於駕馭、無從預卜的前途,是經過努力和抗爭而最終不得不屈從的命運;是經歷了這樣人生和擁有這般命運的人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緊張、他們膽怯、他們的惶恐、他們的希冀、他們的自負、他們的得意、他們的傲慢,無一不從他們的眼睛、嘴唇、額頭委委曲曲地傳達出來。至於東旺為什麼關注這些,為什麼能準確地捕捉並讀懂他們,那是因為他曾經就生活在這些人中間,或者說他就是他們中的一員,更準確地說,他是從他們中間走出來的,所以,他能淪肌浹髓地感受他們的感受,他的脈搏與他們同步,他的神經與他們相通,這位天才畫家與模特之間進行的是“血緣般的心理交流”。更為難得的是,東旺不僅僅只是描繪和記錄,他的筆下有一種濃濃的“同情”,所以,王藝在《詩性的肖像》一文中用了五個“悲天憫人”。東旺的肖像畫之所以能那樣打動,是因為其中傾注了他的真情。——我總以為,東旺的早逝,絕不僅是體力的消耗,而更是心力的枯竭,他是以菩薩般的大慈悲心去畫眾生。宏芳說:“在他心裡眼裡,萬物有情。”這不是菩薩是什麼?
不錯,東旺的畫作透過他捕捉的人物的一個瞬間,深刻而準確地銘刻下那個時代。與此同時,東旺和他的畫一起,嵌入了那段歷史中,他和它們成了那段歷史最忠實最深刻的記錄者。美術史,甚至整個藝術史也因此為他留下一席之地。在那個時間段裡,他無可替代,沒有了他和他的畫作,雖然不能說那段歷史就成了一段空白,至少也會蒼白、黯淡、沉寂許多,而現在因為東旺的畫,那段歷史成了有聲有色有血有肉的鮮活生命。
看過最後幾幅素描,宏芳女士的講解就基本結束了,然而,我覺得一切都依然在進行之中,畫上人物的呼吸清晰可聞,他們口中的大蒜和菸草的味道也同樣清晰可聞,東旺淡淡的微笑就像和煦的陽光一樣依然籠罩著我們。我知道,這就是藝術的力量,畫家不在了,他的畫中的人、物竟然全活著,而且有著超越時空的生命力,他們穿過歲月的長河涌動在我們身邊……藝術的生命是這樣的長久,藝術家的生命於是也被無限延長,與他的作品同在。
那天下午,我們幾個人:藝術評論家馮海、著名朗誦家孫嶽,還有成績斐然的書法家趙雁鴻,再次來到展廳,原打算把上午沒有來得及參觀的另外的作品看一遍,然而事實上我們只是來了一個走馬觀花……真得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其他藝術家與東旺同時開展。能同時、同廳,這一定有某種難得的緣;但說實話,東旺的光太強了,他宛如太陽一般讓別人都變成了星星,白日裡的星星。
走出展廳的時候,我心中忍不住想對大同父老們說幾句,我想告訴大家:東旺回來了,他在美術館等著我們!
記得,你一定要去看忻東旺。
9/9/2021 4:50:39 PM草畢於文瀛湖東畔市委黨校南樓209室
9/10/2021 5:13:15 AM改定於幸福裡舊電腦上
9/30/2021 5:28:52 PM再改文瀛湖東畔市委黨校南樓209室
韓 府
大同著名人文學者、資深教授。在校期間學習自然科學,就業後既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又出入儒釋道三教。多年來致力於匯通各科知識,自備爐錘,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融於一爐,打成一片。讀書從無軫域,可稱旁學雜收、泛覽無涯,故而對讀書人而言是一位難得的良師益友。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現已出版《咀嚼人生》《韓府學術論叢》《耍孩兒劇種源流考》《鄧雲鄉傳》《大同方言古語考釋》等著作12種。
部分圖片來源:拓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