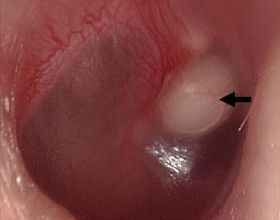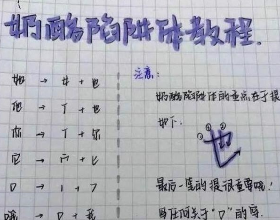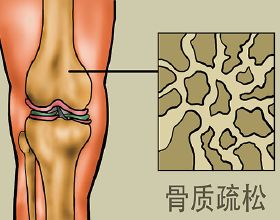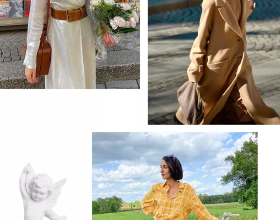中西文化比較,特別是中西哲學比較,是當代中國學術的重要課題,也是將來至少一百年內不可迴避的話題。然而,至今為止,仍然有不少人把握不住中西比較的宗旨,不明白比較的目的不在於爭意氣,而在於透過比較促使中華文化開拓視野、認清形勢、制定切實的發展規劃。中西比較不是要比出雙方的優劣,而是要在比較中找出自己文化的欠缺,以求改進。
我認為,在一般意義上,歷史有進步,文化無優劣。然而,文化雖然無優質文化和劣質文化之分,但在每一具體的歷史時期,一種文化總會表現出自己的優勢和劣勢,因而必須承認有優勢文化和劣勢文化之別,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此時劣勢文化如果不吸收優勢文化的長處,努力趕上時代的步伐,就會越來越落後,乃至被淘汰。
所以,劣勢文化不等於劣等文化。那些滅亡了的文明,如埃及、瑪雅文明,以及那些至今還處於絕對劣勢的文明,如澳洲或非洲土著的文明,也不是劣等文明,更不用說今天處於相對劣勢的中華文明瞭。[1]但在一個文化競爭的時代,如果不看清人類文明的走向,如果劣勢文化不努力向優勢文化學習,那麼歷史不會因為你的文明仍然具有多種優良素質而手下留情,讓你僥倖逃脫被淘汰的命運。
一個民族的文化最深層次的秘密可以從這個民族的哲學思想中尋求答案。在這裡,我想從哲學上闡明,西方文化近一百多年來成為了全球強勢文化,其根源何在?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這就必須在對比中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即西方哲學所體現出來的思維模式。
一、愛智慧論
“哲學”這個概念來自西方,在古希臘,它意味著“愛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對智慧本身的追求和熱愛,將智慧本身視為高於一切其他目的的神聖目的。所以當年日本人最初譯這個詞為“愛知”,後來才從古漢語中拈出一個“哲”字,改譯作“哲學”,意思是“智慧之學”,這就是今天我們中國人習慣上所用的譯名。雖然後來日本又有人把這個譯名改了回去,但中國人一直沒有跟著改過來,我們覺得“哲學”這個詞用得很順手,也很容易理解。
但把“愛智慧”譯作“哲學”(智慧之學),這一譯法實際上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錯位。因為數千年來,中國哲學有“智慧”,但一直沒有“愛智慧”,有“智慧之學”,而沒有“愛智慧之學”。
前幾年國內學界爭論得轟轟烈烈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在我看來完全是一個假問題。當德里達說中國沒有“哲學(philosophie)”時,他講的“哲學”和漢語語境中的“哲學”講的並不是一回事。但我們國內學人卻連他的意思都沒有搞清楚,就一轟而起,紛紛指責他的“西方中心論”。
其實,中國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這要看你怎麼理解“哲學”這個詞。如果理解為“愛智慧”,則中國從來沒有過,今天也沒有。中國人自古以來從來沒有因為對智慧本身的熱愛而研究智慧的,總是為了別的目的,如解脫煩惱,長生久視,如治國平天下,如協調人際關係。
然而,如果把“哲學”按我們通常那樣理解為“智慧之學”,中國當然自古就有了,今天也還有的是,甚至是鋪天蓋地,“從娃娃抓起”。廣告詞裡面天天唸叨“道可道”,于丹講《論語》、講《莊子》,兒童讀經,都屬於此列。這些智慧之學是要叫人“受用終身”,但不是叫人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秘密,有所創造有所發明。老百姓學了“智慧之學”可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數”、養生,當官的學了可以青雲直上、穩座江山,企業家、軍事家學了可以運籌帷幄、決勝商(戰)場。
與此不同的是,西方哲學從一開始就有一種不計功利、只求興趣的傾向。古希臘泰勒斯為觀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遭到他的女奴的嘲笑;但他一旦把觀察天象的知識用於預測橄欖油豐收,就發了大財。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古希臘哲人明明知道知識的用處,懂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道理,卻並不看重這種用處。
赫拉克利特為研究哲學而放棄王位,最後餓死在牛欄;畢達哥拉斯發現了勾股定律,舉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謨克利特說,發現一個事物的原因比當波斯人的王還好;柏拉圖的學園中,有人問學這些知識有什麼用,柏拉圖用一個銀幣打發他開路。亞里士多德總結道:哲學起源於“驚異”。
驚異是一種超功利的興趣,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它所激發的是一種純粹的“愛”的追求。什麼是“愛”?這是一種生命力的衝動,是生命對精神生活的一種向上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的就是這樣一種“愛”,缺乏對純粹精神性的追求,只關心肉體(或與肉體不分的精神),而不關心純粹精神。所以魯迅曾把中國社會形容為一個“無愛的人間”。
而亞里士多德把他的“第一哲學”直接稱之為“神學”,柏拉圖也將世界劃分為感性的物質世界和超越的精神世界,由此而導致西方兩千多年的“唯心主義”傳統。所以,“愛智慧”從古希臘以來就意味著某種超越性,不是用於別的目的,而是超越於一切目的。
當時只有智者派是標榜知識的用處的,但這種用處也不是今天所謂的“經濟效益”,而恰好是用於提高人的素質,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素質教育”。他們自稱為“智者”(Sophist),適應著當時城邦民主生活和市場經濟的需要,智者們教人辯論術和修辭術,販賣知識,收費授徒,其實際作用是提高人們對當時社會的適應能力(素質)。
但即使這種收費教育打著素質教育的旗號,也為一般人所瞧不起,他們特別受到蘇格拉底的嘲笑。蘇格拉底認為這些自稱為“智者”的人太可笑不自量了,因為人的智慧與神的智慧相比有無限的距離,凡人不能自稱為“智者”,只能稱為“愛智者”,他自己則稱自己為“自知其無知”的人。
“愛智慧”的研究當然也會提高人的素質,但這只是後果,其目的不是要提供“有用的人才”,而是這件事本身很有趣,很吸引人,值得去愛、去追求,令人神往。因為它是人的本性,凡是人都忍不住要去追求。而追求的最終的目標就是神。所以蘇格拉底把對知識的追求看作自己對神的最好的“侍奉”。
後來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這種人神之分更加極端化了。在《聖經·舊約》中,人不配吃“知識之樹”的果子,那是上帝的專利,人類僭越了上帝的這一禁令就是犯罪。正是這一“犯罪”的意識把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之間的無限距離固定下來了,人要取得上帝專有的智慧,必須透過並基於對上帝的無條件的信仰和愛。換言之,人對智慧的愛轉變成了對上帝的愛(信仰)。
因此,所謂中世紀的“千年黑暗”雖然導致了西方反智主義的矇昧,但究其根源,並不是一般地對智慧本身的貶低和仇視,而正是因為對智慧看得太高了。“愛”和“智慧”的分離使得“愛”本身成了反智主義的信仰(如同德爾圖良所言:“正因其荒謬,我才相信”),但這種反智只是侷限於人的智慧,而並不涉及上帝的智慧。
東羅馬帝國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聖索菲亞大教堂”就是以“智慧”(Sophia,音譯為“索菲亞”)命名的,西方人取“索菲亞”為人名的也極其常見。所以,中世紀是以貶抑知識和智慧的方式,恰好曲折地表達了西方文化對知識和智慧的另一種更高的推崇,總地來看,仍然是以“愛智慧”為其一貫的傳統。這就為後來的知識、智慧的復興埋下了伏筆。
近代文藝復興是一場人性的復甦,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就是以前專屬於上帝的智慧也被降為人的一種基本興趣了,因而人也被提升為最接近於和類似於上帝的存在。對知識和智慧的愛重新佔據了人們關注的中心,人們畢生投身於對科學知識和原理的發現,以及利用這些發現進行發明創造、藝術創新,不是為了發展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而是為了好奇,為了探索真理,為了瞭解上帝是怎麼創造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的。
人和上帝相比仍然是有限的,但這種有限性本身被賦予了有限的神性,人是上帝的摹本。正如牛頓在《光學》中所說的:“從現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嗎?他無實體,卻生活著,有智慧而無所不在。”[2]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猜到上帝創世的秘密,這極大地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所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主題就是“自然的發現和人的發現”:自然是人所能夠把握和描述的自然,人則是以其自然屬性呈現出來的人。這兩方面都需要人對知識和智慧的不懈的追求,而這種追求的線索就是人的理性和感覺,或者說,從感覺上升到理性。
愛智慧的“愛”迴歸到了智慧,但已經不再是直接相關,而是多了一個上帝的維度;這個上帝不再幹涉人的探索行為,而是作為一個無限的目標為人的探索行為安身立命,賦予其神聖性和崇高性。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現代甚至後現代西方文化中,並不因時代的變遷而被完全拋棄。西方科學精神本質上是一種“愛智慧”的精神。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動物性的一面之外,還有超越動物性的神性的一面。人吃飯當然是為了活著,但活著不僅僅是為了吃飯,而是為了更高的追求,最終是精神上的超越性的追求。人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理想,人要發揮自己的個性和創造性,創造出從未有過的“奇蹟”,人就是一個“小神”。所以人是不能當成工具來使用的,否則就成為了“非人”。
但這一切都是基於“愛”。沒有愛,任何超越都談不上。愛是一種精神性的力量;但在現實生活中,它與其說帶來幸福,不如說更多地帶來痛苦,因為所愛的物件在彼岸,與現實的人拉開了無限的距離。但也正因此,愛才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間形成一種張力,可以摧毀一切障礙。
而在中國文化中,之所以缺乏愛也是因為沒有張力,一切都在此岸,都是純粹技術的問題。中國人的智慧是聖人的智慧,是成功者的智慧,而不是上帝的智慧。因而聖人是不需要“愛智慧”的,他本來就有智慧,只需要回覆本心就可以了。
當然,要做到回覆本心,也需要下“工夫”,需要“磨性”,也就是時時練習拒絕外界誘惑、放棄個人私慾、包括放棄“愛”的技術,日久天長,駕輕就熟,才能嶄露本性。所以,孔子雖然也講“仁者愛人”,但這種“愛”只須保持而無須追求,當下即得而樂莫大焉,它基於小孩子那種天生對父母的親情之愛,自然擴充套件為對他人及萬物的同體關愛(民胞物與)。
所以人只要回到小孩子的天真,是很容易做到的,如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所以原則上人人都可以做到成為聖人,甚至“滿街皆聖人”。相反,西方的愛智慧則恰好是因為沒有人能達到真正的智慧,所以只能“愛”,這種愛不是“工夫”,而是一種意向、興趣。
二、西方哲學的文化背景
中西哲學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別?與中西文化背景有關。
西方哲學既然是“愛智慧”,它就有兩方面的文化背景。一個是個人的獨立性,只有個人獨立才會有真正的“愛”,才會為了自己的愛而不顧一切地去追求;一個是宗教意識的昇華,智慧只有上升為神的智慧才值得人去追求,才具有最高的神聖性,而不只是工具。
1、個人的獨立
個人獨立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且是西方哲學兩千年來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它表現為自由意志、權利和責任等等問題。當然這種個人獨立在歷史上是相對的,有一個發展過程。古希臘和中世紀並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但為此奠定了基礎,一個是私有制的基礎,一個是個體靈魂學說的基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說,希臘社會進入人類文明的門檻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私有制和個體家庭的產生,這導致了希臘城邦國家的產生。而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影響就是個體意識的獨立,並在這種獨立起來的個體意識上建立起了取代家族血緣關係的新型的群體意識,這就是社會法律意識、公正意識。
正是在這裡,可以找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別的最為根本之點。因為在中國,情況恰好是私有制的不確立,家庭被束縛於氏族宗法體制之中,未能發展為以個體為單位的遊離家庭,而國家只不過是氏族宗法的家長制原則的放大,所有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識和公正原則來協調和制衡,而只須由家族習慣的“禮”、“義”制度以及道德觀念的“廉恥”之心來調節,就可以維持大致的社會和諧了。
而這種社會和諧的代價顯然是個體的不獨立,每個人在社會等級關係中都必須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且這種身份地位不像西方的奴隸和貴族那樣是比較固定的,而是不斷處於變動之中,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必須注意自己和他人相互之間在小至家庭、大至國家中的相對關係,而遵守在這種特定的關係中所規定的特殊的“禮”。
所以,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東方社會“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瞭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時[3],他們無疑也揭示了中國文化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獨立的個體意識的秘密。
古希臘個體意識的獨立最明顯地體現在他們的契約關係中。所謂契約,是以訂約雙方個體人格獨立及意志自由為前提的,因而是訂約雙方的一種平等關係。這種關係首先在希臘人的日常生活中取代了以往按照氏族等級關係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特別是經濟交往的慣例,而使人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的權利和義務。
其次,這種平等關係還體現在由獨立個人根據自願訂立的契約所組成的國家(城邦)的政治原則上,當時的城邦法律不是由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某種習慣或禮節,而是由城邦聘請著名哲學家依據平等原則和語言邏輯(邏各斯)來嚴格制定的法律體系,並且是由城邦公民大會表決透過的。
因此,這種體現在法律上的個體意識不是唯我獨尊或為所欲為,而是把個人獨立當做一條普遍原則,不但自己藉助於法律而獲得了獨立,而且懂得自己有義務把每個別人也當作獨立的來尊重。
與之相反,中國人的個人概念從來都不具有普遍性,要麼是凌駕於他人之上的天才、聖賢,要麼就是必須為了普遍性而犧牲的“人慾”。這種唯我獨尊、為所欲為的個體性只具有一種“獨立不依”的假象,因為它本身沒有形成一條普遍原則,而只是特定條件(包括天賦條件)下的特殊表現,一旦條件改變,它馬上就可以變為奴顏婢膝、喪失人格。
正如黑格爾所說的,“東方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但這一個人也並不真正自由。因為人人都想當“人上人”、當皇帝,而皇帝其實是最不自由、最不獨立的。在希臘人眼裡,真正的個人獨立則是有原則、有根據的,我不是因為我是某個特定的人而獨立,而是因為我是一般“人”而獨立。希臘人的獨立精神體現為契約合作精神,他們由此而建立起了古代民主制和最早的社會契約論。
這就是西方哲學的極為重要的文化背景。哲學本身就是個人獨立的事業,沒有一種哲學是集體合作搞出來的,在這方面哲學有點類似於藝術。但同時,哲學和藝術一樣,一旦創造出來之後,肯定是全人類的財富。哲學產品是天下之公器,哲學家雖然出自個人的興趣,但卻被視為“獻身於”全人類的崇高事業。
所以西方哲學家個性都很強,他們心中有更遠大的目標。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西方哲學家不盲從,不滿足於解釋和發揮師說,而是一代一代地進行創造性的開拓,不斷推翻、否定前人,另創新說。
因此西方哲學史顯示為一個“邏輯發展”過程,其中的動力就是每個哲學家對理論的推進。在這裡,沒有新意的哲學家是站不住腳的,人們強調的是個人之間的對話、商談、交鋒,樂此不疲。這些對話和交鋒並不是在世俗層面上展開的,而是立足於純粹思想的領域,其前提是古希臘羅馬靈魂學說的形成。
靈魂是個人獨有的,不可代替、不容混淆;但又同在超越物質的精神世界中,並有自身純粹精神的標準,這就是神或上帝。柏拉圖強調理性靈魂的自由本性,斯多亞派使靈魂的性質擺脫了本族人和外鄉人、貴族和平民、自由民和奴隸等等的世俗的區分,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提出了“世界主義”的人性理想。
世界主義其實是“超世界主義”,即一個超越世界各種區分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具有同一的人性原則和人格獨立性。斯多亞派和中世紀的基督教一起,把個人獨立提升到靈魂獨立的層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在“超世界”的層面上人人平等。這實際上是近代個體自我意識的主體獨立性的先聲。
如果說,中世紀基督教的上帝畢竟對個體人格有一種壓抑,主張為了人的精神而放逐人的肉體,那麼近代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則重新把靈與肉統一起來而形成了近代的“人權”概念。在這裡,個人真正達到了現實中的普遍獨立。在哲學領域,現代西方哲學更是個性化十足的哲學,各種觀點不再是單線發展,而是多頭並進,百家爭鳴。
2、宗教的昇華
西方哲學另外一個主題就是哲學與神學的關係問題,哲學與神學兩者在相互衝突中相互提升。有人把哲學當作宗教,有人認為宗教是最高的哲學。只有很少數的唯物主義者否認哲學與宗教的關係,但主要是否認那些過時了的宗教形式。例如費爾巴哈在批判了舊的基督教之後,仍然主張建立一種“愛”的新宗教。通常西方哲學家對宗教的批判都指向一種新宗教的建立,實際上使西方宗教提升到一個更高階段。
古希臘哲學最初就是出身於宗教批判,早期希臘哲學家、特別如赫拉克利特、塞諾芬尼等人,都反對原始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論和犧牲獻祭,他們嘲笑神話,破除迷信。古典時期的阿那克薩哥拉、智者派更是對傳統宗教不屑一顧。而蘇格拉底的貢獻則在於,他不僅致力於破除舊的宗教,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種具有哲學層次的新宗教,或者說,他使哲學本身提升到一種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慧田哲學公號下回複數字該題講座)。西方宗教從此擺脫了迷信,西方哲學也由自然哲學上升為精神哲學。
相比較而言,中國哲學自從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排斥了古代的神話和迷信之後,並沒有在純粹精神的層次上建立起一種超越性的新宗教來,因而並沒有從根本上揚棄迷信。董仲舒的讖緯神學由於仍然糾纏於“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場,而成為一種迷信和道德說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東西被層層包裹於物質的外殼之中。
宋明新道學則雖然大大減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為一種內聖外王之學和“內在超越”之學,但仍然沒有和迷信絕緣,而是經常性地以天人感應之兆來印證世俗人倫之理。這種內在超越的信仰原則上不可能離開此岸的成功和成就來支援,並且實際上是以現實世界的效果為信仰物件的。
西方宗教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是由於它基於個體獨立意識之上。同樣,中國宗教的不具超越性(或只具內在超越性)則是由於它基於個體意識的不獨立之上。西方超越性宗教的發生原理則在於自我意識的後退性“反思”,其前提是個人自我意識的獨立。
所謂“自我意識”就是試圖把自己一分為二,從“另一個自我”來看自己,以求認識真正的自己;但與此同時人立刻意識到,真正的自我並不是這個被認識的自己(物件),而是那個進行認識的自己(主體),因此要真正把握自己的意向便迫使人再次跳出這個主體的自己,把主體當客體來認識;但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主體一旦成為客體,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這又需要再退後一步。
就這樣,力求把握自己的需要使主體不斷退到自己後面來看自己,這種無限後退最終將推出一個絕對的自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知人心者”,而世俗的自我意識永遠都只是處於認識自我的旅途,對自我的獨立意識同時就是對自我的有限性的意識,在基督教中就表現為基督徒的“原罪”意識。
原罪就在於有限的人想要單憑自己把握無限的上帝,也就是想要把握絕對的自我,這正是個體獨立意識的體現。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對上帝的信仰恰好是個人自我意識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獨立的個人才會有真正的信仰。
由此可見,中國人之所以沒有超越性的信仰,正是由於中國人的個人不獨立。他的安身立命在群體、國家、天道,他的理想是天人合一、迴歸此岸、修齊治平,他用不著相信一個彼岸的神。
他也可以為了自己的理想而獻身,但前提是他相信歷史、“汗青”會對他作出肯定的評價,他歸根結底不是為心中的上帝和精神性的理想而獻身,而總是為現實生活的某個具體目標而獻身。他的精神永遠基於物質,被束縛於物質,不可能擺脫和超越物質。正因為他把自己歸屬於現實此岸的世界,這個世界總是凡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他認為只要自己心“誠”就可以與天道相通,“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一方面他認為一個凡人可以成聖,一旦成聖就可以“替天行道”,在地上建立人間天堂(王道樂土);另一方面他用來實現自己理想的手段總是物質性的,他總是用處理物質的方式來處理精神問題、思想問題,憑藉物質來控制精神、改造思想,以“唯物主義”的方式大搞“誅心之論”、大興文字獄,迫害知識分子。
與此相反,西方人的“太一”、耶和華、上帝完全是非物質性的,無形無象,只能從內心聆聽聖言;而且所謂的“啟示”並不可靠,信仰有可能走火入魔,所以這種信仰實際上沒有任何世俗的標準和物質的手段可以依賴。正因為如此,西方人致力於發展邏各斯、邏輯論證、辯證法,對“聖言”進行解釋和推演,來論證非物質的精神。這就是西方哲學後面的信仰資源。
當然,所有這些論證都不能保證人對上帝的把握是切實的,最終還是要訴之於超越性的信仰。而且這種信仰並不是你想要有就能有的,信仰本身要依賴於上帝的恩典,而這種恩典的內心證據就是看你內心是否充滿著神聖的“愛”,愛一切人,甚至“愛你的仇敵”。
所以在西方基督教中培養著人的謙遜、寬容和博愛的精神。西方教會不是一個世俗政權,而是一個精神機構,它由神學院培養的教士組成,在民眾中極有號召力,常常連皇帝都要甘拜下風。
1075年,教皇格利高裡七世由君權神授問題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發生衝突,皇帝宣佈廢黜教皇,教皇則宣佈破門律,將皇帝驅逐出教,導致皇帝眾叛親離,不得不於1077年親自到義大利謝罪,在教皇門外跪求三天,才獲准恢復教籍。
教皇沒有一兵一卒,為什麼對世俗權力有如此大的制約力?這正說明在基督教世界中,人們普遍的法權觀念認為超世俗的精神生活應當支配物質生活,而不是相反,世俗的皇帝也不能違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教雖然一開始也充滿著狂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教義逐漸培養了西方人講道理、守規矩、維護法律公正的自覺性,其中哲學家們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
現在我們回顧整個西方教會史,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在哲學家們的推動、闡發和批判中宗教層次不斷提高的歷史。反過來說,西方哲學若沒有宗教追求彼岸真理的訴求作背後的動力,也很難提高自己的思辨層次,而將侷限於世俗問題。
由以上文化背景就帶來了西方哲學如下兩方面的特點。
三、西方哲學的總體特點
西方哲學兩千年來有某種一以貫之的要素,這就是“邏各斯”(Logos)和“努斯”(Nous)的辯證結構。在古希臘,首次把這兩個概念納入哲學中來的分別是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薩哥拉。
“邏各斯”本來的意思是話語、言說,“神聖的邏各斯”則是神的話語,引伸為萬物的法則、規律,這個詞在斯多亞派那裡被進一步抽象化,形成了“邏輯”(Logik)一詞。所以“邏各斯”代表著普遍的規範性,清晰的可表達性、可言說性,這是西方哲學的一個根本性的要求。
“努斯”本來的意思是靈魂,特指一種超越性的理性靈魂,阿那克薩哥拉第一次把它置於整個宇宙之外,不與世俗的事物相摻合,其特點是超越萬物而能動地推動萬物。後來柏拉圖將它定義為“自動性”:萬物都是被推動的,唯有努斯是自動的,並因此而能推動萬物。所以努斯所代表的是無條件的絕對自由。
而這兩個希臘詞,即Logos和Nous,在外文和中文裡都可以譯作“理性”(英文reason,德文Vernunft);但它們所表示的是理性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或者說兩種不同的理性:一個是作為普遍的規範性的理性,一個是作為自由的超越性的理性。不講規範當然不能說是理性的,而沒有自由的超越、沉陷於感性的泥沼中,也不能說是有了理性。
規範性的建立有賴於理性自由的超越,而自由的理性之所以能夠超越,又憑藉的是普遍性的規範。所以理性的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西方哲學總是在這兩極之間震盪,有時偏向這一方面,有時偏向另一方面,但永遠也不可能完全撇開一方。
1、理性的“邏各斯”
西方後現代主義把他們自己的傳統稱之為“邏各斯中心主義”,這是非常貼切的。亞里士多德說“人是說話的動物”,又譯作“人是理性的動物”,實際上他說的就是“人是邏各斯的動物”,理性、語言被看作人的本質。
自古希臘起,西方人就非常看重語言以及語言的邏輯,這與他們的生存方式有關。古希臘是一個契約社會,血緣關係不佔日常生活的主流,陌生人之間靠契約和法律處理相互關係,希臘城邦民主制也靠演講和辯論來從事政治活動。不講理性、不講邏輯、說話不算數的人,在古希臘是沒法生存的。
這就是西方邏輯理性傳統的起源。邏輯理性是科學精神,也是法制精神,人們用理性來建立科學,也建立人際關係的科學即民主法制。西方人什麼都喜歡用理性來解決問題,就連上帝也用邏輯推理來證明。西方“後現代”雖然批判“邏各斯中心主義”,但其實還是離不了邏輯理性,他們的反理性主義(“反邏各斯主義”)也是理性的,寫了大量著作來“證明”他們的反理性。
2、自由的“努斯”
“努斯”原義為靈魂,靈魂的本質是自動性、超越性,首先是超越肉體和感性。所以與邏輯理性不同,這是一種超越的理性、自由的理性。邏輯理性與超越的理性既不同,又密切相關,不可分離。因為要想探求到邏輯理性、達到普遍性,必須要超越感性的特殊性才行;而要想真正超越感性,又必須藉助於邏輯理性作為跳板。
柏拉圖把努斯視為一種認識能力,是理性的一種向上攀升的能力。理性主動地向上追求,想要接近神的世界、“理念”世界,但卻做不到,因為人的理性很有限;但畢竟人在這點上比動物要高,體現了人的自由精神,這種自由精神是通往神性的。柏拉圖的唯心主義在西方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傳統,一條“路線”,它對西方哲學的貢獻比唯物主義更大,提升了人的精神生活,併為基督教奠定了理論基礎。
西方哲學的努斯精神實際上是自古希臘以來個體獨立意識的體現,個人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是獨立的,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的,而這種自由追求是一個從物質向精神的超越過程。真正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則要求超越一切物質世界的世俗的束縛而能動地支配物質世界,應該具有類似於上帝創世那樣的原創性。
這種自由精神的最早象徵性表達是赫拉克利特的“火”的哲學。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的本源是火,宇宙就是一場大火,每隔若干萬年就燃燒一次,然後熄滅,又再次燃燒;而這種燃燒又有自身的分寸和尺度,有自己的邏各斯規範,但卻不受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支配,甚至也不由任何神所創造。
火的特點與理性靈魂的能動性非常相似:火是無定形之物,不能被裝在任何形狀的容器裡,但它又不是完全沒有形狀的,而是有自己的形狀(火舌、火星、火苗等等),而這種形狀完全是由它自己規定的。
所以火的比喻一身而兼有邏各斯和努斯雙重特點,它最好地把這兩方面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了,所以歷代西方大哲總喜歡採用火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哲學,火、光明、太陽這些隱喻是西方哲學從古到今最常用的哲學比喻(例如從柏拉圖、新柏拉圖主義、基督教哲學、近代的康德、黑格爾,直到現代的尼采和海德格爾,都是如此)。
3、比較中國哲學的總體特點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比較,有兩個最主要的特點,一個是不重視語言,一個是不重視個體自由。因此中國哲學既沒有邏各斯精神,也沒有努斯精神。體現在哲學隱喻上,就是中國曆來都推崇“氣”的哲學。氣的哲學與火的哲學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在於兩方面,其一,氣沒有自己的形狀,你把它裝在什麼容器裡它就是什麼形狀;其二,氣是完全被動的,沒有主動性,雖然它無孔不入,但那也不是它要入的。
所以首先來看,中國哲學總體上有一種“反語言學”傾向,只重視內心體驗和外部行動,語言頂多只能當作一種臨時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執著。孔子主張要“聽其言,觀其行”,“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對語言採取了極不信任的態度;莊子說:“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禪宗則“不立文字”、“言語道斷,心行路絕”。儒、道、佛都把語言當成一種多餘或誤導性的東西,頂多是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用完之後就應當徹底拋棄。
因此,中國哲學也不重視認識論和方法論,不管條件和過程而只重視結果。在人際交往中,中國人不重契約,只重默契,寫在紙上的東西不作數,代人簽字不為過。對自然知識只重效果不問規律,只重技術不重原理;政治生活中“人情大於王法”,任何規章制度都限制不了“潛規則”;經濟活動中只講規矩不講規範。
而不重視語言的根源在於,中國哲學中沒有真正的個體自由。所以從更深層次上說,中國哲學總體上有一種壓抑個人自由的傾向。老莊、禪佛講的“自由”是去掉個人執著之後的無所拘束、逍遙自在,無追求無責任,等同於“自然”和“無為”,是一種“無意志的自由”;儒家講的“大丈夫精神”則是“無自由的意志”。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似乎達到了自由境界;但這個“矩”並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來的,而是從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傳下來的(雖然有所損益),他不過是習慣成自然了而已。
以上兩方面相輔相成:缺乏邏各斯精神,個體自由就失去了表達的手段和保護的屏障,成為魯迅所謂“沉默的國民”;沒有自由的努斯精神,也就沒有要透過語言來表達個體意志的需要,人與人之間不是靠語言和契約的規範,而是靠自然血緣關係的粘合和霸權的控制,成為魯迅所謂“無愛的人間”。所有這些都是阻礙我們今天走向現代化法制社會的絆腳石。
結論
從中西哲學的比較中我們看出,一個民族的思維模式是決定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魯迅當年講的“國民性改造”就是針對這一點而言的。思維模式不改變,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終會九九歸元,換湯不換藥。
而思維模式的變革又主要著重於兩方面,一個是建立理性精神,一個是發揚自由精神。五四提出的“科學和民主”底下其實是理性和自由,沒有理性,科學就喪失了科學精神,變成了另一種迷信;沒有自由,民主就變成了“為民作主”,即另一種專制。
[1] 文化和文明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本文的主題用不著對此作細緻的區分。
[2] 轉引自丹皮爾著:《科學史》,李珩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52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2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