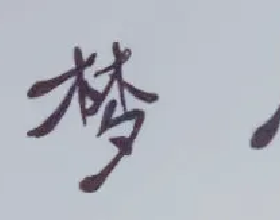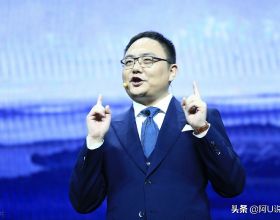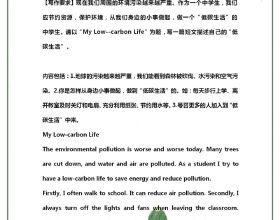(圖片來源:圖蟲網)
——訪《自我的幻覺術》作者汪天艾
馮周/訪、文
在西班牙語譯者身份之外,汪天艾在今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隨筆集《自我的幻覺術》。書名來自於詩人馬雁的詩《自我的幻覺術》,馬雁在詩中寫道:“世界必有出口,你必有脫身的時刻。”
對汪天艾而言,“有好書,有沉浸式的閱讀體驗,就是馬雁寫到的世界的出口。”從某種意義上,汪天艾將自己的寫作視為和翻譯很相近的規律性勞作。在這本書中集結的25篇文章,來自於她在2016年到2019年間基於書籍的報刊專欄寫作。也因此,她強調她的寫作者身份仍舊始於讀者身份,正如她在翻譯時的“工作”,是將“分享的記憶進行鐫刻”(訪者改自馬雁詩)。
這個出口不僅為她,也為她的讀者提供了逃離的時刻。在因疫情封城被困於武漢時,她曾於社交網路上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來信者告知她,她相當久遠的某篇文章中寫到的書,和其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共鳴。這讓她終於擺脫了“自我審視的羞赧”,在“外部世界劇變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勇氣”中,將這些散落於報刊的文字結集。“這些文章背後那些沒有被我縮手縮腳的書寫折損的故事,無論是歷史片段、人物經歷還是作品情節,它們本身是珍貴的、值得被讀到的。”她如是寫道。
在這個疫情連綿、聯結被撕裂的劇變時代,筆者願意相信,汪天艾的這本《自我的幻覺術》或許可以將同樣的出口和勇氣帶給讀者。當我們瞭解曾經的人怎樣度過封鎖、抵禦精神危機,或許能獲得一種力量。正如在專訪中,汪天艾所引述的戰後詩人別德馬為悼念塞爾努達寫的詩:“而我想要一樣我們時代罕有的東西/那種美德,古典的美:/用尊嚴和力量/扛過多年的磨難。”
訪談
馮周:在《現實與慾望》這本您翻譯的塞爾努達詩集的譯後記中,我看到您引用了馬雁的詩句“你成為眾人分享的記憶,/而我此生的工作是對記憶的鐫刻。”在如今出版的《自我的幻覺術》這本書評集(不知道您願意怎麼稱呼)的後記中,您引用了馬雁的另一句詩“世界必有出口,/你必有脫身的時刻。”來分享自己作為寫作者的感受。對於您而言,翻譯者和寫作者的身份有哪些不同處(亦或是相同處)?您如何看待這“兩重身份”,又是如何平衡的?
汪天艾:關於怎樣稱呼這本書的文體,我也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答案,可能勉強算一本隨筆集吧。裡面的文章最初確實都是作為書評發表的,只是大多篇目在寫作的過程中都沒能真正行使到作為書評人與原書作者在齊平的視野上進行評論的職責,更像是作為(能夠閱讀外語原文並第一時間接觸到新書的)普通讀者囫圇吞棗一番,再作為中文寫作者吐露出一點皮毛。
翻譯者的身份至今有十年了,體會到詩歌翻譯本質上是一種勞作(正如馬雁那句詩裡寫到的“工作”與“鐫刻”),最理想的狀態是規律的匠人生活,每天定時定量,絕不貪多。雖然隨時可能鑿壞了,隨時可能需要返工,最終的成品盡如人意的時候並不多見,但是譯過的詩人都是自己珍視與欽慕的,會希望他/她能被更多人讀到乃至記住,那麼這份工就可以無盡期地做下去。
寫作者的身份在我的情況下可能與翻譯者差別不大。
一方面,寫作被我(恐怕有些古板無趣地)轉變成了和翻譯很相近的規律性勞作。從2014年中到2019年初,我接續地為《文藝報》和《經濟觀察報》寫過每月4000字左右的專欄,除了在博士中期和畢業答辯前夕中斷過兩次,其餘時間幾乎每個月都要經歷一輪選書——閱讀——做筆記——寫稿的過程。《自我的幻覺術》裡的文章是從那幾年寫過的五十來篇專欄文章裡選取出來,再重新進行修改和編排的。
另一方面,很慚愧,我實在是個完全沒有虛構之力也沒有什麼奇思妙想的人(身邊有不少師友擁有神奇的創造力,讀他們的作品每每令人感嘆“這是怎麼想到的!”)。如果沒有材料作為基礎,就很難寫出什麼來。從收在《自我的幻覺術》這本書裡的文章也能看出,每篇文章都脫胎於對某一本或幾本書的閱讀,如果說有任何體現我作為創作者主體性的地方,恐怕只是在材料取捨、敘事方式、結構排布之類的方面展開的種種不見得成功的嘗試。
從這個角度上,翻譯者和寫作者這兩個身份對我而言都是始於作為讀者。在任何無力翻譯、無心寫作的時候,也都會退回到讀者的狀態。有好書,有沉浸式的閱讀體驗,對我而言,就是馬雁寫到的世界的出口。
馮周:您在書中的《我們在書店相遇》這篇文章中,以相當有感染力的筆觸記述了弗朗西斯科·布里內斯在書店偶然閱讀到塞爾努達詩集後所引發的熱情和共鳴。您認為這間小書店成全了塞爾努達感嘆過的作為寫作者“令人豔羨的命運”:“穿過同代人的視而不見,在身後未來的讀者那裡找到道路。”在您對於馬雁的不斷引用中,我似乎能看到同樣的熱情。此外,《哈利·波特》也是在您的文字中經常可以看到的意象出處。所以很好奇,除了您所熱愛的西班牙文學之外,您所受到影響比較深刻的文學作品有哪些?它們對您的生活道路有沒有起到過一些獨特的影響?
汪天艾:《哈利·波特》第一本書的中譯本出版的時候,我差不多剛好是書中主人公收到霍格沃茨錄取信時的年紀(10歲出頭),那本書是母親送給我的兒童節禮物。第七本出版的時候,我剛剛升入高三。因此幾乎是“追連載”一般跟著這套書度過了整個青春期。後來在西班牙飽受入睡困難之苦的幾年,也是靠著“油炸叔”StephenFry讀的《哈利·波特》有聲書催眠,從頭到尾聽過好幾輪。回想起來,這套書對我來說,也有點像是在渴望脫身的時刻提供了另一個出口。
對我的語感和語言觀影響比較深刻的文學作品追溯起來,可能最早的源頭是張愛玲。小時候讀的次數太多,被她的細理入微、不動聲色而驀然驚奇的描寫和比喻收得服服帖帖,以至於多年來都對於語言(乃至結構)的精巧、妥帖、不贅有一種執迷。直到最近這幾年,才開始慢慢懂得欣賞粗紋理的語言的勁道。
喜歡的文學作品太多,一時間都羅列不清。對生活道路最大的影響恐怕就是雖然沒能如願地念上中文系,至少最後還是以文學研究為業,以文學編輯為生,這一生應該是都會與它相伴了。不過總還是難免想起本科畢業時候導師跟我說的話,他說:“事實證明你還是不夠喜歡文學,不然哪捨得把它變成專業。”
馮周:您引述了阿根廷小說家皮格利亞的一句話,“文學評論是自傳的一種形式,一位作家以為自己在寫他的閱讀經歷,其實寫下的卻是自己的人生。”同樣的,在您書中收錄的25篇評論中,不難找到關於您在馬德里、倫敦時的生活的碎片。當您身處在西班牙,閱讀並評論西班牙語作品時,是否會獲得某些理解上的加成?對於身處因疫情被迫封閉的世界的我們而言,“在地”地透過旅遊和實地授課去了解和學習他國文化不再那麼容易,我們如何能克服這種困難?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否能寄希望與文學?
汪天艾:在馬德里的時候,每週都會去逛書店,文章裡寫到的西語作品大多是逛書店的時候逛出來的。這種體驗造就了一些很難透過搜尋引擎實現的驚喜,因為出發的時候並不知道想找什麼樣的書,很多時候是很偶然的,因為封面的吸引,因為隨便翻看一頁看到的某句話。這種“在地”的經驗真的是很令人懷念。
疫情之後,所有此前視為理所當然的旅行便利都突然失效。有時候甚至不免會想,可能即便等到一切過去、邊境重新開放的時候,心態也不會完全和此前相同了。因為疫情似乎除了實體地割裂了交通,也暴露和撕裂了更為深層次的聯結。在這樣的時刻,我還是願意相信經過上一個、上上個乃至更久遠以前的動盪時代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裡存有曾經的人怎樣度過封鎖、抵禦精神危機的見證。
馮周:開啟《自我的幻覺術》,第一部分“消磁的空帶”直接將我們帶回了充滿西班牙內戰硝煙的艱難時世中,這是一個相當沉重的開頭。為何您和編輯在體例上做了這樣的選擇?您在一席的演講中,將新冠時代和西班牙內戰聯絡到了一起:身處於“時代和歷史”的重大轉折中,個體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和堅持。親身經歷了武漢封城這樣強烈的歷史瞬間之後,您如何回望和評價您在這兩年以來的疫情時代的生活?
汪天艾:西班牙內戰及戰後佛朗哥時期是我一直以來都很執迷的一段歷史,研究方向也一直是同時代的詩人及作品。在研究的過程中,我開始越來越被內戰及戰後知識分子的心態演變史吸引,想要知道那些人在歷史動盪面前做出了怎樣的選擇,又是為什麼做出這些選擇。“消磁的空帶”這部分裡的文章基本是在回應這種關注。在我看來,歷史不僅是記錄在案的一盤盤錄影帶上的磅礴恢弘的畫面,更是當時當刻被攝錄下來、此後卻在時間或際遇的作用下變得含混不明、充滿雜音乃至消失不見的部分,像是被消磁了或是壞掉的空帶。
大歷史面前人很渺小,有許多的無可奈何,許多的力不從心。塞爾努達在1945年給朋友寫信說:“我們都在這裡浪費時間。如果僅僅是浪費時間其實沒什麼大不了。只是原本可以用來工作和共同生活的最好的年月,就這樣被白白揮霍過去了。確實,誰的生命沒有被白白浪費呢。”後來我讀到沈從文先生在《湘行散記》的序裡寫“這麼一種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維持下去,終將受一種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所摧毀。生命似異實同,結束於無可奈何情形中”,能體會到是同一種情緒在其中流動。但是與此同時,在這些經歷內戰及戰後的具體個體的經歷與故事裡,有一種精神力的東西令人震盪,有一點像戰後詩人別德馬為悼念塞爾努達寫的詩裡的幾行:“而我想要一樣我們時代罕有的東西/那種美德,古典的美:/用尊嚴和力量/扛過多年的磨難。”把這部分放在全書的開頭,是因為對我而言,這樣的嚴肅與沉重裡有一種力量,我不希望這本書寄於輕渺的文藝,而是希望它能有一些力量吧。
這兩年疫情時代的生活,我感覺自己的人生髮生了很大的改變,好像是因為外部的不確定性,自己此前很多無謂的恐懼反而消弭了,人也平靜了許多。可能也是年齡的原因,對於分享的慾望也沒有以前強烈了,無論是翻譯還是寫作,速度都變得很慢,現在主要的身份又迴歸到了讀者。
馮周:在這本書中,《倖存者閱讀》這篇文章相當打動我。它並不關乎文學家或是藝術家,而是關於兩個體育界人士的抑鬱症之死。您在這篇文章裡關注了非文藝領域抑鬱症患者更艱難的處境。大眾對於文學其中一個誤區是,認為其只是小圈子精英先鋒的自言自語,和普通人毫無關係。您如何看待文學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作為寫作者,您是否會考慮到普通讀者的閱讀需求,並希望吸引到他們?作為小眾的西語文學的翻譯者,您對吸引大眾市場仍會抱有希冀嗎?
汪天艾:特別開心你專門提到這篇文章。《倖存者閱讀》是我自己覺得寫得格外“掏心掏肺”的一篇。之前翻譯出版皮扎尼克的詩集之後,在新書分享會上被問起過為什麼詩人總是和抑鬱症以及自殺聯絡在一起。但是其實有資料顯示,在中國自殺比例最高的群體是農村的女性和老人。大家有一種印象,文藝領域的抑鬱症患者特別多,只是他們被看見了。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有更多的承受著痛苦的人。
關於文學與普通人,奧登在《詩人與城市》中有一段很著名的關於現代詩歌寫作物件的論述,說到現代詩歌特有的主人公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男男女女,他們頂著現代社會所有的非人的壓力,試圖獲得並保持他們自己的臉孔。也就是說,文學的創造者(尤其是現當代文學)本來就是普通人,同樣要面對大到歷史動盪的洪流、小到的日常生活的複雜。
我對自己寫的東西一直不是太有執念,可能是因為讀到過太多真的值得被讀到的作品,相比之下就覺得自己的寫作本身其實真的像我這本書的後記裡寫的,只算是“書寫”。但是確實是託了可以讀西語原文著作的福,把一些沒有在漢語語境裡出現過的歷史和文學片段用中文寫出來,這些人和故事我想它們會吸引到一些讀者,那就很足夠了。
作為西語譯者,可能這種希望所翻譯的作品被讀到的執念會重一些,尤其是之前翻譯做得比較密集的那些年。西班牙語文學裡有太多真的很優秀的作家作品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譯介,所以每每想起來,總有一種迫切感。現在沒有之前那麼迫切了,覺得來日方長吧,只要還在做這一行,對得起自己的職業良心,其他就交給時間吧。
馮周:最後仍不能免俗,需要問一下您近期有何翻譯和寫作的計劃?此外,可否將最近讀過的書推薦一二?
汪天艾:近期的翻譯計劃還是在做已經做了好幾年一直也沒完成的幾樣,一個是戰後詩人吉爾·德·別德馬(JaimeGildeBiedma)的詩集;一個是塞爾努達詩歌全集的後半本。寫作的話,從2018年底到今年年初寫完了一本細讀塞爾努達詩歌的書,我一直很敬仰前輩學人在對中國現當代詩歌批評中以細讀為方法產出的成果,這本書嘗試用這種正規化對塞爾努達一些詩歌代表作進行了評論與研究。如果順利的話,今年年內就能和大家見面了。之後暫時還沒有新的計劃,未來幾年應該是以閱讀和積累為主了。
最近讀過的書裡,印象比較深的一本是錢理群老師寫的《1948:天地玄黃》,讀下來酣暢淋漓,還有姜濤老師的《公寓裡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這兩本書關注的都是特殊歷史節點上知識分子的心態與抉擇,這種人與歷史的寫法,是我特別仰慕和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