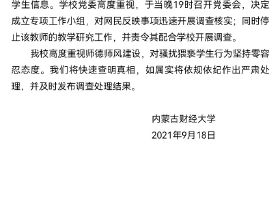時光匆匆,流逝的歲月中改變了太多東西,不僅僅是無聲的自然,更多的還是可以思考的人心。世事無常,命運反覆,誰也不再是曾經的某某某,那些懷念的,慢慢地消散於歷史的塵埃裡,悄無聲息。
《家兄有和再用韻》
【宋】艾可翁
隔林看日落,出戶對天行。
久亂人情變,長貧心事明。
虹拖城郭勢,河瀉甲兵聲。
誰似秋來水,能於濁世清。
這首《家兄有和再用韻》,意思是詩人的兄長曾經寫詩,步韻和他相和,因此興致濃郁之下,再次步原韻又寫了這一首。詩人不改初衷,仍然抒發著對喪亂及之後混濁世情的某些看法,內心裡相應地充斥著一種厚重的對現實狀況無可奈何之情。
“隔林看日落,出戶對天行”,天行,任自然而行,見《莊子·刻意》:“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隔著樹林子,眼看著太陽慢慢地向西山落下,餘暉漫天;走出門外,沒有目的地,自然而然,任意而行。似乎散漫,卻自帶意趣,正是得或失之時的取捨心理。
在這裡,恍若第一視線的角度,使閱讀者也順著詩人的落筆一同去“看日落”和“對天行”。“隔林”和“出戶”,這兩個行為其實是協調一致的,具有連續性,不可分割。這個感覺十分地奇特,給人一種很是強烈的參與意味,一切都彷彿自己親眼目睹一般。
“久亂人情變,長貧心事明”,前面的“天行”,另有一種“天命”的意思。事實上,這個世界上哪有這麼多天命可言,更多的不過是人心。經過長時間的戰亂,過去的人情將會逐漸變得淡薄,而一直處於貧困境遇之內,還有什麼事情是不好琢磨清楚的呢?除非是真正愚不可及之輩。
或許正是這樣的緣故,才讓詩人真正地體會到紅塵俗事的種種不同,社會世態的各種不堪,他選擇了某種相對來說比較“超脫”的為人處世之態度。風雲變幻,笑看日落;人事變遷,隨心所欲。也因此經歷得越多,醒悟得越早,看問題更加通透,不會長時間糾結在這些人事關係之中難以自拔。
“虹拖城郭勢,河瀉甲兵聲”,城郭,亦作“城廓”,城牆,城指內城的牆,郭指外城的牆。甲兵,原指鎧甲和兵械,後亦指軍隊,如高蟾《宋汴道中》詩:“甲兵年正少,日久戍天涯。”。彩虹橫跨天際,拖曵而過,愈發增加了城牆的威勢,而長河滾滾,日夜不停地流淌,喧譁聲響好似軍隊行列。
什麼叫有聲有色?這兩句便是。無論是天際之虹,還是城外之河,其所營造出來的卻是一幅驚心動魄的畫圖。這些全部都是戰亂之後,詩人觸景生情內心所想象的。這種沒有安全的忐忑之感,多像成語所形容的“驚弓之鳥”啊。人之渺小,可見一斑。
“誰似秋來水,能於濁世清”,可以想通所有難解的世情,卻沒有辦法忘懷戰爭帶來的傷害。在這個世界上,又有哪個人能夠像秋天裡江水,可以洗滌乾淨世間所有的渾濁,讓這個世道變得清明起來呢?在這樣的懷疑質問聲裡,佈滿著詩人足夠多的悲憤之意,惱恨之情。精神上的遺留問題,是最殘忍的困惑。
讀至此處,不由得令人想到三閭大夫屈原與漁夫問答後的唱詞:“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楚辭·漁夫》)。同樣都是,把這個世間難得的可貴品質,比喻成尋常可見的水,蓋因:“水有五德,有德、有義、有道、有勇、有法,君子遇水必觀。”相傳這個概念來自於聖人孔子所說。
詩人置身於闊大的自然環境之中,讓自身的情感與外在的景觀有機地整合在一起,以外部的宏大場面去壓抑著奔湧著的內心,並以此凸現作為一個渺小的社會生物,自始至終都難以擺脫命運壓迫的真情實感。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詩人一直想要與自己和解,所以不斷地勸導自己,“久亂人情變,長貧心事明”,儘量去擺脫紅塵俗世的干擾,打造屬於自己的一方淨土。可惜,生而為人,又怎麼能夠說逃離就輕易撒手呢?詩人只好在結尾生出期盼之疑問,強調著對改造“濁世”的希冀。終究有愛,誤我一生。
(圖片來自網路,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