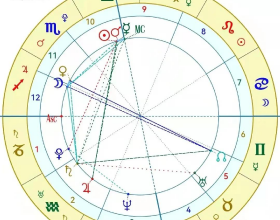江戶初期,陽明學傳到日本。
當時日本的大儒在接觸到王陽明的著作之後,對那些著作進行了詳細的閱讀。
貝原益軒是福岡的一位大儒學家,因博學廣識而聞名於世,在他的讀書目錄《玩古目錄》中有《王文成公全書》。
可以推測,他當時應該也讀過王陽明的著作。
最早在日本介紹陽明學的是中江藤樹。
他先是在伊予國的大洲為官,後來辭官回家侍奉雙親,被尊稱為“近江聖人”。
中江藤樹曾經建立藤樹書院,並模仿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制定出《學舍坐右戒》,招收弟子,講學授業。
藤樹最初修習的是程朱學,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王陽明的高徒、王學左派(良知現成派)巨匠王龍溪的著作;
讀後激動萬分,對陽明學的崇拜一發而不可收,最終將治學方向轉向陽明學。
為什麼王學左派的“良知”說會如此打動中江藤樹呢?
王學左派主張,無論我們多麼卑微,都和聖人一樣具有完滿的良知;
無須做學問,也無須痴迷於煩瑣的修行,只要達到頓悟,就可以變成聖人。
在當時的思想界,王學左派的主張可謂驚世駭俗;
人們不再需要日積月累的學習,也不再需要對內心和品行進行苦修,一樣可以達到聖賢的境界。
日本陽明學鼻祖中江藤樹畫像。
中江藤樹最初修習的是程朱學,後來接觸到王學左派王畿的著作後,便迷上了陽明學。
王學左派的“良知”說很快就俘獲了大眾的內心,成為風靡一時的學說。
王學左派強調絕對的自我,提倡為民辦事和男女平等,肯定人的慾望;
所以信奉民主主義的歐洲學者大都喜歡研究這方面的思想。
無論是誰,當有人對他說:
“你和聖人一樣,都具有出色的良知。你本來就是聖人,只是還沒意識到而已,只要意識到了,你就能變成聖人”時,
這個人肯定會產生強大的自信。
因此,中江藤樹會對陽明學產生興趣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王學左派的思想是對王陽明“良知”說的刨根問底。
它最大的功績在於闡明瞭王陽明潛藏於內心,而沒有直接言明的思想。
但同時也產生了極大的弊端。
此派學者不贊同用倫理道德來約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與自由。
呼籲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結果亂了世間綱紀。
他們大都率性而為,一旦對社會和政治不滿,便會毫無忌憚地發怒。
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傢伙”,狂言酒色才氣不礙菩提路;
並把這些驚世駭俗的舉動看作是順應良知的行為。
日本社會從戰後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風潮和明末的風潮極其相似。
如上所述,中江藤樹因為王學左派的“良知”說而對陽明學產生了興趣,但是藤樹沒有沿襲王學左派的行為。
其實不只是中江藤樹,所有日本的陽明學者都是如此,日本人對陽明學的吸收是積極和穩健的。
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推崇“同心同德”;
這和《論語》中的“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有些相似,
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推崇“仁愛精神”的儒學。
日本是單一民族、單一語言,人與人的心靈自然相通,也不存在嚴重的對立。
由於這一民族性,日本人一直以來都積極吸收外來文化。
總而言之,日本人天生就具有“自他一體”的世界觀,再加上沒有遭遇過外族入侵,所以最終形成了相容幷蓄的民族性。
日本人“自他一體”的世界觀,不僅僅體現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也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
日本列島地理氣候多樣,漫長的海岸線呈鋸齒狀;
四季的變換營造出絢麗的色彩,生長於斯的日本人和大自然融為一體,情感也變得豐富。
具有此種民族性的日本人,當然會樂於接受以仁愛為本的儒家思想。
對日本人來說,很少有人會站在事物的對立面去思考問題,
也很少有人會運用邏輯思維去探求事物的本源。
經常聽到有人說日本人不喜歡“發言”,不喜歡錶達自己的觀點。
其實,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時,是整體性地去理解事物,
而不是站在事物的對立面去研究。
以上所提的“整體性理解”,指的是將事物和自己的內心合為一體之後再去理解,
而不是把事物物件化,然後透過思辨的態度去理解。
其實,這就是日本人的感性理解方式。
日本人非常感性,並將這一特性貫穿到思想和文化領域。
雖然感性的理解方式存在各種缺點,
例如容易造成理性的欠缺,陷入對事物的感性認知等,
但同時它也有自身的長處,那就是對事物的整體性把握以及賦予事物生命性等。
一旦理解方式整體化,被理解的事物自然就有了生命性,理解起來也會變得簡單。
我們在認知一個事物時,沒有必要去擺弄那些煩瑣的思辨和理論,
也沒有必要在抽象的世界裡左顧右盼。
對事物進行感性認識和整體把握,未必不是一條好的途徑。
陽明學不同於朱子學,它的“求道”方式是整體性的,簡單易操作。
王陽明提倡的“良知”說是一個嚴格的生命體,
它包含敏銳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
既有道德的好惡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則。
根據陽明學的理論,只要順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極其簡單。
越是簡單的東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實性。
日本人被陽明學的“良知”說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