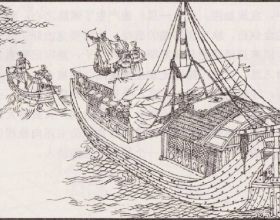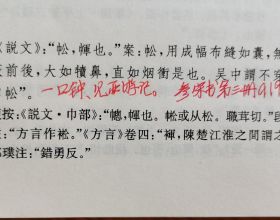常洋銘(魯汶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設拉子有薩迪墓和哈菲茲墓,而伊斯法罕則有珀普墓。”
1981年冬天,時任哈佛大學伊朗學講席教授的費耐生(Richard N. Frye)在寄給雷克斯福德·斯泰德(Rexford Stead)的信中這樣寫道。話雖如此,但費耐生並非是想拿珀普與創作了《果園》《薔薇園》和《詩頌集》的波斯詩聖們相比,這種比較大概純粹是從三座墓葬的建築本身出發的——薩迪墓和珀普墓都是由德黑蘭大學建築學教授、伊朗著名建築師穆赫辛·福魯吉(Mohsin Foroughi)設計的,而哈菲茲墓的設計師則是福魯吉的同事、法國考古學家和建築師安德烈·戈達爾(André Godard),他們兩位都是二戰後伊朗建築設計界的代表人物。自然,不管在波斯文學領域還是就伊朗文明整體而言,珀普都沒有資格與薩迪和哈菲茲相提並論。但是,能在伊斯法罕城內的上佳位置擁有一座花園中的陵墓,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絕非一件平常的事。對於珀普來說,這或許也是他鐘情于波斯文物、藝術與建築的一生最好的歸宿。
在費耐生寄出這封信的100年前,1881年春天,亞瑟·珀普(Arthur Upham Pope)出生在美國羅德島州西南部的小鎮費尼克斯(Phenix)。18歲時,珀普自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學院(Worcester Academy)畢業,考入布朗大學,並且在七年後獲得了碩士學位。在布朗讀書期間,他與後來成為了知名作家的波撒·戴蒙(Bertha Damon)相識並結為連理。此後的五年,珀普輾轉於紐約、波士頓等地,在康奈爾、哈佛等校繼續求學。1911年,珀普獲得了伯克利加州大學哲學系的工作機會,夫婦二人一同移居到加州的奧克蘭。在伯克利執教的六年時間中,珀普遇到了他後來的伴侶和工作夥伴、當時的他的學生菲利斯·阿克曼(Phyllis Ackerman)。這段不倫的師生關係所引發的爭議,最終致使珀普從伯克利辭職,並且最終徹底遠離了哲學界。1920年,在和波撒·戴蒙離婚後,珀普與阿克曼註冊結婚,二人繼續住在加州。自此開始,珀普和阿克曼一起,全身心地投身於他長久以來的興趣,即對東方(尤其是波斯和阿拉伯)文物、藝術品的收藏、鑑賞和研究。

1929年,亞瑟·珀普在伊斯法罕考察清真寺建築,現藏於哈佛大學藝術圖書館
1947年,亞瑟·珀普和菲利斯·阿克曼在位於紐約亞洲研究院中他們的研究室裡,現藏於哈佛大學藝術圖書館
珀普選擇在這時進入東方藝術史領域和文物行業,除了個人興趣的驅使外,可能有更加現實的動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藝術收藏市場的中心從百廢待興的歐洲逐漸向北美轉移。而就中東地區而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逐步崩潰和波斯愷加王朝的衰落所引發的社會政治秩序的更迭,進一步地促使中東的古董和藝術品典藏流入西方、大量地進入歐美藏家的視野。另外,近代以來,西方學者、探險家和各類公私機構廣泛地參與到整個舊大陸範圍內的尋寶和考古工作中。在進入20世紀後,對古代亞非歷史時期各階段的語文、歷史、考古學和藝術史的研究與教學,已經以東方學的名義,在歐洲和北美的學術世界中開拓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並且通常能夠得到所在國當局和社會各界有力人士的支援。當然,西方世界對自己古典文明起源的追問,並非是當時的人們探索古代東方文明的唯一動力。對於當時正在形成的現代中東來說,那些逐漸走出了奧斯曼帝國殘夢的當地居民,擁有不同的信仰,說著不同的語言,也開始透過對上古文明的解釋,重塑各自的民族歷史與認同。這些意識形態領域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對中東古代遺址的發掘、研究與文物收藏產生了影響。
面臨著這麼一個快速膨脹的新興市場,真正有能力評鑑中東古董和藝術品的專家卻依然少之又少,尤其是在美國。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前期,距離珀普從伯克利辭任、潛心研究東方藝術沒幾年,他已經成為聞名全美的中東文物專家了。全美各地的藝廊、博物館和收藏家都向他徵求波斯、阿拉伯文物方面的意見。除了顧問服務之外,珀普也開始幫助北美的博物館和個人收藏家介紹銷售中東古董和藝術品的商人,或直接在其中擔任中介。他先後為舊金山、芝加哥和堪薩斯城等地的博物館建立了相當規模的中東文物收藏。在此過程中,珀普對於波斯藝術的偏愛表露無疑。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檔案裡,收購記錄中400條賣家名稱標註為珀普的藏品,其中的一半以上都來自伊朗。1925年,珀普開始擔任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顧問館員,並且在博物館理事會的委託下前往伊朗,深入調查當地的古蹟和文物。
考古學在伊朗開始得並不算晚。在愷加王朝統治下的19世紀中葉,西方考古學家就已經開始在伊朗境內開展了田野發掘工作。在伊朗西南部的胡齊斯坦(Khuzestan)地區、靠近兩河流域南部的蘇薩(Susa)是其境內首個被大規模發掘的遺址,而這座遺址的發掘史也是伊朗考古學從萌芽到初步發展階段的一個縮影。1851年,英國學者威廉·洛夫特斯(William Loftus)結束了自己在兩河流域南部著名的烏爾(Ur)和烏魯克(Uruk)等地的工作後,開始對蘇薩遺址展開調查。但在兩年之後,洛夫特斯又離開了蘇薩、重新回到了兩河流域。此後,在法籍御醫託羅臧(Joseph Désiré Tholozan)的遊說下,國王納賽爾丁沙赫(Naser al-Din Shah)將蘇薩遺址的發掘許可授予法國探險家馬塞爾-奧古斯特·德約拉夫瓦(Marcel-Auguste Dieulafoy),後者於1884至1886年間發掘了蘇薩遺址。1897年,法國學者讓-雅克·德·摩爾岡(Jean-Jacques de Morgan)重啟了德約拉夫瓦在蘇薩遺址的發掘。這次發掘一直延續到一戰前夕,期間收穫頗豐。著名的漢穆拉比法典石碑、納拉姆辛勝利石碑都是在這次發掘過程中發現的。大量不同時期的埃蘭楔形文字泥版的出土,也為文字起源和埃蘭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另外,蘇薩還出土了大量阿契美尼德波斯時期的建築構件與藝術品。這次考古發掘所出土的文物,如今大部分收藏於盧浮宮。發掘的過程和結果,後陸續發表於《法國駐波斯代表團行紀》(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和《法國駐伊朗考古代表團通訊》(Cahier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Iran)等叢刊中。一戰的爆發使得法國在伊朗的考古活動全部停止,伊朗成為了英、俄、奧斯曼三國的戰場。1921年,哥薩克兵團發動的軍事政變成為了壓垮波斯愷加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法國在伊朗考古領域的王家特許權也因此宣告終結。1925年12月,已實際掌權多年的禮薩汗(Reza Khan)正式登基,成為國王,伊朗進入了巴列維王朝。而在這一年的春天,珀普就已經來到了德黑蘭,見到了登基之前、時任王國首相的禮薩汗。
在德黑蘭舉辦的一場名為“波斯藝術的過去與未來”(Past and Future of Persian Art)的演講中,珀普對在場的禮薩汗與他的朋友和下屬們這樣說道:“波斯以其多樣、獨特且輝煌的裝飾藝術而聞名寰宇。無論古今,兩千多年來,在整個文明世界,人們都曾以文字和錢幣的形式向波斯人的美學天才致敬。”在演講中,珀普對波斯歷史悠久的藝術和建築遺產讚不絕口,敦促在場的伊朗權貴們重視他們所統治的這片土地上的傳統之美。珀普的熱情感染了禮薩汗,後者開始對波斯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復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授權珀普進入伊朗各地的重要的古蹟和清真寺,利用拍攝和繪圖等技術手段,記錄伊朗古代建築並對它們開展研究。自此開始,巴列維王朝的禮薩汗和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這對君王父子,成為了珀普一生中最重要的支持者。
這次伊朗之行對珀普的一生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除了在考察沿途採購了大量古董和藝術品之外,回到美國後,珀普開始將自己的興趣完全地聚焦在伊朗古代建築與藝術史上。1926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上,珀普被委任為伊朗的特別代表。他和建築師卡爾·齊格勒(Carl Augustus Ziegler)合作,以伊斯法罕的沙赫清真寺(現名伊瑪目清真寺)為原型,設計並建造了波斯館,最終在這屆世博會上獲得了金獎。同年冬天,珀普在費城藝術博物館主辦了一場波斯藝術展。用他的話說,這場展覽是“全世界第一次完全以波斯藝術為主角、深入地展現它的各個方面的嚴肅展覽”。與此同時,珀普主持召開了第一屆國際東方藝術大會,即後來他多次主持召開的國際伊朗藝術與考古學大會的雛形。1930年,珀普在紐約創辦了美國波斯藝術與考古研究所(AIPAA),其宗旨是“從多方面去鼓勵和促進對波斯藝術的欣賞和重視”。在珀普和波斯藝術與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美國學者在巴列維王朝時期的考古工作領域搶得了先機。哈佛大學的弗雷德裡克·武爾辛(Frederick Wulsin)、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的艾裡希·施密特(Erich F. Schmidt)和恩斯特·赫茨菲爾德(Ernst Herzfeld)等人,率先開始在伊朗各地進行考察和發掘。後兩者後來發掘了伊朗最為世人矚目的遺址,即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雄偉壯麗的王都——帕薩爾加德(Pasargadae)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

1932年,亞瑟·珀普和艾裡希·施密特在希薩爾丘遺址,愛德華·瓦爾堡(Edward M. M. Warburg)攝
1929年春天,珀普再次回到伊朗,開始進行禮薩汗交給他的伊朗古代建築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在專案開始時,珀普對使用相機一竅不通,但他很快就熟能生巧,成為了一名頂尖的文物攝影師。在拍攝古代建築和遺址的過程中,溫度、光線、灰塵、日曬、陰影以及裝置本身的侷限和問題,都是需要他一一克服的困難。除了技術和環境因素,即便有禮薩汗的支援,但珀普依然需要與當地的宗教領袖鬥智鬥勇,才能說服他們允許他和他的同事這些非穆斯林進入清真寺,順利地完成拍攝和記錄工作。在1936年9月發行的《攝影》雜誌上,他在文章《因拍攝噴泉被殺!》(Killed for Photographing a Fountain! Camera as a Record of World-Famous Persian Architecture)中,講述了在伊朗進行文物攝影工作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
這是史上第一次對伊朗古代建築和遺址進行的有體系的拍攝、記錄和整理專案。除了珀普和阿克曼之外,還有許多人為這項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包括負責記錄、整理建築物和墓葬表面銘刻的銘文學家法拉傑-阿拉·巴德勒(Faraj-Allāh Baḏl),負責建築和遺址測繪製圖的建築師艾瑞克·施羅德(Eric Schroeder)和唐納德·威爾伯(Donald Wilber),負責拍攝建築並記錄沿途資訊的、暢銷書《前往阿姆河之鄉》(The Road to Oxiana)的作者羅伯特·拜倫(Robert Byron),負責沿途拍攝建築、古蹟,並且首次用影像完整地記錄了波斯地毯織造過程的攝影師史蒂芬·奈曼(Stephen Nyman),以及負責整理和編寫建築物索引的秘書瑪麗·克蘭(Mary Crane)等人。在1929至1939年間進行的共九個季度的考察中,珀普和他的同事們的足跡遍佈了整個伊朗,甚至還記錄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分古蹟。在此期間,波斯藝術與考古研究所的考察隊一共在伊朗各地拍攝了超過10000張照片。現在看來,這些照片可能是珀普為伊朗古代建築與藝術史領域做出的最大貢獻。珀普和他的同僚建立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伊朗文化遺產的影象資料庫,其中有許多照片直到如今依然無可替代。
除了在伊朗對古代建築和遺址進行實地考察之外,在紐約的時間裡,珀普和他的同事們還從事了大量的文獻工作。他們在浩如煙海的手稿和歷史出版物中,尋找和波斯藝術有關的資訊,並且對這些資訊進行分類,在梳理伊朗建築與藝術學術史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已有的認識進行系統化的重組和整合。為了追溯各個設計風格和加工技藝的發展歷程,珀普和阿克曼等人蒐集並繪製了大量圖版,根據能夠確定年代的作品,進行分類和分析,這也與他們在田野考察過程中的工作形成了互補。十年時間裡進行的多次實地考察以及對歐陸各國博物館、學者和收藏家的訪問和調查,極大地擴充了珀普所掌握的伊朗古代建築與藝術的圖檔資源。對這十年考察結果的整理和研究,最終凝結成了1938至193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波斯藝術整合:從史前時代到當下》(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這部鉅作初版共6卷,其中包括2800餘頁印刷精美的文字,內含69個部分共115個章節,以及近1500頁的圖錄,內含3500餘張照片、193張彩色圖版和1966張正文插圖。全書共有來自16個國家的72名作者。在珀普的召集下,當時歐美研究古代東方文明的一流學者,大部分都參與到了《波斯藝術整合》的工作當中。作為編者,珀普和阿克曼二人除了親自參與了許多章節的撰寫以外,他們還將不同背景和觀點的學者們團結在一起,統籌大量的文稿,還將不同的學術觀點聯絡起來,在其中加入了數以千計的內部交叉引用。這些繁複的工作無一不展現了他們二人驚人的效率和創造力,而他們選擇這套叢書獻給他們的支持者、伊朗的“百王之王”禮薩·沙赫·巴列維(禮薩汗登基後的新名字)。面世伊始,《波斯藝術整合》就成為了瞭解伊朗古代藝術的必讀書。在20世紀60年代,在珀普的努力和禮薩汗的繼承者、新的“百王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支援下,這套叢書由伊朗和日本的出版商重新整理、編輯和印刷,完善了30年代初版的種種不足。雖然書中的大部分學術觀點已經過時,但這部凝聚了一代學者心血的《波斯藝術整合》,依然是學習伊朗古代建築與藝術的經典書目,也一直是查閱伊朗古代建築相關攝影記錄的最佳選擇。

初版《波斯藝術整合:從史前時代到當下》(共六卷),牛津大學出版社1938至1939年版

伊朗設拉子的蓋瓦姆酸橙花園,巴列維大學亞洲研究院的所在地和珀普與阿克曼晚年的居住地,基米亞·馬勒基(Kimia Maleki)攝,2019年

在設拉子住所中的晚年亞瑟·珀普,阿薩德奧拉·貝赫魯贊(Assadollah Behroozan)攝
2021年是珀普的140週歲冥壽,距離他的離世也已過去了52年。重新翻開《波斯藝術整合》,再去仔細地欣賞那些精美的攝影作品和手工繪製的說明圖式,我們很難不對珀普和阿克曼做出更加寬容的評價。他們在伊朗古代建築和藝術研究以及文物收藏領域裡所充當的學者、策展人、收藏家、文物經銷商顧問等多重角色,實際上是幫助我們理解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學科和這一型別藝術收藏建立過程的關鍵。珀普在學術上的合作者、中東古代藝術史大家奧列格·格拉巴(Oleg Grabar)形容珀普是一個“活躍在學術、交易和收藏之間紛繁邊界上的出色經營者”。回望珀普的職業生涯,從1925到1969年,可謂是伊朗考古學的傳奇年代。在那個年代,許多考古發現改變了我們對古代伊朗乃至古代世界的認識,也有許多考古發現的過程之曲折離奇,讓人難以置信。同樣地,當時許多重要發現的背後,都隱藏著投機者的私心和殖民主義的野心。這個傳奇的時代,也是現代考古學和藝術史學科意識、標準、經典及方法的形成時期。即便珀普需要揹負近代以來“自西向東”的原罪,但若不將他的經歷置於他所在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背景當中,就武斷地評估他的生活和成就,難免會有失公允。珀普在亞洲研究院的後繼者費耐生對他的評價,或許更值得我們參考:“他(珀普)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但是,即使是他的批評者,也會承認他所擁有的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說服力。”那套一人無法輕鬆抱起、也無法輕易讀完的《波斯藝術整合》,就是珀普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說服力——更重要的,他對波斯藝術及伊朗考古學的由衷熱愛——的最好證明。
1968年春天,時年86歲的珀普依然堅持為他在伊朗重建的亞洲研究院而工作,並且成功地將他42年前創辦的國際伊朗藝術與考古學大會帶到了伊朗本土。這場會議共有來自26個國家的270名學者參加,接連在德黑蘭、設拉子和伊斯法罕三地舉辦。會議期間,後來被譽為“伊朗現代考古學之父”的伊朗本土考古學家埃扎特·納伽班(Ezat O. Nagahban)發起倡議,促使伊朗官方發表正式宣告,反對文物貿易。此後,伊朗境內以商業為目的的考古發掘便逐漸平寂下來。1969年秋天,亞瑟·珀普逝世於設拉子,後被安葬在伊斯法罕的扎因代河畔的一片桑樹林中。伊朗考古學的傳奇年代,隨著珀普的永遠沉默,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果園》的開頭,薩迪這樣寫道:
“哪怕一千聯詩中有一聯可取,也請笑納,萬勿過於挑剔。”

位於伊斯法罕的珀普與阿克曼之墓,基米亞·馬勒基(Kimia Maleki)攝,2019年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