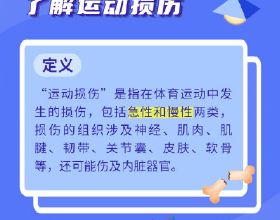講三星堆文明與夏文明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一定會有讀者提出如下問題:
三星堆先民是如何與夏人拉扯上關係的?
位於川西的三星堆文明與鄂西北的某支文明相隔川東、川北和大巴山,它們怎麼會如此相似?
如果不是古籍留下的一些遠古傳說,以及與此相印證的考古發現,使得考古學家重新審視歷史,提出新解的話,或許我們無法就此做出回答。
回答這兩個問題,就意味著要揭開一個深藏了數千年的遠古秘密。
說來話長,事情要從中華上古史的一件重大史實說起。
距今4100多年前。
那時,中國的廣闊土地上分佈著三大民族集團——東部的海岱集團、中原的華夏集團、江漢的苗蠻集團。
當時,堯、舜名震天下,一統天下的事業如日中天。他們部落聯盟的強大武裝,浩浩蕩蕩,一路向周邊掃蕩而來。
真可謂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然而,偏偏有人向他們叫板。那些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傢伙是誰呢?原來他們就是江漢地區的苗蠻集團,因其部落眾多,支系龐雜,歷史文獻上籠而統之,名曰“三苗”。
苗蠻這種行為,雖不能說是“以卵擊石”,但無疑是一種悲壯的舉動。
迫於強大的來自北方的華夏族的持續壓力,江漢地區的苗蠻開始收縮分散的部族。於是,散居在江漢一帶的許多苗民部落開始聚集在一起。他們建立起中心聚落,外圍是無數小聚落護衛著。
部落聯盟首領和軍事領袖還在中心聚落裡修築城牆,建成了一個在江漢地區最大的古城——石家河古城。
在這個古城裡,由部落聯盟的首領們坐鎮。他們授權部落聯盟的軍事領袖,一切戰爭權力都歸屬於他。
勇敢彪悍的軍事領袖,此時成了苗蠻集團中的最高領導。眾人圍著他,他身披獸皮,手握玉鉞,指揮著眾多的苗蠻武裝。他們或手持綁上石斧的木棒,或舉起削尖的木棍、竹竿,分散在中心聚落和衛星聚落裡。他們群情激憤,呼喚吶喊,決心捍衛自己的家園和土地。一些人甚至要求北上去鄂西抗擊準備南侵江漢地區的華夏族軍隊。
江漢苗蠻族面臨的北方強敵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敵人。這個強敵讓任何集團都不敢小視。
這個北方強敵由幾支強勢的部族組成——久經戰爭的炎黃族陶寺人,他們在晉南盆地與舜的族人完成整合,然後由山西南下,在河南與華夏的另一主幹支系王灣三期人完成民族融合。然後,開始向周邊大力擴張。
他們組成的華夏軍隊,各個部落隊伍整齊,人員訓練有素。他們一手持捆綁在木把上的石斧、玉斧,一手持用木頭、皮革製成的盾牌;他們腰佩弓箭。這種遠射武器是用尖銳的石箭鏃和羽杆組成的箭與硬木、竹子做成的弓,在當時,這種武器無疑具有強大的威力。
更要命的是,他們完全聽從於神諭,無條件服從神的指示。上神的旨意,巫師經由占卜知悉,並傳達給每一個人。他們是一個紀律嚴明、目的性明確、頗具執行力的武裝集團。
這樣的武裝集團,令人膽寒。
很快,中原的華夏集團與江漢的三苗集團在今湖北和河南一帶相遇,雙方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事情的起因,歷史上的說法不一:
有人說是堯將天下禪讓給舜,引起了三苗首領的不滿,堯殺了他,引發了三苗人民的反抗。事見《山海經》郭璞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
有人說是三苗在江、漢、淮一帶反覆作亂,威脅到堯、舜的統一方略,致使雙方發生武力衝突。
有人說是因為雙方的宗教信仰不同而引發的戰爭。
上述說法或許都有。不過,可能性較大的,還是宗教信仰問題。
三苗地處江漢,氣候炎熱。據竺可楨先生的研究,5000年前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期,其年平均溫度比今天要高2℃(《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當時的江漢地區約相當於今天的兩廣地區,是泛靈論即萬物有靈論盛行的地方。而盛行泛靈論的族群,不會有通天地傳達神諭的行為,更不會事事聽命於巫師。故史籍記載說“三苗弗用靈”。所謂靈,即巫(繁體“靈”字下面是個巫字。許慎《說文解字》釋:“靈,巫也。”段玉裁注:“楚人名巫為靈。”),即三苗不信巫師,也不用占卜。
從華夏族的祭祀與占卜來看,他們信仰的是天地、山川和祖宗等神靈,而三苗集團的宗教意識還處於很低階的原始宗教階段;從石家河文化遺址的情況來看,苗蠻信仰萬物有靈論,熱衷的是法術,宗教意識還很淡薄。他們對偶像宗教還不怎麼認同。這對於厭惡“三苗弗用靈”、執掌華夏族話語權的華夏巫師和酋邦領袖來說,一定會很不爽,他們很難容忍南邊這些異教徒;何況東邊的海岱民族實力強大,向東擴張易受阻,江漢三苗部落眾多但分散,實力不太強,向南擴張相對容易。
總之,根據歷史記載,華夏族與三苗族之間有過兩次大的衝突。
第一次是在堯、舜時期,堯向華夏族各部及盟友部落發出了聲討三苗族的檄文: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尚書·呂刑》)
堯在檄文之中列數三苗所犯的罪行:不信通天地的巫師,不以神諭行事,濫用刑罰,濫殺無辜;沒有信義,違背盟誓,陷民眾於水火之中。因此諭告天下民眾,將要恢復南正重、火正黎的後裔,使之天地通達,神諭能夠下布,社會恢復正常的狀態。檄文之中所說的重、黎,都是顓頊時的屬官:重為南正,司天以屬神;黎為火正,司地以屬民。兩者都與通天地的神聖職責有關。
堯大義凜然的檄文背後,實際隱藏著的是華夏族一統天下的決心。
最初的戰爭方向,堯選擇在豫西南和鄂西北一帶。這一帶屬於苗蠻集團的邊緣地區,苗民部落不密集,而且文化聯絡也不夠緊密,屬於苗蠻的弱旅。
這個選擇,透露出堯的精明:先攻敵薄弱之處,易於取得戰爭的勝利。
時局的發展也正如堯所判斷的那樣:
華夏族在鄂西丹江口一帶比較容易地打敗當地的苗蠻部落,“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呂氏春秋·召類》)。
戰爭的結果,堯征服了當地的苗蠻族。
這次戰爭的後果與影響,在附近的考古文化中得到反映:丹江附近的淅川下王崗遺址晚一期與晚二期文化出現了較大變異,中原的先二里頭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因素大大增加。
戰後整個形勢也朝著華夏族所想達成的目標轉化: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覆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國語·楚語下》)
江漢地區的三苗,在華夏族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在堯的武力逼迫下,不得不恢復九黎的傳統,而江漢地區重、黎的後裔又重新執掌通天地、傳達神諭的權力。
其後,為了防止被征服的苗蠻部落死灰復燃,重新反叛,舜更進一步強制同化鄂西被征服了的苗蠻,下令他們皈依華夏族。“舜卻苗民,更易其俗。”(《呂氏春秋·召類》)
這種戰爭的後果,考古學家從鄂西地方的考古文化之中得到印證:鄂西土著文化遺存中出土有骨笄,表明當地的土著族即苗蠻族已經被同化,他們像華夏族一樣也開始使用骨笄來束髮,不再使用索帶來束髮(“髽首”)。
不要小看了這一變化。在民族識別上,髮式是非常重要的身份標識。通常,古代民族如果髮式一樣,則表明他們是同一個民族。
歷史上所有想要同化別族或甘願被人同化的民族,都有此經歷。如清軍中的漢八旗,雖原本是漢族,但均要統一為滿族髮式、服飾。清初攝政王多爾袞強迫漢人像滿人一樣剃髮留辮,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被華夏族征服並同化的鄂西地區的苗蠻族群,就是考古學上的青龍泉三期文化的居民。該文化中大量的類似先二里頭文化的陶器的出現,生動地訴說著4100多年前該部落群的重大變故。
鄂西地區被堯、舜征服的這部分苗蠻族,在被“更易其俗”之後,當然就成了華夏族的一部分。就像滿族入關之前的漢八旗一樣,雖然原先是漢人,但入旗籍之後,則變成了滿族。
只是鄂西地區被華夏族同化了的苗蠻族,他們還不能與正宗的華夏族平起平坐,被歸入夏后氏支庶姒姓之中。我們將他們稱為旁支夏人。
雖然勝利了,但堯、舜對苗蠻的激烈反抗仍然心有餘悸。舜為了防止江漢地區另外的苗蠻族造反,向堯建議將鄂西未被同化的苗蠻族遷移到西北的三危山。
我們從文獻中可以看出這個浩大工程的始末:
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史記·五帝本紀》)
這個計劃,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一則所涉及的民族不少,牽扯的人力、物力太多;二則遷徙的路途似乎太過遙遠,尤其是三苗的長途遷徙。舜是否有些異想天開?是否難以執行?
實際上舜的計劃並不太難實現,仔細分析,除了三苗是部族和部落,共工、兜、鯀都是古代部落的首領或重要人物,處理他們,就是將他們的親屬和家人流放而已。鯀是禹的父親,因治水失敗被殛於羽山,既然已經殺死他,還稱之為“以變東夷”,顯然,將其與三苗、共工、兜並列,純粹是司馬遷為了拼湊“四罪”而玩的文字遊戲。
不過,將三苗遷往三危山,卻是真實的歷史事件。此舉透出了堯、舜的精明之處:讓那些不太馴服的三苗族人遠離中原,天長日久,“以變西戎”,斷了他們返回江漢的念頭,華夏族就可以免去三苗的侵擾,一勞永逸了。而且,三危山距離青海湖不遠,湖裡盛產食鹽,讓三苗在那裡採鹽,既控制了重要的鹽資源,又達到流放三苗的目的,可謂一箭雙鵰。
這個計劃是否也與禹有關,今天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對於大禹來說,西北是再熟悉不過的了。“生於西羌”的他,要將這些被打敗的三苗遷徙到西北,首選之地自然是他最熟悉的川甘隴青一帶。所以,我們相信,將三苗遷徙到三危山的計劃,雖是出自舜之手,但禹一定對此有所貢獻。《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說:“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說禹對苗蠻有功德,顯然就是指將三苗流放到三危山,而不是將其趕盡殺絕這件史實。
然而,對於江漢地區“生於斯,長於斯”的三苗人來說,要離開熟悉的故土到陌生的西北去,實在很痛苦。在華夏族武力的威逼下,鄂西地區的部分三苗族被迫遷徙。這一時間,應該是在先二里頭文化時期,即距今約4100年。
三苗的遷徙,揭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向西大遷徙的序幕。
三苗遷徙的目的地,便是三危山。歷史文獻有明確記載:“竄三苗於三危。”(《尚書·舜典》)
但是,更多的三苗族並不願意,他們奮起反抗。舜為了壓制三苗族,親自率軍征討,結果“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舜征討三苗,並未真正將三苗打敗。故《禮記·檀弓下》“舜葬於蒼梧之野”句下鄭玄注:“舜徵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是說舜在登高時突然死去。
舜未完成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了禹的肩上。
不久,為了強行將三苗趕到西北去,華夏族與三苗族的第二次大規模戰爭開始了。
這次戰爭發生的原因,文獻上有記載,說三苗為政不善,致使禹興兵討伐。
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恃其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戰國策·魏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作為禪讓制度的受益人,繼承舜所禪讓帝位的禹,成為華夏各部族的共主,理所當然地要繼承堯、舜統一天下的遺志。
由於此次是與江漢地區苗蠻集團進行大決戰,事關重大,禹必須全力以赴。
禹下定決心,召集華夏各個部落及其姻親部落——來自山東的有緡氏、有仍氏,秣馬厲兵,準備決戰。
盟誓之時,禹發表了重要的講話:
濟濟有眾,鹹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徵有苗。
禹用簡潔有力的話語,向華夏族及盟友、姻親部落發出了向苗蠻集團宣戰的號令。這就是中國上古史上非常有名的一篇宣言——《尚書·禹誓》。
公元前2070年,時機一到,禹親率大軍,征伐三苗族。
當時戰鬥的情形異常慘烈,雙方打得天昏地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墨子·非攻下》記載了這次衝突:
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徵有苗也。
處於鬆散聯盟的三苗族哪裡是久經炎黃戰爭考驗的華夏族的對手?
終於,三苗族大敗,潰亂四散了。
三苗族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我們從古代的一些史籍中能夠看到這次戰爭帶給三苗族近乎覆滅性的創傷:
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國語·周語下》)
華夏族與三苗的兩次大戰爭,均以三苗的大敗和崩潰而告結束。
【摘自:《三星堆:開啟中華文明之門》作者/範勇 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