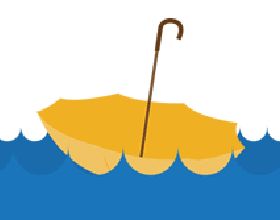李雪牙/文
寫在前面的話: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進工廠當一名工人是件幸事,謀得一個好工種又是幸中之大事。好工種能帶來好運,能找到好老婆。
本文中的萬道友就吃盡了工種的苦頭,如若不信,且看下文:
畫師萬道友,退休前是一家大型機械廠一名電焊工。開始,他並不是幹這個,而是鍛工。鍛工就是打鐵,一個月的口糧都比別的工種多10來斤。打鐵的名聲不大好聽,俗話說:人生三苦,撐船、打鐵、磨豆腐。
萬道友深知打鐵的高風險係數,這個高風險不是別的,而是直接影響到找女朋友。
果然不錯,一個叫伍蘭花的女孩闖入了他的視線。據介紹人說,這個伍蘭花系文藝青年,特別是舞跳得好。
就憑這一點,把萬道友的胃口吊得老高。因為,萬道友在校期間就是文藝宣傳隊的,除了管樂,什麼二胡、小提琴等絃樂都可對付。由於跟音樂接觸多了,好像他也變成了藝術人:幾個月不上校理髮室,頭髮長得要披肩,加上他那1.75的個子,就形象而言,在男同學中間還算得一個。
萬道友偷偷地看了伍蘭花一次演出。他被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深深地吸引住了。幾次花前月下,她對他也頗有好感。
“你們廠有多大?”
“光職工就有8000~9000,如果把家屬也算在內,只怕有好幾萬!”
“哇塞,這麼大?”
“那你在廠裡是幹什麼的?”
“我是幹鍛工的。”
“鍛工是幹什麼的?”
“鍛工是……”
在伍蘭花搞清楚鍛工就是打鐵的以後,他(她)們的對話就再沒有進行下去了。
結果,介紹人傳過話來說,這個廠子是個好廠子,就是打鐵的不行!
一氣之下,萬道友去理髮店剃了一個光頭,以銘志:不混出個人樣,決不談女朋友。
70年代中期,廠裡有3~4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厂部還算開明,將這4個名額全部向他們一線傾斜。他們車間分到一個,萬道友爭取到了,表也填了。他家裡的終於出了一個大學生,人情份子錢也收了,酒也辦了。
誰知道呀,厂部政治處領導找他談話:
”萬道友同志,這次你不能去,打鐵崗位人手那麼缺!”說後,這位領導送他一沓入黨學習材料:
“把這個學習材料看看吧,我會同你們車間支部打招呼的!”
又是打鐵這個崗位,像個木塞子一樣,嚴嚴實實地將他上升通道給堵死了。回來後,他將那位領導送的學習材料,放到了一邊,連翻都沒有翻一下。也許,萬道友在不知不覺中犯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因為他沒有順著領導的杆子往上爬。
大學沒有去成,領導拋過的杆子沒有爬,上天給的機會是有限的。萬道友就只能在社會底層,隨著芸芸眾生的洪流,滾到哪裡算哪裡了。他依然是這個大廠子裡的鍛工,依然幹著打鐵的活。
這就是一般人的命。
一次,班組一個同事揹著一根直徑50的圓鋼過來,他為了躲開空中的行車,一不小心圓鋼直接捅到了萬道友的左腰子上。一陣天昏地暗,他住進了廠醫院,痛定思痛:
鐵是萬萬不能打了。
換工種談何易,有如現在的大學換專業。
領導還是同意了他換工種的要求,但是必須要他找一個人對換,否則免談。恰好,隔壁車間有一個農村頂職來的小夥子,他是電焊工。帶電的工種有多好啊,但是他不想幹。他主動要求去打鐵,究其原因:他圖的是打鐵的口糧,他經常吃不飽。
謝天謝地,萬道友終於摔掉了“打鐵”這頂帽子,幹起了電焊工。
“萬道友,你工種是換了。但是,你這個名字還是打鐵的名字。不信,你看喔,我們師傅算是我們打鐵的老前輩吧,他叫胡先道,帶個’道’字;你的師兄叫付先友,帶個’友’字是吧。他們兩個加起來就是你的名字道友了。你把這個名字改了吧,除非你還想回來。”一位工友善意地提醒著。
名字是換了,叫“萬一達”。他有一萬個理由,一定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什麼目的?他沒有想好,先把名字改了再說,反正不能跟打鐵行當有一丁點聯絡。
那個年代凡是帶電的工種都走翹,他輕而易舉地找到了老婆。究其原因,除了他個人的形象外,而且一個重要的因素:他的工種帶“電”。
大概是五年前,萬一達遭遇到了“滅頂之災”,醫院斷定他為腎癌。那段日子,他感覺到自己一隻腳已踏進了閻王殿,就差沒點他的名字了。一句話:他嚇得半死。
無影燈下,一個跟隨他,忠心耿耿為他服務了近70年的左邊腰子(腎)被“咔嚓”切下來了。在醫生的提醒下,他記起來了,這個腰子曾在打鐵的時候受過傷。他孃的,又是打鐵闖的禍!他在心裡罵道。
開始,萬一達對醫院,特別是視主刀醫生為再生父母。後來,竟不是這會事,什麼癌根本與他不打界,是誤診了。有什麼辦法呢?那個腰子已經沒了。
現在,但凡有人問起這個事,他一臉的無奈:
“一切都是命,都過去了。”
喝茶的時候,同學問他要什麼茶。他擺擺手:
”不喝,不敢!一個腰子負擔重啊!”
不過還好,他說,現在除了不舉,兩到三次夜起外,其他沒有大礙。有人不同意了:不舉,這個事還不大啊?他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哎,老夫老妻了,還講這個!
具體是什麼時候,萬一達愛上了畫畫的,沒人能夠知道。按他自己的說法,光畫畫工作室有兩個。他主攻的是國畫。
一次,同學們受他的邀請都來了。聚會上,他展示了畫作。
“我這個畫是給懂畫的人看的。”他這句話一出,嚇得絕大多數同學都走開了,唯恐避之不及,因為大家都不懂畫啊!
當然,出於禮貌,還是老遠拿著手機“咔咔”地照著。至於照沒照到,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吃了萬一達的,喝了萬一達的呀!
還有,一位跟他過往甚密的領導老母親90大壽,他畫了一幅畫作。他拿著這幅畫,請書法大家蔡明華同學題詞。明華是什麼身價?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一字值千金吶。明華反覆將他這幅畫,左看看,右看看。最後說:
“一達同學,你看這樣好不?你先請我們的作家黎平臺,把要題的內容寫好,用微信發給我。”
一頓電話下來,平臺同學出去採風去了,沒十天半個月,不會回來。
無法,他將這幅畫裸送給人家了。後來,他再去這位領導家的時候,樓上樓下找了個遍,就是沒有他的那幅畫。
畫的水平不怎樣,上面的墨寶題詞也沒有。裸畫豈能等同裸體?領導當然不會掛的了。他認為蔡明華不講同學情分,對此老是耿耿於懷。
現在的蔡明華一般都閉門謝客,要字的人太多了。同學們都知趣,都不去煩人家。明華成名後好多事都是聽說。好比,他的二婚。他現在的老婆是誰,漂不漂亮,沒人能說得出來。
蔡明華能在百忙之中接待萬一達,並指點一、二,已屬難得。
腳盆洗臉面子大,萬一達還怪罪於人,這就有點過了。
後來,他才發現:自己的畫作還沒有上路。
再後來,據說他上路了。路走多了,也就有路了。
又後來,“畫師”這個稱謂叫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是畫師了。
現在叫萬一達,後面不加畫師兩個字,他不一定會搭理你。就跟XXX院士打招呼,後面如若不加個院士,就顯大不敬一樣。
又是在同學蔡明華——這位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的斡旋下,該市文化藝術館,終於同意萬一達的畫作展出了。同他一起展出的還有書法作品。
這個展館樓地兩層,每層近500平方。萬一達的展位設一層,只佔一半;另一半是留給書法作品的。在進展館的左前方有一標牌,很大。其目的旨在提升作者(家)的知名度。上面寫什麼?萬一達和蔡明華想到了作家黎平臺。黎平臺對萬一達是這樣表述得:打鐵的命,繪畫的運——工人畫師萬一達作品展;對蔡明華委託的那位書法作品展是這樣表述:纖纖玉手,揮毫潑墨,橫直是春秋——玉蘭書法作品展。
現在一切都是有償服務。所有展出費用,包括另一半的書法作品展場地,萬一達一肩挑了。這是事先同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蔡明華同學說好了的。否則連門都沒有,他心甘情願。第二天就要開館展出了,他連絡了好些同學舊友。
“明天展館見!”
”展館見!”
這一夜,萬一達幾乎沒睡。這是個月圓之夜,月兒在天上像是躲貓貓一樣,時而從這朵雲裡進,時而從那朵雲花兒出。明明暗暗的夜空下,那螢火蟲三五結隊,不知疲勞地飛來飛去,留下了一絲絲,一線線的銀色光來。那遠處的池塘邊,蛙聲此起彼伏。這一切,都好像在向萬一達昭示著什麼。是的,他正在拖著春天的尾巴,他已看到了曙光。他的繪畫水平肯定會越來越好,有了明天這個平臺,他將會飛得更高、更遠。
萬一達身著一件西裝,這件西裝做工特別地精緻,麻灰色的。一根紅色的領帶,頭髮還是那麼長,由於時光的侵蝕,有一半的頭髮都花白了。他那個作派,往門口一站,儼然一位老藝術家,讓人肅然起敬。
這個時候,他的幾位女同學到了。其中一位服裝設計師叫李末子的走過來,一手就逮住了他那件西服說:
“都什麼年代了,還穿鬼佬二手貨?”
另外一個女同學則毫不客氣的掀開這件西服口袋那邊,一看:喜二郎。
“哈哈哈,好一個藝術家,你也太那個了點吧!”
等大家笑夠了,他那副老臉似乎有點泛紅了說:
“這好久好久以前,我老婆給我買的,我看還可以就穿來了,沒想到被你們行家識破,實在不好意思啊!走,走,裡面請……”
萬一達一走進展館,一個相當眼熱的女人映到了他的視線裡。他沒有馬上過去,他站在這位女人大概兩米遠的地方,仔細地上下打量著:沒錯,是她,就是她:伍蘭花——他的初戀。
這個時候,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蔡明華過來了,他拍了一下萬一達:
“來,我來介紹一下。”
隨即,他就對正在看畫的女人一招手:
“來,來。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我的同學,他叫萬一達,是這個畫展的畫師,同時又是這個場地的贊助商。”轉過臉,他又對萬一達說:
“這位是我的老婆——伍蘭花女士,今天展出的書法作品是出自她之手。”說完,他笑眯眯地看著萬一達和自己的老婆。
伍蘭花很自然地伸出手來,萬一達卻木納地、機械地將手伸了過去。
“久仰、久仰。我時常聽我家先生提起過你,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她那灑脫的神情,絲毫也看不出,她跟萬一達有過什麼戀。
“小孩子過家家,過家家……玩泥巴!”萬一達十分勉強地、一語雙關地說。
萬一達一萬個沒想到蔡明華玩得這麼深,佩服啊,佩服!他想起了作家同學黎平臺那句張貼在標牌上的廣告語來:打鐵的命,繪畫的運!真是入木三分吶!這就是他,一個曾經的老鐵匠,萬一達的命運。
2021.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