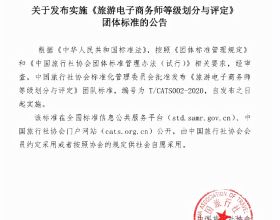黎軍在一個建築工地打了半年工,到頭來沒有拿到一分工錢。現在他困得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了。沒辦法他只好到一家飯店洗盤子買菜,工錢每天30元,當晚結賬,老闆還管吃管住。
這天,他蹬三輪車去城郊買菜,在一個人跡稀少的路段發現一隻包。他忙下車拾起,開啟一看,裡面有8千元現金和一張合同。那合同的甲方是興華機械廠,法人代表叫陳斌,乙方是個叫伍洪民的機器零件加工戶。合同規定乙方伍洪民為甲方加工5萬元的零件。這8千元錢對黎軍來說,那可真是一場及時雨,沒有人再比他更需要錢了。老孃有病需要錢,兒子上學也需要錢,有了這8千元就能解決很大問題。
三天後,還是在買菜回來的路上,黎軍在拾包附近的電線杆上見到了一張招領啟事。啟事上寫道:本人收到一張欠條,債務人也就是寫欠條人,是興華機械廠的法人陳斌。債權人也就是持欠條人,是伍洪民。欠款金額5萬元。欠款緣由是,伍洪民給陳斌加工零件。請伍洪民見到啟事後,立即前來領取。啟事的最後是拾欠條人的地址和聯絡電話。
看完啟事,黎軍忙用筆記下拾欠條人的地址和電話。黎軍心想,這伍洪民太粗心了。他又想到,他撿到的那個包裡的那張合同。合同是伍洪民給陳斌加工機器零件,加工費正好是5萬。
由此可知,一定是伍洪民給陳斌加工好了機器零件。當時,陳斌沒錢,就給伍洪民寫了一張欠條。可惜這個粗心的伍洪民,竟然把5萬元的欠條給丟了。黎軍還推測出,他撿到的那個包很可能就是伍洪民的。
沒有等回到飯店,黎軍就用大街的公用電話,按照啟事上的號碼打了過去。接電話人說,他確實拾了一張欠條。黎軍問,是否必須持伍洪民的身份證,才能領到欠條。對方回答說不一定,只要有證據就行。這證據必須足以證明認領者就是伍洪民。黎軍又問,是否已經有人前去認領。對方說,到目前為止還無人問津。
又等了幾天,黎軍又打電話問拾欠條人,是否有人前去認領。對方的回答與上次一樣,至今仍無人認領。
這天,黎軍趁外出買菜的機會,按啟事上的地址,找到了拾欠條人。拾欠條人說他叫陸建一,還拿出欠條讓黎軍看了看。黎軍看到,欠條上不但有欠款人的簽字,還有欠款人的地址及電話。黎軍將那張伍洪民與興華機械廠的合同給陸建一看了。
陸建一說,他相信黎軍就是伍洪民,他願將欠條還給黎軍,但黎軍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因為現在是市場經濟,全社會都市場化了,當然也包括做好事。黎軍問他要多少錢。陸建一說,這張條子是5萬,你少說也得給1萬。
黎軍問能否少點,陸建一說,9千元一口價,再少了免談。黎軍又費了好多口舌,陸建一才又讓了一千,8千元不能少一分。黎軍又看了看欠條,將興華機械廠的電話記住了,之後,說,今天沒帶錢,改日再來。
第二天,黎軍又趁外出買菜之機,又用公用電話給興華機械廠打了電話,接電話的是陳斌。黎軍問陳斌,他是否欠伍洪民的錢。陳斌說,他確實欠伍洪民5萬元的加工費,但現在伍洪民沒有欠條了,不見欠條他是不會給錢的。黎軍問伍洪民的住址,對方很不奈煩地說不知道。黎軍本來想掛了電話,不料陳斌又語氣極緩和地說,不管是誰,只要能拿來欠條,他都會給錢的。不過,若持欠條討債的不是伍洪民,他將不付全額,只要能將欠條交給他,他最少給3萬元。黎軍想,這陳斌也夠黑的了。
黎軍思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用拾來的8千元去換回那張欠條。黎軍懷惴8千元撿來的錢,又一次來到陸建一家。陸建一很爽快地與黎軍完成了這場交易。
黎軍丟下8千元現金,拿走欠條後,陸建一高興得一蹦三尺高。
這是為什麼呢?難道這個陸建一就沒有按欠條上的電話號碼,給陳斌打過電話,問陳斌有欠條能否討回些錢?
提這個問題的人,是他不知道陸建一就是陸減一,陸減一就是伍,就是伍洪民。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聽我慢慢說來。
伍洪民丟了包,丟了錢,心裡不好受,就把事情跟好朋友、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陳斌說了。伍洪民沒有想到,陳斌很輕鬆地說:“這個錢,找回來非常簡單。我能讓你的8千元失而復得。”
伍洪民說:“你不是在說夢話吧,你能有這個本事?”
陳斌說:“我說簡單,就是簡單。你包裡除了有8000塊錢,還有咱倆的合同。拾包的人,一定會仔細地看我們的合同。我們就利用這個合同,把錢哄過來。俗話說,打死人償命,哄死人不償命。”很快,陳斌就設計出一個無懈可擊的方案,等著拾錢人揣著8千元往坑裡跳啊。當然,陳斌在這場戲中演得也十分出色,配合得天衣無縫。
8千元失而復得後,伍洪民與陳斌,除了沒事偷著樂之外,還在等著比弱智還弱智的黎軍拿欠條去找陳斌討債呢?然而,令他們大惑不解的是,陳斌卻從來沒見過黎軍的影子。
一個月過去了,不見黎軍;一年過去了,仍不見黎軍。
一轉眼兩年多過去了,伍洪民的生意像滾雪球一樣。由原來的小小加工戶,發展成了一個小型加工廠。這期間,伍洪民不但沒見過黎軍的影子,就連他的訊息,也沒聽說一星半點。起初,他與陳斌還不斷提起傻瓜黎軍。每次提起他,他們都會為黎軍的傻,笑得肚疼。後來,他們就覺得黎軍這人,不但傻還有些怪,既然他舍花8千元換回一張假欠條,可他為什麼不去找陳斌討債呢?再後來,他們就漸漸地把黎軍忘掉了。
伍洪民的業務擴大了,需要人手多了,現有的員工不夠。於是,就在報上發廣告招聘員工,幾天來不斷有人前來應聘。
這天,來了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伍洪民以為他是來應聘的。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這個年輕人見到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伍洪民?”伍洪民心想,你作為一名應聘者,怎麼能這麼跟我說話?你太沒禮貌了,於是,就不客氣地回答道:“我是伍洪民,怎麼啦?”
當年輕人確信,眼前的人就是伍洪民時,他一把抓住伍洪民的雙手,說:“你讓我爹找得好苦啊。”伍洪民一頭霧水,如墜氤氳,驚得張大嘴巴,不知該說什麼,半天才問:“你爹找我?你爹是誰?我怎麼不認識他?”
年輕人說道:“你當然不認識了,他也不認識你。”“那他找我幹啥?”“他要給你送欠條。他拾了你的包,包裡有8千元現金。後來又用這錢,換來一張陳斌給你打的欠條。他費盡了周折也沒找到你。上個月,他因患病沒錢治療……。
臨終前,他千囑咐萬叮嚀要我一定找到你,把條子還給你。因為欠你錢的陳斌不見條子不還你錢。”
伍洪民接過他自己寫的這張欠條,一時心潮翻湧。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張欠條竟讓一位素昩平生的人,為此付出了這麼多。“這裡還有我爹寫給你的信。”伍洪民展開信紙,急切地看了起來。
伍洪民:我已沒有時間再找你了。但我死了,也要讓兒子千方百計找到你。請原諒我,沒有得到你的允許,就自作主張把你的8千元動用了。因為我在買欠條之前,打電話問過陳斌了。他太黑了,我不這麼做,你的損失會更大。拿到欠條後,我去陳斌廠裡問過你的住址,但沒有問出來。他的員工不願搭理我,粗暴地將我趕走,說他們廠壓根就不曾欠你的錢,我拿假欠條去胡鬧。而陳斌,我根本就見不到。他的員工就不容我問半句話。
我知道,這是陳斌事前安排好的,他指使他的員工將我趕走,他就可以賴掉欠你的錢了。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再去陳斌那裡。這三個月,我天天都為找你奔波。我在飯店打工,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打聽你。卻一點訊息也沒有。就在我為找你而著急時,飯店老闆告訴我,說我家人給他打電話了。家人說,我父親有病,讓我趕快回去。
回到了家,我說了我正找你,要還你欠條。孩子他媽說:“乾脆你拿著欠條,去找陳斌,讓他給你3萬、2萬也行。現在爹的病正需要錢,沒錢爹的病就看不好,可能就會要命。”
我說:“那不行啊,這不是咱的錢,咱不能花。我一定要找到伍洪民,把欠條給他,讓陳斌把他的5萬元還給他。只有這樣,我死了才能閉上眼睛。”最終,爹的病因無錢治,把命要了。這段時間,我既要照看爹,還要打工掙錢,還在想如何找你。就這樣,我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我病倒了。在病床上,我隱隱約約地聽到,我兒子和他娘說:“乾脆把爹手裡的那張欠條拿到手,去找陳斌要錢。他給多少都行,總比現在一點沒有強。”我非常體諒他們娘倆的難處。我們家現在太需要錢了。沒有錢,我可能會和我爹一樣,很快就會走進墳墓。但是,我一直執著地認為,這個欠條必須給你。不是自己的錢,自己是不能要的。我一直在想,陳斌賴你5萬元,這對你是多麼大的損失啊!你是小小的加工戶,一下損失5萬元,怎麼維持下去呢?
我想到這裡,就把兒子叫到我的床前,對孩子說:“兒子,我有句話要對你說。你一定記住我的話。這個伍洪民的欠條,我們一定要想辦法給他。就是我死了,你也要繼續找下去。你是孝子的話。就聽我的話。你要是不聽我的話,我現在就吃安眠藥,死給你看。”
我兒子非常孝順我。我的話他句句都聽。這是他從小就養成的習慣。剛才他和他媽說的那些話,那是我們家的日子實在太需要錢了。我相信,我死了以後,我兒子一定能夠找到你,把你的欠條還給你。兩年來,為找你,我誤了不少工,費了不少的周折,可我覺得值。遺憾的是,一直沒有找到你,這任務只好讓我兒子來完成了。由於我沒有及時給你欠條,肯定會誤了你討債,所以,我再次請求你的原諒和寬恕。
伍洪民再也看不下去了,多少年來從沒流過淚的他,此時早已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