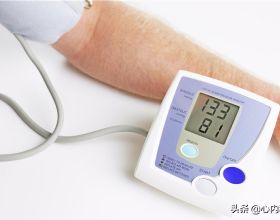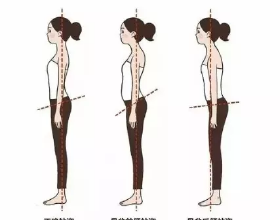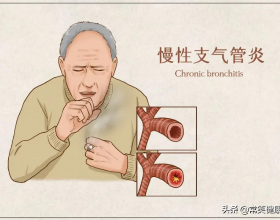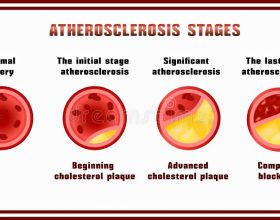髙炮67師(在越南抗美期間叫67支隊),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得到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嘉獎。
打過美國偵察機,保衛過西北核試驗,參加過援越抗美戰鬥,是一支英雄的部隊。能夠成為其中的一員,是我終生的榮耀。
部隊的英雄事蹟早己載入史冊,現將生活中的那點鮮為人知的小故事彙集幾個,以窺當年的青年軍人的情懷。
火車情緣
55年前的張參謀是一個人見人愛,花見花開的青年軍官。學校剛畢業,中尉軍銜。
春節前夕,經領導批准,第一次以軍官身份回老家長春探親。
火車上人不少,但都有座位。張參謀穿著軍裝,按票上的指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來。
這一坐不要緊,立即變成了整個車箱的焦點,不論男女老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往他這裡看一眼。英俊瀟灑,鶴立雞群。
車開動了。不一會,年青漂亮的女列車員來送開水,大大方方地看著張參謀,滾開的水倒滿了一瓷杯。還不忘鶯聲燕語地說一聲“同志,請喝水”。
張參謀望著列車員遠去的背影和嫻熟的倒水動作,心裡想,真漂亮。列車員的身影消失在車廂盡頭,張參謀扭頭望向車窗外,樹木田野,全都排著隊向他奔來,又奔向身後的遠方。想起父母,想起父母來信說有人要給他介紹物件,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做什麼工作,也像這位列車員一樣勤快漂亮麼?
正在出神,“同志,看看你的車票”,女列車員查票。張參謀從上衣口袋裡掏出車票,遞給她,她接過車票睨了一眼,“去長春,明天早上到”。張參謀接回車票的時候正目去看列車員,不想列車員也在看他,瞬間紅著臉低了頭。
列車咣噹咣噹地走,列車員來來回回地忙,打掃完衛生送水,送完水又打掃衛生。每次擦地板路過時,張參謀都會禮貌地站起到一旁。擦完地板列車員姑娘也會客氣地請張參謀坐下。
天黑了,張參謀去餐車吃完飯回來空坐著無聊,便拿出一本書來看。夜深了,列車過了瀋陽。張參謀困了,卻不敢睡,怕坐過了站。列車員姑娘讓他睡一會兒,說到站叫他。
張參謀放心地趴在小桌上睡著了。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隻潔白的白天鵝帶著他在天上飛,飛到白雲上邊,看見遠處的大山披著金光。
“嗚……”,氣笛聲驚醒了他。天亮了,太陽正好曬到面前的小桌子上。往窗外望去,長春站的站牌從眼前緩緩滑過。不好,過站了,張參謀急忙站起來要往外撞。列車員姑娘連忙過來攔住他,一臉誠懇地向他道歉,說是忘了叫他了。
怎麼辦?列車員提議他坐到哈爾濱,休息一晚上,明天還跟這輛車回來。張參謀沒了主意,只好照辦。因為是列車員姑娘的錯,便一路上盡心盡力照顧他。把自己休息的鋪位讓他休息,到點給他打飯。
這回列車員姑娘好像沒有開始那麼忙了,總有時間回到休息車廂與張參謀聊幾句。列車長也來看望了張參謀,除了表示歉意外,還聊了些家常裡短。軍人實在,幾句話就把父母的工作,家中人口以及自己的基本情況全說出去了。
列車回到長春之前,張參謀對列車員姑娘產生了好感,說是要感謝列車員姑娘一路對他的照顧,要了姑娘的通訊地址和電話。當然,也把自己的通訊地址和電話給了列車員姑娘。並且約定,歸隊時還坐她跑的車。
歸隊時,列車員姑娘遠遠地等在車廂門口。張參謀穿著便衣,拿著大包小包,其中有一個是張參謀的母親帶給列車員姑娘的禮物。一路上,張參謀跟著列車員送水,擦地板,為旅客們做好事,嚴然一位英俊勤快的男列車員。
後來,這位女列車員就變成了他的老婆。
我認識張參謀的時候,他已經有兒子了。他老婆到部隊探親,是我見過的家屬裡頂尖漂亮的。
有戰友問他,你是不是故意坐過站的?他說不是,是老天安排的。
戰友們幫忙
1960年前後,部隊駐地在山東益都,也就是現在的青州。營房好象在縣城西邊的一個小山頭上。
宣傳科的幹事們絕大多數都結婚了,只剩下一位姓秦的幹事還是光棍一條。
他是大學畢業直接入伍的軍官,學生氣很濃,為人靦腆不愛說話,不愛參加社交活動,有空就讀書,寫得一手好字好文章。
20大幾的人還沒物件 ,往往是父母同亊都操心的事。科長也時不時地問問,偶爾會前會後還會對科裡的其他幹亊說,你們飽漢子不知道餓漢子飢,眼看秦幹事這麼大了,也不知道想辦法幫幫忙。大家覺得科長說得對,但都是軍人,與地方上接觸少,手裡沒有資源,也是沒法。
這天是週六,過完組織生活,幾位幹亊湊在一起商量這件事。有人提出去縣城找找,就不信這麼大的益都城給秦幹事找不到一個物件。於是決定週日去縣城海捕。
老幾位換上便裝,吃完午飯一人一輛腳踏車就出發了。一路走一路商量先去哪裡。其中有人建議,女同志比較多的單位是醫院和紡織廠,咱就去城北的大橋上等,看到合適的再說,於是幾位就上了大橋。
大橋是拱橋,過橋上坡,女同志力氣小,往往推著車走,方便觀察。
過來一位姑娘,一人問,行不行?大家都搖頭,又過來一位姑娘,又問,又搖頭。看了20多位了,沒一位中意的,眼看太陽要下山了,都快要失去信心了。突然一位姑娘推著車子由北向南上橋,老幾位眼晴一亮,都直勾勾地盯著姑娘看,誰也不說話。眼看姑娘過了橋頂騎車下坡了,幾乎齊聲說“追”,幾位追著姑娘就下去了。
走大街,過小巷,左拐右拐,緊追不捨。眼看著姑娘下車進了一處小院子,想必這就是姑娘的家了。
幾位商量好,以討水喝為名,進去了解了解情況。進門一打聽,家裡就母女倆。老太太聽說來了幾位路過的解放軍討水喝,忙喊女兒倒水。幾位一邊喝水,一邊與老太太套磁,三套兩套就套出了姑娘的基本情況。衛校畢業,縣醫院當護士,還沒物件。
說到物件,老太太也為女兒的婚亊操心,拜託他們在部隊幫忙物色。一槌砸到鼓心裡,相互留下地址電話,幾位髙高興興地回了營房。先給科長彙報 ,再通知秦幹事下週去相親。
下週日,幾位拉上秦幹事,買了點水果點心,以感謝為名去姑娘家相親。老太太是過來人,一看來人中有一位生臉兒,心裡就有了幾分數。先是招呼大家都坐下,吩咐姑娘泡茶。一把茉莉花茶沫兒放入大茶壺內,滾開的水一衝,立即香盈滿屋。又拿出花生瓜子招待大家。老太太把那個面生的秦幹事拉到自己旁邊坐下,對秦幹事說,“上次他們來好像沒有你”,秦幹事立馬臉就紅了。戰友中年長的趕緊對老太太說,“您老真好眼光,好記性,上次沒有他。他呀,姓秦,我們科裡歲數最小的幹事,很能幹,領導很器重。今天我們來感謝您,特意把他帶來,讓大娘您認識認識”。大娘聽了老幹事的話,心裡有數了,兩眼便不離秦幹事臉上身上看,嘴裡還招呼女兒倒水。
姑娘倒了一杯熱水雙手遞給秦幹事,秦幹事趕緊站起來雙手去接,不小心四隻手碰到了一起,兩個人都感覺像觸了電一樣。雙雙一鬆手,水杯掉在桌子上,水灑了一桌子,也灑了秦幹事一身。
大家看到這一幕,都覺得有門兒。老幹事乘熱打鐵,對大娘說,“這天也不早了,我們現在回去也趕不上飯了。我去買點菜,我們這裡有會做飯的,今天這飯您就管了唄”。
大娘樂的嘴都合不上,一連說好。還說,“你們都離家遠,就拿大娘這裡當家吧”。
於是分工合作,很快弄出一桌豐盛的午宴。大娘拿出老頭子留下的益都大麴,熱熱鬧鬧地開飯。秦幹事初次與姑娘見面,始終拘謹著,靦腆著。
以後的幾個星期日,大家又陪秦幹事去了大娘家幾趟,再後來就推託有事,讓秦幹事一個人去了。
從此開始了一年左右的戀愛,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了。
我認識上文所說的秦幹事時,他己經是我們團的宣傳股長了。他媳婦也隨軍到了濰坊,在濰坊的一所醫院上班。一兒一女兩個孩子,老太太跟著他們幫忙做家務,生活幸福著呢!
老隊長的拉菲克
1973年,部隊駐在太原,衛生隊迎來了新任老隊長。這位老隊長1949年參軍,是解放兵,也就是從國民黨部俘虜過來參軍的。
他老家是山東的,具體哪個縣不記得了。他說當年他在老家被抓了壯丁,直接編入部隊被送到上海。上海解放的時候,他們一個團像沒頭的蒼蠅在上海亂跑。最後跑到江邊,大家擠著上船逃命。他被人擠倒了,掉到江裡,以為要死在江裡喂魚了。被咱們部隊救了起來,從此成了解放軍的一員。
部隊看他年齡小,才16歲,就讓他當了衛生員,後來又送他去軍校培訓。畢業後,恰好我們師在山東益都組建,他被分配到衛生科,成了軍醫,授銜時授了少尉。
那時候部隊經常組織幹部與地方的醫院或學校聯歡,這些聯歡活動客觀上起到了解決大齡幹部們婚姻問題的作用。老隊長就是此時認識了他的“拉菲克”。
他老婆是個大個子,長得黑,五大三粗,一點也不像個大學生,有點像後來那些年所說的鐵姑娘。老隊長有一次提到他媳婦時說,“我第一次看見她就想,這個大個子,黑乎乎的,真帶勁”。老隊長的媳婦在益都縣是某個局的局長,一直沒有隨軍。老隊長年歲不小了,身體也發福了,成了一個矮胖子,卻依然是牛郎織女,每年兩次鵲橋會。
1974年春天,老隊長家屬來部隊探親,給戰友們帶了不少高粱飴。好多人不認識這個“飴”字,就叫做高粱臺。
那時候我跟老隊長住同一宿舍。一天晚上,老隊長回宿舍拿東西,對我說“槍不行了”。我那時還是個生瓜蛋子,就說,“放這兒吧,明天我去軍械股找他們修”。老隊長笑著在我頭上給了一巴掌,然後就去藥房了。當時不明白,心想老隊長咋回事兒。結婚後才知道老隊長說的槍是什麼。
老隊長長我16歲,算起來現在小90歲了。多方打聽,訊息全無,不知道還在不在了。
沙漠中的坐懷不亂
1965年冬天,部隊在西北大沙漠中執行絕密任務。通訊地址為蘭州市xxx號信箱,實際駐址在1000公里以外的沙漠腹地,條件之艱苦,出行之困難可想而知。
這天是週六,楊幹事去郵電所發信。郵電所在離部隊駐地大約10華里的地方,孤零零的一幢磚混結構的平房。平時一共有兩位工作人員。
這天下午天氣特別好,大太陽曬在地面的沙子上,亮晶晶地閃著光。沒有一絲風,暖和得穿不住棉襖。看著天好,郵電所的一位同志騎著跨子去鎮裡辦事,留下一位女同志守門。
楊幹事走到郵電所差不多5點左右了。沙漠上黑得晚,常規情況下,辦完事趕在太陽下山前回到部隊沒問題。
這一天偏偏就來了個特殊情況。楊幹事忙完十幾村信的郵寄手續後,突然就覺得天黑了下來。兩人出門一看,不得了,西北天邊一堵黑黃的牆頂天立地向郵電所撲了過來。
女同志大喊一聲不好,黃毛風來了。楊幹事第一次見這陣仗,不知道害怕。再說自己一個軍人,當著一位女同志的面,害怕也不能表現出來。
楊幹事拔腿要走,想盡快趕回部隊。女郵電員知道厲害,一把拉住楊幹事。你絕對不能走,這風說話就到,風沙一刮,最容易迷路。一旦迷了路,夜裡沙漠上溫度很低,凍也把你凍死了。再說,我們那位同志肯定回不來了,你走了,留下我一個人怎麼辦?
說著,風沙就到了。天黑得對面看不見人,風大得站不住,沙子一個勁兒地往眼睛、鼻子裡鑽。趕緊進屋,找東西加固門窗。
楊幹事心想,多虧這位同志攔下我,要不這回就交待在沙漠裡了。
風把電線刮斷了,郵電所裡一片漆黑,與外界的聯絡也斷了。楊幹事問有沒有蠟燭,郵電員摸著找到一根,點著了。
一個在櫃檯內,一個在櫃檯外,就著燭光,喝著白開,兩人聊天。先是郵電員講她們郵電所的故事,後來是楊幹事講部隊在朝鮮戰場打飛機的故事。
夜深了,風沒有停的意思。當然,即使風停了,夜裡也不能走。
楊幹事讓郵電員去屋裡睡覺,自己在外邊守著。
漸漸地風小了,楊幹事一夜未睡,困了,坐著打盹。
楊幹事一夜未歸,部隊領導都急了。風一停,立即派人出來尋找。找到郵電所時,天剛放亮。敲開郵電所的門,見到楊幹事,大家懸著的心放了下來,幸好沒出事。
看見女郵電員散亂的頭髮和楊幹事惺忪的睡眼,孤男寡女,夜來共處一室,心又提了起來。楊幹事不會犯錯誤吧?他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回到部隊,股長、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逐層找楊幹事談話。工作暫停了,派兩名幹部監控著。整整一個月,楊幹事一口咬定什麼事情都沒有。最後不了了之了。
後來,楊幹事調連隊當副指導員,就在副指導員崗位上轉業回原籍江蘇東海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夜影響了他的前程。
雪為媒
1969年初冬,部隊奉命從山東濰坊調駐山西太原。我們一幫江蘇兵在老家見過雪,到濰坊後才知道江蘇的雪充其量也就是個小雪。營房裡的積雪能有半尺厚。到了山西太原,見識了馬路上的雪被汽車壓成雪冰的時候,才知道了雪的威風。這種威風的雪對行人,腳踏車和汽車都不友好,稍有不慎,就會摔你個七葷八素。
但這摔人的雪偶爾也會做好事。
後勤機關食堂的司務長姓陳,1966年的江蘇兵。下雪了,怕上士外出買菜不安全,自己親自去柳巷菜店買菜。
他騎著永久牌的二八腳踏車小心翼翼地在路邊走著。突然從衚衕裡出來一輛腳踏車,騎車的是一位圍著大紅圍巾的女同志。
眼看就要撞上了,他下意識地揑了揑閘。這一揑不要緊,車歪著滑行的瞬間倒在馬路上,然後連人帶車在地上迅速滑行。滑行的腳踏車撞上了那位女同志的車,把人家也撞倒了在地上滑行。女同志的腳踏車撞到路右邊又彈回到路中央。
陳司務長爬起來就去扶那位女同志,一扶才發現是位面容嬌好、氣質非凡的漂亮姑娘,自己先羞紅了臉。姑娘發現撞了自己的冒失鬼原是一位年輕的軍官,想罵人的話立馬嚥了回去,趕緊說不要緊。陳司務長看看兩輛車子,姑娘的車前輪扭曲了,不能騎了。自己的車只是龍頭歪了,正一正照樣騎。拉姑娘起來的時候卻出了問題,右腳崴了,走不了了。
姑娘的家就在衚衕裡,不遠。衚衕裡的雪壓得不實,不滑。陳司務長先背起姑娘送她回家。姑娘在他寬厚的背上突然覺得此生有了依靠。
把撞壞的車扛回家後,問清楚了姑娘上班的地方,是柳巷菜店旁邊的副食店,陳司務長趕緊去買菜,同時幫姑娘請假。
下午,陳司務長請示協理員後去給姑娘修車。後來又買了點心去慰問。
週六,姑娘的母親讓他晚上去家裡吃飯。弄了好幾樣菜,姑娘的父親和哥哥陪他喝酒。
最後的主食是麵條。太原的麵條不是隨便給人吃的,那是女方待新姑爺的,在挑明之前是一種暗示。
陳司務長不懂這些,只覺得這家人很好,自己在這裡不拘束,有到家的感覺。
來來往往一年多,1971年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結婚了。
戰友們有說嫂子先看上司務長了,故意從衚衕裡出來撞上的。也有說是司務長看上嫂子了,一愣神撞上的。還有說嫂子腳沒崴,裝的。不管怎麼樣說,就是該著。
現在差不多70大幾了,應該生活得不錯吧!
老師變成岳父
1971年8月底,部隊駐紮在山西太原,衛生隊新提拔的軍醫助理小馬被保送去山西醫學院上學。
小馬是1968年的兵,衛生隊還有一位1964年入伍的馬醫生,為了區分他們,那一位被稱為一馬,小馬被稱為二馬。
二馬是班上三個軍人之一,加上高挑的身材,說不清楚的江蘇普通話,二十出頭的年紀,明亮的大眼睛和粉嫩的小臉,在班上特別顯目,是眾多女主關注的物件。
二馬當兵後與女生接一觸很少,一下子淹沒在班上眾多女生之中,很不適應。開始時兩眼不敢看女生,一說話就臉紅。他的這份靦腆反而激起了許女同學的興趣,有幾位女同學故意找楂與他說話,看他的囧像。
二馬基礎學歷不高,初中沒上完。最頭大的基礎課是生物化學,完全聽不懂。但他命中有貴人,教生理的孫老師特別關注他,有空就來幫他補習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有了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的基礎,再聽生物化學課就沒有問題了。
孫老師不但在學習上幫助二馬,在生活上對他也照顧有加。時不時從家裡帶點好吃的給二馬。冬天了,二馬常常學習到深夜,孫老師從家裡拿來一桶麥乳精,讓他晚上用開水衝了喝。
二馬也是有心人,除了用功學習報答孫老師外,盡力幫孫老師做一些力氣活。挖菜窖,拉煤這些活二馬承包了。
1972年春天,孫老師在大同下鄉插隊的女兒選調進山西醫學院上學,成了二馬的學妹。孫老師髙興,第一次叫二馬去家裡吃飯。
孫老師住在學校的職工樓裡,就一間房,做飯在走廊裡,屋裡除了書就是床。一張三屜桌靠床擺著,既是書桌又是飯桌。
女兒回來了,只能住學生宿舍,家裡沒法住。
孫老師的妻子是圖書館職工,為人慊和,家中大事小情孫老師說了算。
晚飯很豐盛,有雞蛋,有肉,有魚,還有花生。孫老師提議喝點酒。孫姑娘拿來兩個小酒杯,孫老師從床下拿出一瓶汾酒。二馬說自己不會喝酒,孫老師說哪有當兵的不會喝酒的,一定要喝。孫姑娘給倒酒,二馬不好意思,還沒喝酒臉先紅了。
才喝了1杯,不超過25毫升,二馬從臉到脖子全紅了,全身像火燒,孫姑娘趕緊泡茉莉花茶給他解酒。
孫老師看二馬真不會喝酒,就讓妻子去煮麵條。
從此,每到週日孫老師就叫他回家吃飯。時間長了,在孫姑娘面也不靦腆了。兩人開始有說有笑。再後來就相約著去圖書館,誰去得早誰佔座位。慢慢地,粘上了。
二馬好福氣,上了二年學,有了大學文憑,還拐了一個好媳婦。
戰友們有人說二馬鬼頭,知道孫老師有個女兒故意粘孫老師。
二馬說孫老師對他好是因為他好學。
誰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