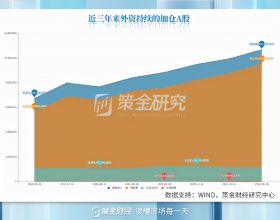一
滎陽人鄭紳和吳興人沈聿,從長安啟程,東出潼關至華山。
路上無聊,聊起佛道神怪。
鄭紳說,我還是好佛,你說,那我佛如來,本是淨飯國的儲君,棄一國之榮華而不顧,在大雪山成聖,可知成佛有莫大的好處。
沈聿說,學佛雖然時尚,但跟道家比起來,畢竟出生得晚,根基淺。這些年也沒聽說誰又成了佛的,但是傳聞成仙的倒是比比皆是,還是學仙靈驗。
鄭紳說,你那不行,是速成的,沒營養!
沈聿說,你那才不行,吃多少都沒療效!
二
兩個人一路走,一路吵,來到華山之下。
天降大雪,進退兩難,盤纏有的是,但乾糧耗盡了。
一連幾天,二人荒野求生,四處找能吃的東西,就欠互相換著啃手指頭了,結果在一處懸崖底下找著一個小窩棚。
窩棚搭得很潦草,枯枝為骨,荒草為肉,四下透風。
挪開入口的草把,裡面黑黢黢的,僵坐著一個人,一動不動。
二人嚇了一跳,趕緊逃出來,一個勁的喘氣。
一個說:“裡面那個和尚是死了吧?”
另一個說:“瞎說,分明是個道士嗎!”
“和尚啊!”
“道士哪!”
兩個餓得奄奄一息的槓精,倚在窩棚外徒逞口舌之利,誰也不敢再進去看看。
沈聿說:“實在受不了了,又冷……又餓。”
鄭紳說:“不然……咱們把窩棚拆了吧?不就有柴了嗎?”
沈聿說:“對,柴一燒,肉就熟了啊……”
鄭紳說:“啥?……吃人哪?你還有沒有人性啊?”
沈聿沒說話,窩棚裡有人說話了:
“你有人性?拆了我的窩棚,我不得凍死嗎?”
三
二人驚懼。
窩棚裡鑽出一個人來,裹著一件鶴氅,光著頭,頭上燒著香疤,瘦骨嶙峋但神采奕奕。
鄭紳說:
“高……高人,你家裡有吃的嗎?賣給我們點吧?”
那人說:
“吃的是沒有,進裡邊來躲躲雪吧,我講個故事你們聽聽,聽完了興許就不餓了呢!”
窩棚裡擠進來三個人,顯得異常的逼仄。
鄭紳和沈聿盤腿坐在落葉上,膝蓋抵著對方的膝蓋。
那人說:
“既然已經促膝了,那咱們就開始長談了啊?有誰受不了我的嘮叨,可以自動離席哈!”
鄭紳說:“離席?那不就得出去凍著嗎?”
那人說:
“然也。”
四
我的法號叫契虛,俗家姓李。
父親在玄宗時任御史。
我自幼好佛法,二十歲自願剃度,在長安出家為僧。
後值安祿山叛亂,破了潼關,玄宗倉皇西幸入蜀,我也隨著逃難的人群躲進太白山。
太白山也不太平,盜匪橫生,人們無以療飢,甚至易子而食,實在是人間地獄。
天天唸經,天天唸佛,佛祖也不來。
想來,這就是所謂業力吧,誰也改變不了,佛爺也沒辦法。
我受不了那個刺激,掙扎著躲出去,離群索居,一個人往更深的山裡走,找了一處乾淨的山崖落腳,心想,即便死,也落個清白。
從那兒起,我就開始絕粒了,就是不再吃人間的食物,沒辦法,想吃也沒有啊,只好咬松嚼柏充飢。
慢慢的就越吃越少,不是因為別的,那些東西實在太難吃了啊!
都說猴子咬松嚼柏,我在山中見過那麼多猴子,它們可不吃那個。
說來奇怪,吃得越少,越覺得身輕體健。
偶爾也念唸經,但不那麼執著於頓悟啊,弘法啊,畢竟,頓了又能怎麼著?弘又能跟誰弘去呀?
蒼茫天地,孑然一身,一切都是背景。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我是誰,但是又說不出是什麼。
純粹,這個詞兒你們明白嗎?
哦,不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吧。
五
後來,有個姓喬的道士從我那兒過,看到我那副樣子很驚訝,他說:
“矮油,這位先生,你根骨清奇啊,而且狀態也不錯,你這個樣子,是可以直登仙都的啊!”
我說:
“仙都?我可是個和尚啊!況且我只是個凡人……”
他說:
“嗨,我們……他們那兒從不歧視別的興趣班的,只要有興趣,有同等學力,都可以去旁聽一下。況且,你不一定非得註冊,可以用遊客身份登入嘛!”
我當然想去見識一下,畢竟,在死之前多些經歷,誰又不想呢?
於是我就問他:
“仙途渺茫,敢問路在何方?”
那人笑了,他說:
“登仙路,實際上還是人間路。
等先生你閒下來,去一趟商山,多準備些零食和乾糧。
商山上有不少揹著竹簍、來往販賣的挑山工,那裡面就埋伏著仙都的細作……”
我問:
“老師,我聽著有些不得勁兒啊,這像是勸我上山入土匪窩的節奏啊?”
那人說:
“我啊沒什麼文化,但是話糙理不糙,你聽我的不會害你——你就請那些挑夫吃東西,他們肯定都吃啊,對吧?”
我說:
“對啊……可是,吃完了我能要錢嗎?”
他說:
“那你不能要錢,要錢性質就變了啊……
然後,其中就會有人問你“先生你這是要去哪兒?”
你就說“我要去稚川”,這就接上頭了。
跟他走,你就能去仙都了呢!”
我說:
“你這聽起來還是像……騙老實人入夥啊?
而且,新入夥的上山前的分例酒食,不是應該山上提供嗎?難道我這算投名狀?”
“不是。”他氣哄哄的看我一眼,“算買路錢!”
六
再後來,安史之亂總算是被平了,玄宗還都,長安又恢復了往日繁華。
我也回到了舊日的寺廟,舒舒服服的呆了一年多。
但是再呆下去,心就膩了。
經歷了那些喪亂,眼前的燈紅酒綠歲月靜好,都像是貼在窗戶紙上的窗花,一捅就破。
實在不想呆了。
可是,我本就是個出家人,離了寺廟,何處可資容身呢?
腦子裡有個聲音在說:“天下。”
沒錯,天下之大,到處是我容身之所啊,天地之間一個人,其餘都是背景。
但總得去哪兒吧?就去商山吧。
我買了好多素食乾糧,僱了個挑夫挑著,進了商山。
在路邊找了個客棧住下,給過往的挑夫們送吃的。
人倒是真不少,有背一個筐的,有挑兩個筐的,還有挑二十多個筐賣筐的;給東西也真吃,有吃一個餅的,有吃兩個餅的,還有想全都搬走慢慢吃的。
但是都是吃完了就走,沒人理我,都忙著做生意謀生嘛,誰理會我這看起來有病的閒人?
這麼著過了幾天,餅和零食都快派完了,我都開始懷疑,太白山裡遇到的那個道士,是這班挑夫的老闆,騙了我來給他的員工加餐。
這一天,最開始我僱的那個挑夫小夥子又回來了,他說:
“大師,你還在這兒哪?我已經在山裡轉了一圈了,聽說這邊在免費施餅,沒想到是你啊?
我給你把這一擔吃的挑進山,你都沒說請我吃一個餅。
反倒是我的那些同行,啥也沒幹,想吃多少拿多少?
你不覺得這很欺負人嗎?”
我說:
“還真是誒!你快請吃吧!
你也是個挑夫,而且也在商山裡呢。”
“嗯,”那個年輕人嘴裡塞滿吃的,一邊嚼一邊問:“大師,你這是要去哪兒吧?”
我說:“稚川。”
七
上仙都很難,但難不過登天。
我跟著挑夫,從藍田登上玉山。
玉山不高但巖崖險惡,攀巖捫蘿,行八十里,才見到一股山泉。
隨山泉崎嶇而下,是一個不小的石洞,泉水就注入其中。
一洞的水,清可見底。
我跟著挑夫,搬石磊壩,雍塞泉水使其改道,又等了三天,讓洞底的積水滲幹。
挑夫扶著我下到洞底,洞底又有一個橫洞,往裡走潮溼晦暗,泥濘難行。
行了三天兩夜,才到得盡頭。
出得洞來,青山綠水,麗日祥雲,奇花異草,珍禽瑞獸,真乃神仙之都。
我以為這就到了,挑夫說,早著呢!
又翻過百里之外的一座高山,過了山又行百里,穿過另一個山洞,這才有了真正迥異人間的景色。
洞口下臨深潭,潭水夾在兩山之間,綠油油的深不見底,廣袤無邊,潭面如鏡,沒有一絲波瀾。
水面之上一寸,有一條石頭砌成的小徑,兩尺來寬,綿延不見盡頭。
又沿著石徑走了一百里,到一座高崖之下。
崖高千尺,光溜溜的毫無可借力落腳之處。
崖前又有一株巨樹,也高千尺,樹冠直入雲端,若隱若現。
挑夫攀到樹頂,放下竹筐把我捶上去。
樹頂上,山風獵獵,樹幹上另繫有一條粗纜,深入雲裡,只能看見一半。
挑夫搖動橫著的纜繩,遠處的雲霧裡傳來渾厚的鐘聲,不知鍾系在哪兒。
沒錯,雲霧裡又過來一隻大筐,我們就坐在筐裡,上了仙都稚川。
八
仙都不在山頂,而在雲端。
浮雲為底基,上建城郭宮闕,瓊樓玉宇,虹橋彩砌……真是沒見過啊。
確實不是賊窩,乃是仙都,我信了。
先是圍上來一群仙童,嘰嘰喳喳問東問西要東西,挑夫給了他們兩塊餅,爭搶著就散開了。
我愕然的問:
“這些孩子,餓成這樣嗎?”
挑夫笑了:
“他們幾百年沒見過人間的東西了。
這些餅拿去也不是吃的,會被分成小塊,封進琥珀裡,做成飾品。”
我又問他:
“這些仙童是在人間出生的?還是在仙都出生的呢?
如果是人間生的,怎麼會有幾歲就悟道成仙的?
如果是仙都生的,神仙又怎麼會有情愛呢?”
挑夫說:
“你想得太多了。
這些仙童既不是仙也不是人,你看腳下的白雲了嗎?
這乃是仙壤,五百年生芽,芽則為伢,長大即是仙童。”
正說話呢,一個仙人走過來問挑夫:
“誰呀這是?聞著像個凡人哪?你帶他上來幹啥?”
挑夫說:
“他說非常想來見識一下,我就帶他來了。
你這麼嚴肅幹啥?種族歧視啊?
你原來不也是人嗎?剛來幾百年就忘了本了啊?
當初我接你上山的時候,你會用這種語氣跟我說話嗎?
前恭而後倨,不是個好人你……”
九
呵斥走了閒人,挑夫帶著我去大殿裡拜山頭。
好多好多的雲彩,雲彩裡伸出一排白玉臺階,每個臺階上兩個黑炭一樣的武士,手執金瓜斧鉞,一直排到雲端。
拾級而上,又走了將近一百里,中間歇了無數次。
只要一坐下,就有黑炭武士上來呵斥、驅趕。
我偷偷的問挑夫:
“這些人什麼來歷,恁麼黑啊?”
挑夫說:
“這些也不是人,是生前作奸犯科被天雷劈死的罪人的軀殼……”
哦,難怪啊,都燒糊了啊!
爬得骨軟筋麻,終於爬到了階梯的盡頭,感覺身子已經不是自己的了。
挑夫笑了:
“這就對了,這就叫脫胎換骨……一會兒見到真君時,認真回話,說不定會破格把你留下呢。”
十
大殿裡燈火……沒有燈火,但是通明,不知光從哪兒出來,連牆壁都是亮的。
正中的仙台之上,坐著一個高大的仙人,有三五丈高,巍峨的如同山嶽。
戴著冕旒,一副王者氣象。
挑夫說:
“趕緊參拜,這位就是仙都的負責人,稚川真君!”
我趕緊給磕頭,但不知說些什麼,確實不知道啊……
就聽頂上一個威嚴渾厚的聲音在問:
“爾絕三彭之仇乎?”
啥意思,實在聽不懂,三彭是誰?我跟他不認識,能有什麼仇啊?
認錯人了吧你?
真君看我支支吾吾的,不再理會我,轉頭跟挑夫說話:
“這個……棒槌吧?三彭都未斬,弄過來幹啥?這個可真不行啊,趕緊弄走啊,在這兒可呆不了!”
被人嫌棄了啊?
十一
挑夫拉著我出了大殿,說:
“哎,既然無緣就算了……不過你也別白來一趟啊,我帶你參觀參觀吧。”
先去了一個叫翠霞亭的所在,亭子在空中漂著,用根纜繩系在樹上。
亭子裡躺著一個人,身材偉岸,面板黝黑,兩隻眼睛一直在眨啊眨的,看得人心跳加速。
挑夫說:
“這個人也是剛來的,隋朝末年來的這兒。人間的名字叫楊外郎,也算是皇室宗親,也是因為避兵禍而修的仙……”
我問:
“那眼睛就這麼一直眨啊?”
挑夫說:
“這不叫眨眼啊,這叫“徹視”,他是在洞悉下界人間的事,每一次眨眼所看到的東西,都會被記錄在卷宗,一次眨眼就是一年呢!”
我問:
“那要是直接睜開眼呢?”
挑夫說:
“臥槽,別亂說……”
躺著的那位楊外郎神仙,應該是聽見了我說的,直接就把雙眼睜開了,一瞬間,兩道光柱,貫徹天宇,照得整個稚川,人物鳥獸昆蟲,纖毫必現。
挑夫說:
“完了……這一下就是百年出去了。一百年沒有監察和德政記錄,那意味著天下將有百年的亂世了……你還真是,哎。”
十二
挑夫沒心思帶我參觀了,說:
“行了,趕緊送你回去吧,淨捅婁子。”
往下走的時候,石壁之下又躺著一個人,挑夫跟我說:
“這也是剛成仙的,叫乙支潤。
乙支潤,你別問,好吧……”
我也不敢問,為啥新成仙的都得躺著啊?
挑夫帶著我原路返回,坐大筐,溜下高樹,翻高山,鑽山洞……
快到玉山的時候,我說:
“現在應該早已離了仙界了吧,所以,請問閣下,什麼叫“三彭”啊?
怎麼叫“絕三彭之仇”啊?
當時被真君問得張口結舌的,不明所以啊!”
挑夫說:
“你啊,不是修道之人,難怪你不懂這修行的法門。
人有三魂七魄,另有三尸神附體。
人死之後,魂歸天,魄入地,三尸成鬼。
這三尸神吶,都姓彭,所以又叫三彭,這三彭住在凡人體內,主要工作就是蒐集宿主犯錯的證據,每到庚申之日,上天彙報。
所以,立志修仙之人,如果不斬了三彭,就算你修行再精進,功德積攢得再多,根器再出眾,也沒有啥用,你禁不住它們給你打小報告啊!
所以,只有斬了這三個禍根,才能真正有仙根,明白了吧?”
我說:
“明倒是白了,就不知道怎麼斬哪?”
挑工說:
“這個事兒還真是因人而異啊,就比如我,當年是個篾匠,在做竹器的時候劈出來三條竹蟲,順手就給碾死了,稀裡糊塗的就成仙了。
有個叫陶弘景的真仙,他不總在仙都,據說他斬三尸更神。說是自己在淨室焚香打坐,眼見香薰裡出來三股異色的煙塵,心中煩惡,用扇子一扇,散了,就成仙了。
還有,周處知道吧?就是那個上山殺虎入水斬蛟的猛人,最後,他死了,直接成仙了。因為虎啊蛟啊還有他自己,就是他的三尸,牛吧?當然,他是身死而成仙,又叫尸解仙,也就是說三尸中的一屍是他自己,非得這麼斬!
所以,怎麼斬三尸,只有你自己去理解嘍。但是,就我的經驗而言,什麼時候最容易識別三尸呢?就是當整個世界都成了背景,你的身邊只有兩個或三個活動之物,而你又特別厭惡它們的時候……
我是在獨自做竹器;陶弘景是在枯坐;周處另類一點,是整個世界把他和猛虎惡蛟歸為“三害”;而你呢,只能自己去找,去等……”
十三
契虛和尚看看兩位聽眾,說:
“你們看,我的故事就此講完了呢!”
外面下著雪,天地一籠統。
外面冷,裡面也冷,和尚柔和的目光看起來也很冷。
鄭紳和沈聿,感覺冷到了骨髓裡,像打擺子一樣抖起來。
“大……大師,你不是說笑吧?”
“當然是說笑,”契虛說:
“但是真是巧得很呢,兩位居士雖然結伴而來,是不是彼此厭惡呢?
兩位是不是又厭惡老僧我呢?
而我,肯定是要厭惡你二人呢,一個要燒我屋子,一個要吃我的肉呢。
所以,就算是故事,是不是一切都安排的那麼湊巧呢?”
說著,從窩棚裡抽出三把長劍,晃了晃,寒光一片:
“不過,這還真是個技術活兒呢,殺死二位施主,或是被二位施主殺死……”
契虛咧嘴一笑,嚇得二人奪門而逃,既忘記了風雪,也忘記了飢渴。
在大風雪中跋涉了一天,才在山中遇上一隊獵戶,逃得了性命。
捱了一晚,第二天領著獵戶,冒雪去尋那個“邪僧”,發現窩棚半掩在積雪裡。
拔開一個缺口,火把進去一晃,裡面只有一件鶴氅和貼身的衣物,再有三把斷劍,每一把都碎得像渣兒一樣。
“評書廉頗”,好故事多多,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