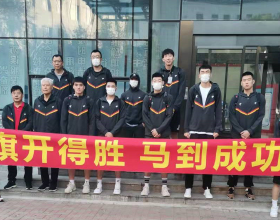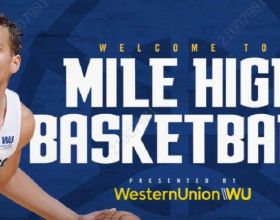每天暮晚,當華燈初上,對面公寓的那些玻璃窗,便成為一面一面的螢幕,同時上演一部電影(片名不妨就叫“人生”)。一至五樓,有白髮蒼蒼的老兩口,有獨居的老婦,有年輕的三口之家,有單身青年男女。
數月前,三樓的單身女士有了男友。隔空十幾米,很難判斷女士的年齡,她身材纖小,論穿著舉止,當在三十多歲。我注意到他們喜歡一起吃晚飯,二人安坐在圓木桌前,在那盞蘋果綠罩燈下,促膝長談,常常一直談到夜半。
愛一個人,就和他有說不完的話?我不相信話會說不完,而連月以來,卻暗暗羨慕他們。尤其在周圍的窗都熄滅之後,那間廚房仍亮著燈,被無邊夜色靜謐地簇擁,他們的愛情,就像樓頂上方疏朗的星空。
撰文 | 三書
01
七夕,你想家了嗎?
/ /
《他鄉七夕》
(唐)孟浩然
他鄉逢七夕,旅館益羈愁。
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
緒風初減熱,新月始登秋。
誰忍窺河漢,迢迢問鬥牛。
/ /
若不看日曆,我不會想到七夕,想到七夕,我也不會想到愛情。七夕,愛情,神話,都是回憶中的回憶,渺不可及。和別的傳統節日一樣,七夕首先讓我想家,想念起從前那種家的氛圍。
浩然此詩,於我心有慼慼。“他鄉七夕”,一讀題目,已不禁潸然。“身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佳節而身處異鄉,這在古人是一個事件,一個特殊的經歷,在我們已是常態,如今在哪裡都可以安頓,在哪裡都找不著家。
羈旅他鄉的遊子,此時客館獨坐,倍添淒涼。回憶的潮水漫過,捲起的浪花上,灑落婦人的笑語。穿針乞巧、喜蛛應巧、為牛慶生等七夕風俗,在民間歷史悠久,各地形式稍有不同。在我的童年時代,每逢七夕月上,女孩子們就坐在桂花樹下梳頭髮,沒有桂花樹,就坐在別的樹下,總之為了美麗的緣故。大些的女孩子,還要穿針乞巧。朱夏涉秋,鳳仙花正是時候,女孩子們這時候也會染指甲。七夕似乎是女子的節日,男子很少參與,但同樣置身其中。
浩然記起七夕的氛圍,回憶的潮水退去,眼前卻沒有穿針的婦人,更不見故國的房屋。風,已換了一個吹法,緒緒的,有些涼。“緒風初減熱,新月始登秋”,日月密移,流年似水,才至大暑,已過立秋。他鄉遊子,聽見時節流轉,聽見盜夢人的馬蹄聲,不覺心驚。
“誰忍窺河漢”,不忍窺河漢,為什麼不忍?是河漢雖同路絕嗎?抑是“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嗎?或是“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箇中滋味,我們可以自己去體會,也可以同浩然一起,“迢迢問鬥牛”,問問遙遠的牽牛星,問他天上人間為什麼這麼多的別離。
清 任頤《乞巧圖軸》
02
恐是仙家好別離
/ /
《辛未七夕》
(唐)李商隱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
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
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
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
/ /
古典詩人中,李商隱的聲音總是不同,有點另類,相當前衛。當其他詩人還在慣性思維裡為牛女而悽悽切切,義山卻喊出一句:“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也就是說,不要老是站在人的立場,要換個角度,試著站在仙家的立場去看別離,凡人喜聚不喜散,仙家也許相反,喜散不喜聚呢。在《紅樓夢》裡,超凡脫俗之人,如林黛玉、賈寶玉、甄士隱等,皆有仙緣,所以最終都撒手而去,不在紅塵世界纏縛牽連。
牛郎織女一年一見,義山說“故教迢遞作佳期”,沒有迢遞的別離,哪來相聚的佳期?從這個意義上,義山不是古人,是我們的同時代人。別離與相聚,並非簡單的物理位移,更是個心理感覺問題。你不在時,我和你說話;你在時,我和自己說話。那麼,你我究竟什麼時候是在一起的呢?
“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從來都在天河畔,何曾別離?何必非要金風玉露時,那樣的相見才叫相見?義山這兩句有點痛心,或正出於不得相見之故。
此詩的寫作時間是辛未年七夕,大概他當時也離居在外,孤身一人望空有感。清夜寂靜,漏聲漸移,牛女二星隔河相望,義山望著他們的相望,就像望著自己與戀人的相望。夜已深,天將曙,微雲卻還在遲遲,幾乎所有的佳期都叫人著急。
相傳農曆七月七日,烏鵲搭橋渡牛郎織女相會,義山此時雖未看見他們團圓,但仍暗自感激烏鵲援手相助。“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最後他想到民間風俗。據《荊楚歲時記》,是夕,婦人女子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向織女星乞巧,有嬉子(即蜘蛛)網於瓜上者,則以為符應。義山似乎另有所指,也許是對令狐綯失望又感激的複雜心情,所以才說別光想著為自己乞巧,也要想著如何酬謝烏鵲的搭橋。
明 仇英《乞巧圖卷》(區域性)
03
正人間天上愁濃
/ /
《行香子·七夕》
(宋)李清照
草際鳴蛩,驚落梧桐。
正人間天上愁濃。
雲階月地,關鎖千重。
縱浮槎來,浮槎去,不相逢。
星橋鵲駕,經年才見,
想離情別恨難窮。
牽牛織女,莫是離中。
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
/ /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立秋後,兩個明顯的物候便是蛩鳴與梧桐。蛩鳴就是蟋蟀的叫聲。《詩經·七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立秋之後,夜涼追著蛩鳴,步步逼近。北方的梧桐幹粗葉闊,不能耐寒,剛剛立秋,梧桐受氣之先,開始黃落。闊大的桐葉,墜地時啪的一聲,使人聞之心驚。
“草際鳴蛩,驚落梧桐”,說的就是這兩個物候。詩意來自事物本身,也來自作者的自覺心,有詩意的人很多,但真正的詩人很少。詩人不僅能敏感到詩意,更要將之加工成藝術。怎麼加工?這得靠語言的鍊金術,即怎樣在詞語內部、詞語之間發生裂變。蛩鳴和梧桐,本來都是感應到秋氣而自然生髮的物候,但易安在它們之間用了“驚落”,立刻就有了震動的效果。草際鳴蛩細細一聲,倏然驚落了高大的梧桐,兩個貌似不相關的物象,因此獲得新的秩序。詩人不明說她心驚,而是讓自己隱藏並顯現於萬物之中。
“正人間天上愁濃”,為何這樣說?因為人間在動盪和別離,天上的星辰也一樣難聚難期。據說李清照作此詞時,是她和趙明誠最後一次因戰亂被迫分離那年的七夕,她獨自暫住池陽,舉目無親,憂時傷離,倍感淒涼。“雲階月地,關鎖千重”,易安仰天而嘆,嘆的實則是命運的阻隔。
“雲階月地一相過,未抵經年別恨多”,杜牧的詩句固苦,易安更連“一相過”也渺茫了。她的處境是,縱使乘著浮槎,上通天河,也難與其夫團聚了。據西晉張華的《博物志》記載,天河與海可通,每年八月有浮槎往來,從不失期,有人就曾乘槎而往,航行十數天而到達天河,且看見牛郎在河邊飲牛,織女則在遙遠的天宮裡。乘槎之事是否真實,易安已不在意,她預感到這次的分離,將是比天河更無法逾越的生死。
詞的下片,她還在仰望天穹,既久,她似乎忘了自己,來到牽牛織女的夢裡。“星橋鵲駕,經年才見,想離情別恨難窮”,星橋鵲駕,浪漫傳說背後,是人對不可能的幻想和願望。即使真有鵲橋會,那滋味想必悲喜交集,悲是底色,片時相聚,怎抵經年別離。
當天晚上,天氣陰晴不定。“牽牛織女,莫是離中”,莫非他們已在離中,易安自問,為什麼“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疊用三個“霎兒”,甚是悶人,天亦如人,憂心忡忡。
李清照憑天才的直覺,多以尋常語填詞,度入音律,即便不歌詠,讀之亦清新自然,頗能曲盡人意。不僅兩宋,在整個詞史上,她的語言都是獨一無二的。
清 陳枚《月曼清遊圖冊》之“桐蔭乞巧”
04
又豈在朝朝暮暮?
/ /
《鵲橋仙》
(宋)秦觀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 /
若論最經典的七夕詩詞,公認首推的當數這首《鵲橋仙》。據有關考證,此詞背後是少遊的一段悽美戀情,即他與一位長沙歌妓的故事,歌妓慕少遊之才,少遊愛歌妓之貌,且酬其德,但數日後他不得不南行,雖盟約再來,卻很快客死廣西。《鵲橋仙》大約就作於別離後的七夕,不論有沒有這個背景故事,都不影響我們喜歡這首詞,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費力地被代入詞裡。
有一個問題經常被問起:你怎麼看異地戀?其實不必問,別人怎麼看異地戀,與你何干?異地戀的滋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什麼參考答案。然而,少遊卻在詞中大聲說出了他的意見:“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兩句真是灑脫,也許因此,我們都更喜歡這首詞。
然而,凡事都經不起一個然而,風起雲湧的人心豈能那麼容易安撫,豈是一個正確意見所能輕鬆降服?再說如果只是發表意見,又怎能算作詩呢。我們還是真實地體察體察詞中的幽微。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中度”,民諺有:“七月七,看巧雲”,即每年農曆七月七日,夕陽西下時,大家都會走出家門去看火燒雲,據說那是織女的巧手織出來的。《古詩十九首》所謂的“盈盈一水間”,在少遊這裡成了“銀漢迢迢”,字面相反,其意卻同。盈盈一水間而不得相見,是一種遙遠;因為無法相見,盈盈一水即成銀漢迢迢,更是一種遙遠。“暗度”甚好,與“弄巧”、“傳恨”,浸透相思的況味。
“金風玉露一相逢”,如風露般短暫,如金玉般珍貴,如此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少遊那段長沙戀情,不就是這樣的嗎?這樣的相逢不就是仙緣嗎?雖然不知那樣的相逢,是不是真的勝卻人間無數,但我也相信有那樣的人,你和他(她)度過一天,勝過你和其他人度過很多年。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年度鵲橋會,可不就是一個夢嗎?當他們回顧,哪裡還有鵲橋。人生如夢,七夕,愛情,詩歌,藝術,都無非是夢中之夢,較為自主的美夢。既然是夢,金風玉露與朝朝暮暮,也沒有什麼不同了。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三書;編輯:張進;校對:柳寶慶。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