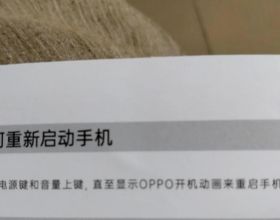又是一個星期一的早晨,陽光隔著窗簾照進周靜安家臥室的床上。周靜安躺在床上,雙眼直愣愣地盯著白花花的天花板。
過了一會,他拿起手機,看了一眼——6點50。他輕輕地嘆了口氣,然後熟練地關掉了手機上設定的7點的鬧鐘。
他想想感覺有點可笑,每天都好像是自己準時醒來叫醒鬧鐘一樣,鬧鐘從來就沒按照它原本的設定去正常地叫醒過他一次。
關了鬧鐘,周靜安習慣性地開啟網易新聞,看到頭條的位置寫著“3-4! 31歲梅西黯然告別世界盃”。他回想起12年前在大學時第一次看梅西的比賽也是在世界盃的時候,那時還是翩翩少年的梅西在最後幾分鐘替補登場,他旁邊懂球的同學告訴他,這個人才87年的就在巴薩進了很多球了,以後肯定很牛逼。說完他就深深地記住了“梅西”這個名字,倒不是因為他牛逼,而是因為他自己也是87年的,和梅西同歲。
他開啟這條新聞的評論,果不其然,裡面一樓樓地都在感嘆梅西老了,青春已逝之類的,另外還有一些大呼“姆巴佩牛逼”的。他不由地想起自己在公司的處境——領導是89的,身邊的同事基本都是90後甚至95後。每每有新同事入職,部門每個人自我介紹的時候他都儘量地不提自己的年紀。
隨便地翻了一會兒就到7點了,周靜安知道自己必須要起床了。那感覺就和死刑犯知道自己終於要上刑場了的感覺一樣。但不同的是,死刑犯只需要體會一次這種煎熬的感覺就夠了,而他卻要每天都體會一次,而且這種煎熬的感覺不會隨著每天的重複而變得習慣和淡化,反而是隨著一天天地重複而變的越來越煎熬。他能感覺到這種煎熬的累積正在變得越來越接近他所能承受的極限值。
“別忘了帶飯啊”,周靜安的老婆睡眼惺忪地跟他說到。
“嗯,好的,知道了,你再多睡會吧。”
“嗯,路上慢點。”
周靜安回頭看了一眼床上又倒頭睡過去的老婆和依舊還在熟睡的剛一歲的兒子,然後輕輕地關上了臥室的門。
他機械地刷了牙洗了臉,來到冰箱前拿出昨天晚上老婆給準備好的飯菜。今天的菜是紅燒肉和魚香肉絲。他老婆看他最近瘦了,還老沒精神,說要給他好好補補,於是最近的飯菜標準提高了很多。
老婆貼心地把兩樣菜分別裝在了兩個飯盒裡,以防串味,另外還有個飯盒裝了滿滿的一盒米飯。周靜安把把三個玻璃飯盒裝到飯盒袋裡,提了提,沉甸甸的。他想到老婆做這些飯時的場景:老婆在狹小悶熱,充滿油煙的的廚房裡一邊做飯,一邊還要隔兩三分鐘看一下客廳圍欄裡的兒子,擔心他會不會摔倒,是不是餓了或者哭了。
他想起他們最開始來上海的時候,老婆也是每天給他做飯帶飯,那時候他提著飯盒袋感覺到的是滿滿的幸福,而現在感覺到的則是沉甸甸的責任。
周靜安下了樓才發現外面竟然下雨了,淅淅瀝瀝的,天色也灰沉沉的,他無奈只能又爬上六樓回家拿傘。一番折騰終於出了樓門,但心情卻被這番折騰和這惱人的陰雨搞得更加低落了。
因為下雨,並且原有的一件雨衣前兩天又在停車子的地方被人偷了,所以今天只能走路去地鐵站了。這樣算下來時間有點晚了,有可能上班會遲到,想到這個他不由地加快了腳步。路過早餐車也沒顧上買早餐。
這個月他已經遲到兩次了,一次是帶兒子去打疫苗,一次是送他母親去火車站。如果再遲到一次那這個月的績效就泡湯了。
地鐵安檢的入口排滿了人,都是像周靜安這樣的上班族,一個個兩眼空空地,或者抬頭盯著前方,或者低頭看著手機。坐在安檢機後面負責盯著安檢螢幕的小哥正在打盹,安檢機前面的兩個小姑娘則是無精打采地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那套她們可能已經重複了好多年,以後有可能還要再重複幾十年的動作——左手無力地上抬十度,然後用催眠的語氣說“進站請安檢”或者“雙肩包檢查一下”。而上班族們空洞的眼神中則自動地過濾掉了這些,繼續一步步地往前挪,沒有一個人去安檢。安檢的小姑娘也很默契地在一個合適的距離時把上班族們一個個地讓過去,這個距離既不會產生肢體的接觸,又能表明她們盡到了要求安檢的責任。大家都心知肚明地互相配合著,希望能儘快把這操蛋的早晨趕緊地熬過去。
周靜安想起自己之前剛來上海的時候看到這些在地鐵站安檢的小姑娘時還為他們感到可憐,大好的青春年華就荒廢在這陰冷的地下,每天伴隨著滾滾而過的車輪,機械地重複上萬遍安檢的動作,然後又上萬遍地被人拒絕和無視,沒有一絲成就感。
但現在周靜安感覺相比之下自己才是應該可憐的。能進地鐵系統的大部分家裡都會有點關係,而且還基本都是上海本地人,家裡沒準有幾套房子,自己掙多少就能花多少,甚至能花更多,不像周靜安這種每個月的工資在自己卡里待不了一天就被房貸和信用卡扣走了。而且要一直這樣省吃儉用二三十年之後才有可能像這些安檢員們一樣有一套完全屬於自己的房子。
現在安檢員的工作內容也是周靜安羨慕不已的。安檢的工作雖然機械、單調,但卻簡單,不費腦子,沒有壓力和競爭,不用背不靠譜的KPI,不用擔心公司倒閉,不用害怕被裁。每天在標準的上班時間裡按照要求不斷重複那幾個動作和那幾句話就夠了,其他的什麼也不用管,不用想。每天只是出賣自己標準的8個小時,剩下的時間都是自己的。而且即便是8個小時裡面出賣的也只是自己的身體和大概1%的精神,剩餘99%的精神都是自己的,上班的時候可以隨便胡思亂想。而對於周靜安來說,自己出賣的則基本上是全部的自己——每天7點多出門,晚上10點多到家,上班的時間就跟打仗一樣,時刻保持高度的精神緊張——去和別的部門搶資源,和開發爭取工期,和同事爭論需求。晚上回到家或者地鐵上都隨時有可能收到釘釘訊息——線上出了bug或是老闆有個緊急需求。每天只有晚上躺倒床上之後睡前的那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才是完全屬於自己的。
周靜安一邊想著一邊終於挪到了閘機口。他用手機刷了下二維碼,閘機沒反應,抬起來重新掃,還是沒反應,又重複了兩次還是不行。排在後面的人開始不耐煩,周靜安也感覺到了投射在背上的一道道冷箭,於是知趣地閃到一邊。過了兩個人後他又擠進去,掃碼,還是不行。身後的隊伍裡開始有人嚷了:行不行啊,不行別擋道!周靜安從小就是個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看法的人,此時在大庭廣眾下被人嚷,感覺到萬分的不自在,恨不能立馬回家拿被子把自己埋起來。
周靜安走到附近的服務視窗,告訴裡面的乘務員說自己掃碼進不了站。裡面的乘務員小姑娘用冷冰冰的語氣說到:“掃碼問題請到2號口服務檯。”
周靜安沒說什麼,默默地繞了一大圈去到另外一邊的服務檯。裡面的乘務員拿過周靜安的手機看了兩眼,然後說:“買張臨時卡吧。”周靜安心裡憤憤地想如果自己有帶錢的話早在1號口那邊買了,但實際從嘴裡說出來的還是弱弱地:“不好意思,我沒帶現金。”
乘務員:“哦,那就沒辦法了。”
......
周靜安撐著傘站在公交站,雨越下越大,還刮起來一些風。周靜安撐著的那把之前從地鐵站口買的十塊錢一把的小透明雨傘早已抵不住這風雨,身上都溼透了。但他已經顧不上這些了,只是焦急地隔幾秒鐘看下手機上的時間,然後再抬頭看是不是有公交車過來。
現在已經八點二十了,周靜安估計到公司時至少要遲到一個小時。他能想象他們產品部的王VP用各種陰陽怪氣的腔調來調侃他的場景。王VP比周靜安還小一歲,因為進公司早,於是三十歲就成了VP,在年紀比他大,職位比他低的周靜安面前,王VP總是忍不住的想透過調侃、嘲笑、指使周靜安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因為對於部門裡的其他人他只是職位單方面的優越,而對於周靜安則是年齡和職位雙重的優越。內向敏感的周靜安對這些心知肚明,但又無可奈何。來這家公司已經三年多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成績,所做的方向又很小眾,在這個領域現在這家公司已經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出去很難找到比現在這個更好的了。
又等了十幾分鍾公交車終於來了,積攢了快半個小時的人群像聽到了發令槍響一樣一股腦地往車上擠。周靜安本來排在靠前面的位置,但因為內心深處對於這種赤裸裸的競爭有那麼一絲絲的不屑,不像其他人一樣積極地往上擠,於是不進則退,一會兒就被擠到了後面的老弱病殘組。等人上的差不多了,他終於到了車門前,才發現車上早已擠滿,連站一個腳趾頭的位置都沒有了。
周靜安想起這個月的績效,想起王VP的陰陽怪氣,心一橫悶著頭往上擠。這時車上的一位大叔沒好氣地向周靜安大罵道:“cnm,擠什麼擠!沒看到人都滿了嗎?”周靜安抬頭看了下,認出來這個人剛才是排在他後面的,開車門後就數他擠得最帶勁。對這種情況周靜安平時都是採取避讓的策略,默默地躲開他們,感覺和他們吵自己就會變得和他們沒什麼差別了。雖然他自己也知道這樣就是大眾眼中的“慫”,自己內心深處其實也是很氣憤,很憋屈的,但靠著精神勝利法還是都能忍過去,保持住自己的“風度”。
但今天的情況有點不同,這一早起來周靜安已經煩躁不堪了,感覺好像每件事都不順,老天爺今天好像換成了王VP值班一樣,故意刁難自己,看自己笑話。而且今天已經很晚了,這一班車他必須擠上去,上不去就真的完蛋了。
一股悶氣從從周靜安的胸口湧上來,化作一句對他來說算是非常硬氣的話懟給那位大叔:“我今天非擠不可!”然後使出全身的力氣拼了命地往上擠,像是要把一直以來壓的自己喘不過氣來的生活擠扁,擠倒,擠到跪地求饒一樣。
那位大叔看著好像紅了眼的周靜安倒是沒再說什麼。但隨著周靜安擠的力氣越來越大,壓力傳遞給了車裡面的人,感覺到被擠的人們開始發出各種“嘖,嘖”的不滿的聲音,臉上也都露出一副嫌棄和厭惡的表情。相較於大叔直抒胸臆的罵人,這種無聲的不滿和鄙視對周靜安的殺傷力要大很多。因為對於罵人的大叔周靜安感覺自己還是有一絲“在理”的。但對於車裡的人們,自己則完全屬於理虧的一方。他所做的正是他曾經也鄙視過的行為。這一聲聲嘖嘖的聲音像是一根根的銀針一樣扎向周靜安,之前憋足了的那一口氣瞬間洩了下來。
公交車毫不留情地開走了,只剩下在站臺呆呆地站著的周靜安。他開啟手機看了眼時間:9點20,釘釘上已經有人@他訊息了,他不想點開看,對那些訊息感覺到無比的恐懼。他盯著手上的手機,隨著收到的訊息越來越多,螢幕忽明忽暗的頻率也越來越快了。看著看著就感覺這個手機好像變成了一把皮鞭,正在傳輸的4G訊號就像伸長出去的鞭繩,每來一條訊息就會在自己後背上抽一辮子,抽打這他這頭老邁疲憊的黃牛快點拉著鐵犁往前走。
就在這一瞬間,周靜安心裡突然生出一個念頭,雖然這個念頭之前也出現過無數次,但以前都老老實實的只是作為一個念頭想想而已。而這次卻不同,這次的這個念頭有種強烈地從心底衝出來變成現實的衝動,一下下地衝擊著周靜安的理智閘門。
終於——周靜安關掉了手機。
他來到一家餛飩店坐了下了,折騰了一早上,此時才終於感覺到肚子的抗議。他點了一個大份的薺菜餛飩,什麼都不想地吃了起來。
吃完餛飩,他感覺肚子是飽了,但心裡卻空空的,一時不知該做什麼。就像坐了一輩子牢的囚犯過慣了被別人驅使、監管的生活,突然有一天被釋放,有了自由,反而不知道該怎麼去享受這份自由了。
於是周靜安便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閒逛,他仔細地觀察街上來來往往地人,儘量控制自己不去想和上班相關的任何事。
逛著逛著來到一個公園,一踏進去周靜安感覺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一樣。裡面三五成群的老人,有的在打太極拳,有的在散步,有的在唱歌,一片祥和安寧,和外面那個匆匆忙忙,吵吵鬧鬧的世界形成鮮明的對比。周靜安無比羨慕地看著這些老人們,想著自己什麼時候才能過上這樣的日子。
他在一個小河邊坐了下來,看著河裡的平靜的水面開始胡思亂想。他又想起前幾天剛回家的老媽。老媽本來是來給看孩子的,但不巧那幾個星期正趕上他基本一直都在外面出差,家裡只剩他媽,他老婆和孩子。婆婆和媳婦這兩個天然敵對的角色,再加上他老婆因為剛生產心情有些抑鬱,在家裡一直沒有笑臉。要面子的老媽受不了媳婦的臉色,帶著一肚子氣回家了,剩下老婆一個人在家帶孩子。老媽要走前的那幾天,他夾在中間感覺痛苦不堪,感覺兩邊誰也對不起,這讓他感到了自己人生徹徹底底的失敗。以前支撐著他努力學習工作的動力是儘快讓自己的爸媽和老婆孩子過上好日子,如今發現不管他怎麼努力,到頭來還是沒有什麼改變,甚至變得更糟。老媽生了一肚子氣,回老家繼續種地打零工,省吃儉用,以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願意再來上海。老婆也感覺受了委屈,並且因為周靜安岳父岳母正在給他小舅子帶孩子,所以只能讓老婆一個人在家帶孩子、做家務,給他做飯,每天也是非常辛苦。
周靜安想了半天,除了讓心裡更加難受外,沒有想到任何能解決這個問題或者改變現狀這個現狀的辦法。他感到深深的無力感,感覺自己就像個廢物一樣,什麼也不會做,什麼也做不了,每天只會想著逃避後退,如今已退到了最後的底線。他沒有勇氣開啟手機,不敢回到公司,不知道如何回答王VP“幹什麼去了”、“為什麼關手機”、“為什麼不提前請假”的質問,不敢面對同事們的眼光和竊竊私語。他越想越亂,心裡如同刀絞一樣,他想不如一頭扎到這條小河了算了。他真的站起身來,往前走了幾步,看著冷漠的河水,想象著跳進去後會怎麼樣。他看了看四周,老人們都還在各自悠然自得地進行著自己的娛樂活動。他擔心自己跳進去後會本能地掙扎,然後這些老人們會注意到,然後跑來救他,打破這個本屬於他們的這個平靜的上午。
周靜安走出公園,來到大街上,看著街上來來往往地的各種樣式、各種牌子的汽車,想著自己應該選擇哪一輛比較好。他不想給那輛車的司機或者乘客帶來太大的麻煩,同時又想著最好能夠獲得一些賠償,給家人多少地留下點東西。他盯著一輛輛飛馳而過的汽車,腦子裡反覆演練著自己衝過去之後的場景,但可惜哪種場景都不能完全滿足他的要求。
突然,周靜安聽到旁邊傳來一陣小孩子的哭叫聲,他轉身看過去,發現是在旁邊的一個幼兒園門口,一個好像發了瘋的中年男人,正在揮舞著一把菜刀,追著幾個小孩子砍。有個小孩已經倒在了地上,一攤血從他幼小的身子裡流出來。平時的周靜安是很膽小怕事的,遇到這種情況多半是等著看是否有其它人能站出來,最多是大局已定後自己上去幫個忙。但今天他感覺這好像是聽到了他的心聲的老天專門補償給他的一個機會一樣,他衝上去,不管是死是傷對他都會是一個滿意的結果。死了,正好就是自己正在想的,而且這種死法不給其它人添麻煩,有可能還能獲得一些國家的獎勵。傷了,也正好有理由解釋自己為什麼不去上班,而且有可能養傷休息一段時間後,自己的狀態沒準能好起來。
周靜安有些興奮地衝過去,不顧一切地揮舞著手裡拎的三個沉甸甸的玻璃飯盒向那個歹徒砸去。那個歹徒看到突然直愣愣衝過來的周靜安,慌了一下,被一飯盒砸到了右邊肩膀上,菜刀差點脫手。回過神兒來的歹徒立即轉過身向周靜安砍去,但無奈剛被重重地砸了一下,肩膀生疼,菜刀揮舞地很無力,而且由於一寸長一寸強,周靜安揮舞的裝著飯盒的飯盒袋因為有帶子,比歹徒的菜刀的攻擊範圍要大多了,歹徒拿著菜刀很難進的了周靜安的身。一番打鬥下來,歹徒被周靜安的飯盒砸中了好幾次,最後一次被重重地砸在了頭上,暈了過去。而周靜安這邊只是被菜刀在身上和手臂上劃出了幾個大口子,流血很多,但都是皮肉傷,並不嚴重。
打鬥結束後110和120也都陸續來了。周靜安被送到了醫院。在救護車上週靜安大概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傷口,胸前兩道,左胳膊上一道,經過包紮感覺已經都不流血了。周靜安的心情從剛才打鬥時的興奮一下又跌回低谷:就這點傷去醫院都有點浪費醫療資源,估計今天去醫院走個過場明天就又要上班了。他有點怨恨那個歹徒,怎麼那麼笨,就不知道多往自己右手臂或者腿上砍兩下。
到了醫院醫生又給他檢查了一遍,確定沒有什麼大傷,告訴他沒什麼事等會交完費就可以回去了。周靜安聽完一驚——原來還要自己交醫藥費,不知道要交多少,瞬間覺得今天自己真的是背到家了。
周靜安想幹脆多在病床上躺會,反正住院費肯定是按天收費的,現在走也不會少交一分錢。他躺在床上想著今天的遭遇,初想感覺挺可笑的,再想感覺又有點可悲,想的多了又感覺自己好可憐。除了醫生問了自己幾句傷口的情況,沒有人關心他,沒人問他今天為什麼沒去上班,為什麼會走到那個幼兒園附近,為什麼會想著上去和歹徒搏鬥......為什麼看上去那麼不高興?
他感覺有一肚子話想找個人訴說,但翻了一遍卻一個合適的人都沒有。
他越想鼻子越酸,於是起身想去交錢走人。這時卻有個護士跑過來,說:“13床周靜安,你今天先不要出院,明天區長要過來看你。”
周靜安愣了下說:“剛醫生說我沒事了,讓我回去了。”
護士不耐煩地說:“現在是院長親自跟我說的,今天區長在外面開會趕不過來,明天上午來看你。”
“我明天還要上班呢。”
“你就跟你們領導說傷勢嚴重需要再住院觀察一天,需要的話我給你出證明。”
“額,那我明天的住院費......”
“這個你就不用想了,好好地在床上躺著吧,反正一定不要出院哦。”說完護士轉身就走了。留下週靜安糾結護士說的不用想了是指不用想醫藥費的事,肯定給報銷,還是不用有什麼幻想肯定是他自己付的意思。
周靜安深吸了一口氣,有些緊張地打開了手機:99+的釘釘訊息,5個未接電話。他先在部門群裡發了張自己傷口包紮的照片,選了個合適的角度儘量把幾個傷口都拍進去,還能顯得每個都挺嚴重。然後@王VP說自己遇到了個持刀歹徒,受了點傷,要請兩天假,後天再去上班。正是快下班的時間,群裡同事們抱著八卦的心情詢問了下歹徒長什麼樣,拿的什麼刀,為什麼行兇......周靜安惜字如金又蒼白無趣地回答了幾個問題,同事們聽的沒什麼意思,也就不再問了。
處理完公司這邊周靜安又給家裡打了個電話,告訴老婆自己今天晚上上線新版本要通宵加班。他老婆也習慣了他們上線加班的傳統也就沒再細問。周靜安沒說實話是因為不想她一個人帶著孩子來看他,太折騰了。
打完電話,周靜安想著明天不用去上班,也不用回家,突然就有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一天時間,心情一下子輕鬆了一些。躺在床上,睡了最近這幾個月以來最踏實的一覺。
“快起床,區長來了!”
正在做夢的周靜安睜開惺忪的睡眼,看到是昨天那個小護士在叫自己。周靜安爬起來,剛用手胡亂整理了幾下頭髮,就見一群人走了進來,居中的是一個笑容可掬的中年人,應該就是小護士說的區長了。這位區長走上前來一把握住了周靜安的手。親切的詢問周靜安傷勢怎麼樣,有幾處傷口,縫了幾針,還疼不疼......
突如其來的熱情問候讓周靜安一時有點招架不住,感覺好像流浪在外多年吃盡苦頭的流浪狗終於找到了原來的主人一樣,心頭一熱,鼻頭一酸,眼淚都要留下來了。這時這位區長卻把頭轉向身後的人,語氣也轉換了一下:“我們現在物質文明搞上來了,但精神文明卻落後了,像小周這樣見義勇為的好青年越來越少了,我們以後要加大宣傳力度,號召全社會向小周同志學習,讓我們的社會湧現出越來越多像小周這樣的好青年。”
周靜安的情緒還沒完全轉換過來,咔咔幾聲,區長和周靜安握手講話的照片就被隨行的記者拍到了相機裡。
第二天早上,周靜安依然和往常一樣絕望地去擠地鐵上班。他沒注意到每天路過的那個報刊亭裡的市日報上登出了他見義勇為的新聞。在第三版,佔的地方不大,當然配圖就是他和區長握手的那張。而歹徒襲擊幼兒園的事因為並沒有造成什麼大的死傷,而這則見義勇為的新聞也算是順帶報道了這件事,而且還是從正面的角度,所以也就沒有再專門的報道。
在周靜安擠上地鐵的同時,這個城市的市長剛喝了第一口秘書給煮好的咖啡。他拿起辦公桌上的報紙,翻閱起來,看看自己管理下的城市昨天又發生了什麼事。當他翻到第三版的時候一眼就看到了周靜安的新聞。因為他看到了那個熟悉的幼兒園名字,那正是他兒子上的幼兒園。他想起來昨天他老婆跟他嘮叨了一晚上說有人去他兒子幼兒園行兇,拿著刀追著砍小孩子,要不是有個人見義勇為打倒了壞人,他們兒子不知道會怎麼樣,想想就後怕。
市長想了下,給精神文明辦的劉主任打了個電話,說到:“劉主任,你好哇,有看今天的報紙嗎,有個新聞,是一個小夥子見義勇為制服了襲擊幼兒園的歹徒。我認為這種事值得好好宣傳下啊,你看呢。”
“對!這種正能量的事肯定得好好宣傳宣傳宣傳,我這就安排下去,搞一個系列的學習宣講會,然後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這些渠道都利用起來,爭取掀起一波全民學習見義勇為精神的熱潮。”劉主任鄭重地說道。
掛了電話劉主任立馬找來今天的報紙,翻了半天才找到周靜安的那則新聞,盯著這個豆腐塊大小的新聞看了十幾分鍾,也沒想通日理萬機的市長大人怎麼今天一大早地就為這麼一個看上去沒多大的事專門給自己打電話。但既然是市長安排的任務,那肯定不能怠慢了。於是立即召集人開會,想方案,定計劃,分任務。
會開完,負責新媒體渠道宣傳的科員小李犯了難。從來不刷微博的主任會上一拍腦袋就給自己定下了微博100萬閱讀,10萬轉發,1萬評論的三個一目標。小李心想主任以為自己是張藝興,鹿晗這些小鮮肉啊,隨便發個自拍就能有幾十萬的評論。就這麼個普普通通的小新聞,沒死人,歹徒不夠奇葩,見義勇為的也不帥,看著也不像有什麼特殊經歷或做什麼特殊職業的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這件事有什麼能有希望完成任務目標的傳播爆點。
無奈之下的小李想起自己在公安局的同學,於是聯絡他要了那天幼兒園門口的監控錄影。他仔細地看了遍錄影,看著裡面的周靜安笨拙又毫無章法地胡亂揮舞著飯盒袋,驚愕的歹徒雖然拿著把刀但對這邪門的武器卻無可奈何。只見分量十足的飯盒袋子在歹徒的頭上,身上重重地砸了沒幾下,歹徒就暈倒在地了。
看著錄影小李突然來了靈感,他把錄影裡面幾段比較精彩的打鬥做成了gif動圖,然後又因為最近剛看了復聯三,於是想了句文案:所謂超級英雄不是盾牌、鎧甲和超能力,而是在需要的時候勇敢地站出來,用笨拙的動作和簡陋的武器來守護一方安寧。向我們的飯盒俠致敬!
小李編輯好微博發了出去,看著自己的作品有點小得意,想著三個一的目標可能做不到,但三分之一的目標應該差不多,夠交差的了。
此刻的周靜安正在痛苦地開著需求評審會。因為耽誤了兩天時間,需求準備的很不充分,在會上被開發和以王VP為首的各個領導和小嘍嘍們各種挑戰,本就嘴拙的周靜安疲於應對,頭腦從混亂逐漸變得空白,後面對於大家提的問題完全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只能不斷地重複“好的,這個問題我回去改下”。
晚上十點周靜安才走出公司大樓,走出樓門口的一刻,周靜安感覺身體立馬洩了氣一樣,想要癱坐到地上。
第二天周靜安還是像往常一樣掙扎著按時來到了公司,他坐到座位上後感覺周圍有點奇怪。自己周圍的幾個同事都在低聲地議論著什麼,還不時地向他這邊看上兩眼。
過了一會,王VP來了,王VP沒進他的辦公室而是徑直走向周靜安,一把拍到他的肩膀上,笑呵呵地說:“可以啊,兄弟,沒想到還是個大英雄啊,真沒看出來。”
周靜安一臉懵逼地看著昨天評審會上剛把自己噴地狗血淋頭的王VP:“王總,怎麼了,什麼英雄啊。”
“啊,怎麼你自己還不知道啊,快看看微博熱搜吧!”
周靜安開啟微博,進到熱搜,看到第三位寫著“飯盒俠勇鬥歹徒”,他點開看了下,真的說的就是自己,而且熱門的那幾條微博轉發和評論數都還很多。
微博剛看沒幾條,前臺的小姐姐過來說老闆找他。周靜安有一點忐忑地走進老闆辦公室,只見裡面除了老闆還坐著幾個有著濃濃的公務員氣質的人。老闆跟他介紹說這是市精神文明辦的,要跟他談下推廣宣傳他的見義勇為精神的方案,要給他做專訪、上電視、發專題報道還有十幾場的宣講會。周靜安一聽這麼大陣仗,連連推辭。無奈幾個文明辦的同志能說會道,建設精神文明、弘揚社會正氣幾個大高帽子扣下來,讓周靜安感覺自己要是拒絕就成了人民的罪人一樣。
無奈之下週靜安只能央求:“其他的都可以,宣講會能不能算了,我從小到大都沒上臺演講過,一上去就緊張,講不出話來。到時候搞砸了更不好。”
沒想到文明辦的同志早想到了這個問題,回答道:“這個你放心,我們會派專業的老師給你封閉培訓一週,就算是啞巴也能給他培訓成演講家。”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周靜安完全不記得怎麼過得了。最開始的一週是做採訪、上電視臺做節目、寫宣講稿、改宣講稿、背宣講稿、練習怎麼演講、用什麼語氣、什麼表情、什麼動作......
周靜安感覺自己就像個牽線木偶一樣,被別人任意地擺佈。而他好像也很習慣甚至有一點喜歡這種做木偶的感覺,因為不用上班,不用動腦子,不用和別人溝通協作,不用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每天只需要按照別人安排好的行程計劃,按照練習過很多遍的劇本去“表演”就可以。他甚至在這件事上做的有點“出色”,培訓的老師誇他語言和動作都做的很標準,後面的幾場宣講會,如果不看底下的觀眾,只看周靜安的演講簡直就跟看新聞聯播的重播一樣。當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周靜安在演講的時候臉上完全沒有表情,他的語氣和動作會忽而激昂,忽而低沉,但表情卻沒有一絲變化,一直冷冰冰的。不過培訓老師和文明辦的同志們並不太在意這一點,因為演講基本都是在大禮堂,臺下的觀眾也看不太清,大部分也不關心周靜安臉上是什麼表情。
隨著宣講一場場地進行,周靜安也變得越來越火了。除了線下宣講的推動外,還有電視臺、報紙、雜誌的頻繁報道。而這其中影響最大的卻還是小李那篇簡短的微博。飯盒俠的名字在網上被廣泛的傳播和討論,很多有才的網友還將周靜安勇鬥歹徒的動圖成了各種各樣的表情包和惡搞圖,有的還做成了鬼畜影片。一時間火的周靜安都坐不了地鐵了,一進地鐵站就會有各種人上來圍觀、拍照,大叫“飯盒俠!”。周靜安在這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火,更沒有想到過會以這種方式火。他心裡對此有一些不解,但沒有一絲波動。因為他知道火都是暫時的,火著的越快,滅的也就越快。一個月、兩個月過後大家都熱情退散,自己還是要每天都擠地鐵,上班,加班,原來的生活繼續,不會有任何變化。
一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宣講的最後一站被特地地選在了周靜安見義勇為的那個幼兒園。上午九點,周靜安來到幼兒園的時候園長已經組織全幼兒園的小朋友們在院子裡坐好了。在園長一番致辭後,周靜安走到演講臺上,看著臺下一個個坐在自己小板凳上,用純淨又充滿期待的眼神看著自己的小朋友,突然感覺有些不知所措。之前演講面對的都是成年人,他可以毫無壓力地按劇本“表演”,而今天他感覺一下子失去了之前的“演技”。
周靜安完全憑著肌肉記憶尷尬地完成了這次演講。宣講會結束後,孩子們散場,他也往外走,這時一個長得很可愛的小女孩向他走過來用關切的語氣對他說:“叔叔,你怎麼看起來這麼不開心啊。”
周靜安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問懵了,一時不知怎麼回答。
小女孩看周靜安不說話,便從兜裡掏出一個棒棒糖,送到周靜安面前:“這個棒棒糖送給你,可甜了,我每次不開心的時候媽媽都會給我一個,吃完就什麼煩惱的事都忘了,你嚐嚐。”
周靜安蹲下身來,接過棒棒糖,看著小女孩關心的眼神,眼淚禁不住地流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