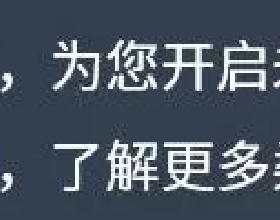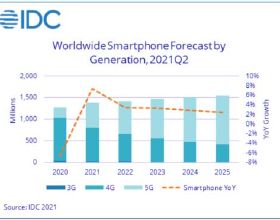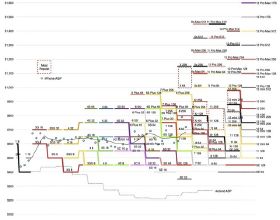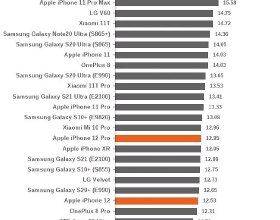多多是一條狗。確切地說是楊威父親養的一條狗。多多以前沒有名字,這個名字是楊威給起的。
楊威的父親去世了。那天深夜,楊威接到了妹妹從鄉下家裡打來的電話,妹妹哽咽著說,“哥,爸……他沒了……”楊威手裡舉著電話愣怔了好久,最後他淡淡地說,“知道了!”掛了電話,楊威站起身來,走出臥室。他開啟客廳的燈,在冷清的光亮裡站著。那一刻,他才想起自己有兩年多沒見父親的面了。自從兩年前,楊威跟妻子離婚後,楊威一直沒回老家看過父親。楊威重新點了一根菸,走到陽臺,推開窗子,讓深秋的風吹進來。一輪明月掛在天邊,對面樓層裡的燈都熄了。這一夜,楊威站在陽臺一根接一根的抽菸,直到東方泛白。
楊威一夜沒睡。菸頭在腳下散落一片。天剛熹微,楊威就開著車回老家了。老家離他居住的城市有一百多里,一個多小時後楊威的車就進村了。小山村不大,衚衕窄小,楊威的大個頭越野車開不到家門口,只好停在村委大院裡。清晨的山村出奇的清靜,走在幽深的衚衕裡,楊威感到了一種壓抑感,腳步越接近家越發變得沉重起來。楊威老遠就看到父親家門口聚著一堆人,然後他就看到了低矮破舊的木門上貼著白色的對聯。那一刻,他倏然感到心裡一沉,瞬間湮滅了來時路上的默然。雖然二十年來,楊威一直承受著來自父親所帶給他的痛楚,以致於取代了父親在他心中的位置,但此時親眼看到這個場面,心靈還是被觸動了。妹妹最先看到了楊威。她全身孝服,眼睛紅腫,看來早已哭過多次了。妹妹說,“你回來了!”然後拉著楊威繞過人群進了父親住了十幾年的小院子。楊威再次出來時已是全身戴孝了。
山村並不大,三百來口人,除了幾個主事的,也就有十幾個幫忙的。楊威沒有叔伯,只有一個姑。所以,孝子也不多,場面顯得很冷清。楊威進屋找到了姑姑。姑姑用乾枯的老手拉著他的手,眼裡含著淚花,表情說不上是傷心還是愧疚?姑姑說,“孩子,你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姑姑說著不停地用寬大的白袖子擦拭眼睛。楊威看著姑姑花白枯槁的頭髮,眼眶也有點熱。楊威鬆開姑姑的手,說:“姑,我想看看他……”姑姑用嘆息一聲音說,“孩子,去看最後一眼吧,你爸爸在裡屋哩!”楊威此時才注意到父親住的屋是那樣的低矮,灰暗。外屋是兩小間,一張黑乎乎的八仙桌歪歪扭扭地靠在早已泛黃的報紙糊就的土牆上。其餘就看不到什麼傢什了,牆角處堆著一些凌亂的破爛,抬頭就看到灰黑的房梁和葦箔。外間和裡間由一道布簾子隔開。布簾子也是一樣的灰暗色調。楊威看到屋裡的情形,鼻頭突然一陣發酸。姑姑又說,“進去看一眼吧,一會就入棺了。”楊威這才鼓起勇氣,右手挑起簾子,彎腰進去。楊威一眼就看到了炕上的父親。
父親直挺挺地躺著,身上穿著嶄新的壽衣,臉上蓋了一張方形的黃紙。楊威專注地盯著這張黃紙,他彷彿看到黃紙在鼻息的作用下微微扇動著。楊威盯著這張黃紙有十分鐘,然後他慢慢地俯下身去,慢慢地伸出手拿開它。父親的臉出現在楊威的視線裡——那是一張陌生的又黃又瘦的臉——褶皺縱橫,如山坡上新犁的土地;父親嘴邊的皺紋呈放射性延伸進乾癟緊閉著的嘴巴里。楊威只覺胸口一熱,眼淚幾欲奪眶,他拿著黃紙的手在抖動著,那一刻,他才發覺父親已是一個老人了。這時,一個聲音飄進楊威的耳朵裡,“孩子,人已經沒了,你就原諒他吧?畢竟是你的親生父親啊!”楊威回過頭,不知何時姑姑已在身後站著。姑姑的身邊站著自己唯一的弟弟和妹妹。楊威看著自己身邊這幾個最親的人,只感到喉頭一陣翻動,眼淚嘩地奔瀉而出。此時楊威再也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撲在父親的屍體上,嚎啕大哭起來。他的聲音撕裂,氣勢恢弘,震得這三間老舊的泥巴屋也在瑟瑟顫動,似乎要把壓抑了二十年的痛苦化作眼淚一併發洩出來。楊威一哭,弟弟和妹妹也撲在炕邊大哭不止。楊威的姑姑早已哭啞了喉嚨,眼淚又一次無聲的墜落。
楊威和弟弟把父親抬進棺材裡。楊威用手反覆地撫摸著棺材的蓋板,過了好一會兒,他對身邊的弟弟說,“一會,我來抬棺,你為爸爸指路……”二十年來,他第一次對父親產生了一絲留戀。在一片哭聲中,楊威和眾人起棺上路,向半山腰的祖塋走出。
葬完父親,幫忙的鄰居鄉親吃了飯,收拾停當,漸漸散去。楊威的妹妹領著兩個孩子也回去了。楊威對弟弟說,“你也回家吧。我想一個人呆一會兒……”弟弟說,“哥,你看爸爸也沒了,過去那件事就忘了吧……爸爸自從搬進這個小院子裡,只有妹妹隔三差五來看看他……我曾幾次想接咱爸回家住,也好方便照顧,可咱爸怎麼也不同意啊!其實這麼多年裡他也過得不容易啊……哎!我看……咱們也都原諒爸爸吧?你說呢,哥?”
楊威坐在天井裡的半截石磨上,眼睛茫然地盯著三間低矮的泥巴屋,自言自語地說,“整整二十年了……”說著楊威站起來,走到弟弟面前,緩緩地抬起胳膊,兩隻手緊緊的握住他的肩頭,帶著哭腔說,“咱們整整做了二十年沒有孃的孩子了,你知道嗎……?”
弟弟擦了一把眼淚說,“哥,可是咱們就因為爸爸的一次過失,記恨了他二十年,難道對他的懲罰還不夠嗎?因為記恨,我們也失去了爸爸啊……”
“過失……?這不是過失,是謀殺。你知道嗎,二十年前的那天晚上,是我親眼看到他用馬紮打在孃的頭上……他像瘋了一樣,不停地揮舞著手裡的馬紮,直到娘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我用力推那門,怎麼也推不動,是他在裡面把門頂上了。難道這不是有意識的謀殺?因了他是我們的父親,又是村長可憐我們的三個還小,才沒有去報案。那時我已經十六歲了,我什麼也懂了。當我看到他親手殺了孃的那一刻,父親在我心裡就已經死了……”
‘可是……“弟弟說,“這麼多年來,你也看到了,父親拼命把我們拉扯大,攻我們倆讀完了大學。他也盡責了。”
“他這是在贖罪。”楊威突然鬆開弟弟的肩頭,在小院子裡快速的走著,情緒有點失控。“他以為對我們盡到責任就行了,那二十年來,我們失落的感情他能補償嗎?他以為不花我們給他的錢,搬進這麼一個簡陋的小院子來,心靈就能得到安寧嗎?不會的……失去的東西永遠不會找回來。他做下的惡就由他自己來償還,沒人能幫得了……”
“哥……爸爸剛剛走,咱不再譴責他了,好嗎?再說,那次事件也是有原因的。再加上爸爸的暴躁脾氣,要不也不會發生那件事!”弟弟說。
“沒錯,他不但脾氣暴躁,而且猜忌心更重。他一直懷疑咱娘跟村頭老王有扯不明白的關係。可那根本就是他憑空想象。娘死後,我曾找老王談過,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事。娘那一段時間經常出入老王家,那是因為娘想跟他學學養平菇。咱娘想空裡在家養點平菇給我們改善一下生活,吃不了還可以趕集去賣點錢。可他呢,聽信村裡人閒言碎語……”楊威說到這裡,一擺手,“弟弟,你回家吧,弟妹還在家等著呢!”
“哥,那以後,咱啥也不提了,就當作一個誤會吧。現在咱爸也過去了,見到咱娘他會向她好好解釋的。還有,你看,你的性格脾氣也隨咱爸,雖然離婚了,以後也常常去看看佳佳【楊威的女兒】,這對孩子的成長有好處……”
楊威回過頭看著弟弟的眼睛說,“你和咱妹妹的性格像娘。哥聽你的——以後一定改改這個臭毛病!……好了,這件事現在就過去了。走,我們一塊回去。我也順便看看兩個侄兒。”
日暮開始了籠罩了這個小山村,月亮從山巔升起來,夜漸漸降臨。楊威兄弟倆一前一後走在安靜地衚衕裡,不知從誰家傳處幾聲狗吠。
那天楊威從城裡回去給父親上頭七墳。下山時,他讓弟弟妹妹們先各自回去,自己說要去父親的老宅看看。楊威拿著鑰匙打開了低矮木門上的鏽跡斑斑的鎖頭,鎖鏈子嘩啦一聲垂了下來,楊威的心頭猛地一顫。他這才記起自從父親搬進這個小院十五年來,自己跨進這個門檻的次數真是屈指可數。而且每次去,連父親的屋也不進去,只把手裡的大包小包往門裡一放就轉身走了。而父親總是默默地接受著他買來物品,不拒絕,也不高興。父親知道兒子並不想見自己,每當他看到楊威拿著東西進門,總是馬上躲開去,或者連忙轉過身,背對著兒子,避免直面對方帶來無以言對的尷尬局面。只有楊威的妹妹,父親不會去刻意躲避他。楊威的妹妹嫁到了七八里路外的村子,每隔兩三個月就領著孩子提著東西來看父親。當然,就算是女兒,對父親也沒有過多的話說,沒有話說也不能立刻就走,老遠來一趟不容易。女兒就拿起牆角的掃把來掃天井。掃完了天井她就去屋裡找出父親替換下來的髒衣服來洗。父親由於年輕時抽菸嗜酒,脾氣又大,在五十幾歲這個年齡上,看上去就有些老態了。女兒在收拾,他就披一藍布褂子、冬天則披一件羊皮棉襖,蹲在石磨後抽菸袋。父親默默地抽菸,不時地抬起頭來看女兒一眼。父親抽完了一鍋煙,在一旁自個兒玩耍的才幾歲的小孫女就跑過來搶過爺爺手裡的煙鍋子笨拙的幫他裝上一鍋煙,再次送到爺爺的手裡,自己又去一邊玩了。小孩子可能見母親和爺爺都不說話,自己也就不說話了。一切像在上演著一場啞劇。等父親抽了幾鍋煙,女兒就收拾的差不多了。女兒一般不在父親家吃飯,她幫父親做好了午飯,就領著孩子去弟弟家吃。女兒臨走前不忘說一句,“爸爸,我們去弟弟家吃飯了啊……”父親一貫不說話,只把手裡的菸袋機械的在地上磕幾下。女人領著孩子走出家門走到衚衕深處了,父親才走到大門口,目送著女兒漸漸離去的背景一直消失在衚衕的轉角處。
楊威邁進了門檻,才幾步,已站在了天井的中央了。牆根下有一顆碩大的棗樹,有一半樹冠探到了低矮的土牆外,另一半遮住了半個院子。本來就小的天井就更小了,朝天看,只看到簸箕大的一塊不規則的天空。在棗樹的覆蓋下有一間土坯飯屋。飯屋很小,裡面堆滿了半間秫秸和茅草。一個土坯的灶臺孤零零的貼牆蹲著,長期被煙火薰得烏黑吧唧。楊威站在低矮的飯屋門口,彷彿看到父親坐在土灶前像女人一樣一把把地向灶膛裡送著柴火。火舌在灶膛裡翻卷吞吐著,映紅了他那消瘦的黑紅臉膛。一年一年,父親就默默地坐在土灶前苦熬著日子……楊威想到這裡,心裡有一種難言的痛楚,為父親?還是為過早離世的母親?楊威也說不上來。在最近十年裡,到底‘原諒父親還是不願原諒’這個念頭一直折磨著他——多少個午夜,楊威在夢中懺悔、又多少次夢醒,他在理智與親情之間徘徊,權衡,撕裂……尤其近幾年,父親漸漸老了,楊威多想在父親的晚年盡一份作為兒子的孝道呵!可是,當二十年前父親用馬紮兇狠的砸死母親的一幕又跳進自己腦海裡時,理智又使自己陷入冰涼的低谷。楊威結婚後,定居城裡,遠離了父親,而身心並未因此而平靜下來。他依舊經常做噩夢,夢中父親殺死母親的一幕更加鮮活的在楊威眼前重演。每次楊威帶著一身冷汗從噩夢中醒來,妻子在他胸口撫摸著,像對孩子一樣的安慰著他。但這並不能阻止楊威不去做噩夢。就是這樣,在噩夢中的重複中,一次次加深了他對父親刻骨銘心的怨恨,使他在二十年裡一直不能原諒父親的那次‘過失’。
剛結婚幾年,楊威的妻子還對他體貼入微的關心,自從女兒出生後,她就把大多精力和愛心傾注到可愛的女兒身上,對於丈夫的心結她也無能為力了。甚至,當她看到楊威下班後總是那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時,心裡竟產生了一些厭煩的情緒。當然,楊威一貫沉浸在心靈的折磨和自我救贖中,並不注意到妻子的情感變化。當女兒漸漸長大,上了幼兒園後,妻子應聘去了一個私立小學當語文老師。妻子還年輕,性格開朗活潑,大學時期她也是一個文藝青年,骨子裡還有一絲浪漫的情懷。雖然與楊威結婚五年來,她儘量把自己定位在一個好妻子、好母親的角色,但那種文藝化的浪漫情調時常在一場秋雨或者走在暮春的街頭,像一杯剛煮的熱咖啡,慢慢散發出它的香醇和厚重。那時,她會突然覺得自己回到大學時代,有一種要逃離飛昇的感覺。而在這種美好的感覺裡會不時地浮現出楊威那張憂容苦臉,那時她已經確信自己與楊威之間已經出現問題了。終於有一天晚上,楊威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中,一把摟住她的腰就要向床上按時,她欠身一躲,放下手裡正讀的書——《嘉莉妹妹》,說“今天來了好事,不能做的……”那次,她是第一次對自己的丈夫撒了慌。以後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以致後來,楊威喝了酒去歌廳找小姐被抓。她才真正跟老公進行了一次嚴肅的對話。然後,他們分居了。在給女兒過完了第五個生日後,他們就和平的離婚了。離婚後,她帶著女兒去了另一個城市生活,並帶走了家裡所有的積蓄。楊威就這樣成了一個孤家寡人。妻子帶著孩子走了,楊威依然還要生活在那個令人壓抑的城市裡,他無處可逃,因為壓抑來自他的內心深處。
離婚後,楊威每月兩次開車去另一個城市探視女兒。一年多後,他再去時,前妻已經結婚了。她嫁的是一個畫家。畫家沒有房子,在城郊租賃了一個破舊的院子、號稱‘雅逸居’的畫室裡,凌亂不堪,滿桌的五顏六色的墨跡和滿地的畫了一半的畫紙。楊威站在‘雅逸居’門口,看著女兒坐在地上撕著畫紙玩,小臉上也塗得黑兒吧唧。畫室的主人,一頭亂髮,如秋後的茅草,雞爪子似的手裡正抓著一隻筆站在桌子前作畫。他東一筆,西一筆的抹,把所有盤子的顏料都在紙上抹了一遍,紙上實在沒有空白了,他就停下來,掐著腰在端詳自己的“作品”。楊威看得一臉霧水,也沒有看懂這張畫的內容。楊威離開畫家,在另外兩間平房裡找到了前妻。前妻坐在馬紮上,神情黯然,手裡拿著一本書,書打開了,字卻是倒著的。從她的口裡,他知道了那是個所謂的印象派畫家。楊威臨走前,意味深長的看著妻子說,“你跟那傢伙必須談好,自己掙錢自己花。”說完,楊威就走了。
以後,楊威很長時間沒有去探視女兒。
楊威在父親的小院裡徘徊了很長時間不捨得離去,在那裡他感到了一種孤獨——這是他非常熟悉而親切的一種孤獨。多少年來,一直與他須臾不能分開就是這種孤獨的情感。他知道父親的後半生是孤獨的,所以他也體會到了這種孤獨。難道這就是父與子之間的心靈感應?
楊威開啟房門,走進屋裡。還是那道灰舊的布簾,靜靜地掛在那。楊威輕輕地挑開布簾,他又看到了父親曾經睡過的那盤炕。土炕空蕩蕩的擺在那,炕上卻沒有了自己的父親。楊威感到一陣失落,鼻頭一酸,眼淚差點流下來。此時,他才確信,這麼多年來,自己對父親一直是有感情的。楊威突然感到後悔了,如果父親再活幾年,他一定試著去接受父親,緩和他們之間的矛盾,甚至和好如初……楊威看著這盤炕,彷彿看到父親一個人捲曲在上面,默默地無可奈何地在日復一日的悔恨中熬過了幾千個長夜,那是怎樣的一種精神的煎熬啊!楊威想到這裡感到不寒而慄,難道自己不也是這樣熬過來的嗎?其中滋味自己早已品嚐透徹。楊威覺得自己與父親就是兩隻拴在一條繩上的螞蚱,不同是:父親是在悔恨中生活著,而楊威是在怨恨與糾結中煎熬著日子。而父親終於解脫了,作為兒子的楊威卻開始在另一種悔恨中開始以後的生活。楊威真的後悔了,作為兒子,他沒能很好去安慰做錯事的父親,卻還聯合他的子女們去捨棄他,在他本是懺悔的心靈上又加上了沉重的砝碼,使父親在萬劫不復的悔恨中離開了人世!這是人世間何等殘忍的行為啊!楊威開始真正面對自己了,並從中看到了自己靈魂中的汙穢之處。但一切為時已晚,父親不在了,他懺悔的靈魂已經無處安放。
楊威在父親遺留下來的小院裡逗留了兩個時辰。他往外走時,突然聽到飯屋的草堆裡刷拉刷拉的作響。好奇心使他停下來,拿起一根木棍去秸稈裡戳了戳,竟從裡面鑽出一隻老黃狗來。老黃狗也不怕他,慢悠悠走出來在天井中心站定,抖動了幾下身上的稻草,這才回過頭來,拿狗眼瞭了一下楊威,就拖著尾巴慢騰騰地走到牆角的石槽邊喝水去了。楊威這才記起來,這隻黃狗不就是父親養的那隻大黃嗎?沒想到大黃也這麼老了!記得幾年前楊威見到大黃時,它身上的毛很光滑,在陽光下泛著金黃色的光。現在大黃的毛已是黃裡泛灰,耳朵也不再豎立著,而是耷拉下來,無精打采的吊在那。大黃喝了水,就在石槽前趴下了,腦袋擱在前腿上,兩隻渾濁的眼睛盯著楊威看。楊威也注視著它。人和狗對視著好一會兒,楊威忽然看到了大黃眼裡流出了兩滴渾濁的眼水。那一刻楊威的眼睛也溼潤了。
楊威回城時,也把大黃帶回了城裡的家。他給大黃起了個名字——多多。自此,楊威與多多住了一起。楊威的房子是兩室一廳,他單獨把一間臥室收拾出來給多多來住。剛開始他不知道多多喜歡吃什麼,就變著法的買回食物來給它吃。蒸包、油條、火燒、火腿、肉……他甚至還炒了一盤大蔥炒雞蛋放在多多的鼻子下面,可多多連聞也不聞,腦袋一歪,就閉上了眼睛。楊威實在沒法了,就一早去市場買回了新鮮的豬腿骨。狗本來是喜歡肯骨頭的,可是多多對新鮮的骨頭也不感興趣。楊威掰開它的嘴看了看,牙也好好的。沒辦法,楊威只好扯起它的兩條前腿把多多背到了小區附近的一家寵物醫院。寵物醫院的女大夫戴著口罩皺著眉頭瞅了兩眼多多說,“我們這裡只給寵物看病。”楊威說,“多多就是我父親的寵物……不要緊,您只管看,錢沒問題。”然後,楊威對大夫說了多多的症狀。大夫極不情願的撬開多多的狗嘴看了看,又端詳了一會兒說,“這條狗太老了!”楊威說,“是啊,它已經跟了我父親十幾年了。”大夫用怪異的眼光看著楊威,把聽診器放在狗肚子上聽了聽,站起來說,“它沒什麼病。只是太老了,厭食。”楊威問,“能治嗎?”“我這裡治不了。”大夫說。楊威點點頭,支付了診療費,領著多多走出了寵物醫院。
楊威走在前面,多多跟在後面。人和狗都低著腦袋,失魂落魄的走在街上。楊威一直在為多多的飲食犯愁,而多多眼睛裡的迷茫是為什麼呢?在回家的路上,楊威停下來兩次,他看著多多的眼睛,企圖從這雙漸漸老去的狗眼裡看出點什麼來。可是多多懶得跟他對視,見他不走,乾脆後腿一彎坐在地上了,坐了一會又趴下了。楊威知道多多是老了,走路都顯得吃力了,而且幾天來也沒吃什麼東西,只喝了一點楊威熬的小米粥。奇怪的是,楊威看著多多不吃飯,自己也沒有什麼食慾了。所以,楊威這幾天也很累。上樓時,楊威又背起多多回到家中。晚飯楊威照常熬了小米粥。楊威喝一碗,多多喝一碗。楊威喜歡喝小米粥就著胡蘿蔔鹹菜,他也把胡蘿蔔鹹菜切成末撒到多多的碗裡。晚飯後,楊威喜歡看韓國電視劇。之所以喜歡上看韓劇,開始時他只想從韓劇上學學做菜,最後他就離不開韓劇了,每晚不看上兩集就睡眠不好。妻子還在身邊時,楊威最煩的就是她的嘮嘮叨叨;離婚後,他卻喜歡上了嘮嘮叨叨的韓劇。楊威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自從身邊有了多多,楊威看韓劇的興趣少了點,他開始跟多多說話。楊威坐在沙發上抽著煙,多多就坐在客廳的一個涼蓆子上。電視裡依然是放著韓劇。楊威有一搭沒一搭地問,“多多,天天喝稀飯可不行啊!”多多不理他,茫然的盯著電視。楊威說,“多多,你覺得城裡好,還是鄉下好?”多多的喉嚨裡呼嚕一聲響,同時把狗頭歪了歪。楊威看了看多多,“你說你不喜歡城裡?我知道,你喜歡鄉下那個小院,畢竟你在那兒生活了十幾年了。可是,你的主人……哦,也就是我的父親,他走了,沒人管你了……你知道嗎?既來之則安之嘛!”楊威顯得有些苦口婆心。多多的鼻孔裡噗嗤打了一個無力的噴嚏,前腿一軟,趴在地上了。楊威說,“好了,我知道我說什麼你也聽不進去……我答應你,以後我經常帶著你回鄉下去看看。哎,其實,我也挺想回去看看……”楊威說著說著,聲音就有點哽咽。他開始想念自己的父親。之後,每隔半月十天,楊威就開車帶著多多去鄉下父親遺留下的那個小院。順便去弟弟家坐坐。弟弟告訴楊威,村裡有個人找了他好幾次了,想買下父親留下的那個小院。楊威對弟弟果斷地說,“我們不賣。”弟弟就說,“我不賣就是。”
多多看上去很喜歡這個小院,一進院門,整條狗就精神多了:步子邁得輕盈了,尾巴也亂搖,狗頭到處轉動。還小跑著去牆角的石槽裡喝水。楊威開啟房門,多多先從他胯下竄進屋裡去,鑽過布簾子,在裡屋亂轉,又直立起來,用兩隻前爪把著炕沿向裡瞅。多多看著炕上沒有人,又衝到外屋四處亂竄。當它在這個熟悉的家裡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主人時,渾身就像散了架一樣,又恢復到以前的老樣子了,似乎比以前更加老態龍鍾了。它默默地走到裡屋,坐在土炕前,嘴裡發出嗚嗚嗚的聲音,像是在哭;渾濁的狗眼裡流露出一種無言的孤獨。楊威看著這一幕深受感動,同時一種更大的自責也在拷問著自己。每次臨走前,多多都賴在飯屋的草堆裡不願跟著楊威回城。楊威只好硬揹著它送到車上去。楊威揹著一條老狗走在村裡街道上,一路上引來大人的側目和小孩的追逐。楊威全然不在乎。他知道多多已經老了,也許活不了多長時日了,所以,他想盡心把它照顧好,不讓它做一條流浪的老狗,最後孤苦的死在街頭。
問題是,隨著多多越來越老,它開始不願意呆在樓上了。只要楊威下班回家,多多就湊上前去,用嘴叼住他的褲腳向外掙。還經常用前爪不斷地去拍打房門。楊威以為多多在家悶了,要出去散步。於是,他就背起多多下了樓。下了樓,多多也不走,乾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裡只是嗚嗚嗚的響。楊威知道多多唯一惦念的就是鄉下的它的家——也是父親的家。楊威心想:不是昨天才回的家嘛?” 楊威不回去,多多就開始在夜裡不停地拍門,致使他睡不成一個囫圇覺。楊威終於明白了多多的意思——它是想回鄉下去住。同時楊威似乎有了一種不好的預感——也許多多快要死了。想到這些,楊威決定帶著多多回老家去住。至於上班,可以開車天天趕班。可是父親留下來的那個小院也太簡陋了。於是,楊威找了一個施工隊,把父親的小院全部剷平,重新蓋了一個精巧雅緻的四合院。楊威想好了,等送走多多後,他就長期在這個小院裡住下來。
那天,楊威帶著多多回到村裡。三間青磚灰瓦的房屋顯得古色古香,兩邊各有兩間耳屋,也是仿古建造的。高高的門樓,灰色的圓筒瓦,兩邊站立著可愛的小獸。這是仿北京四合院門樓設計的。笨重拙樸的兩扇榆木大門,青黑色的鐵門環發著光。楊威站在門前,心裡激動不已,心想:從今後我要住在這裡了。從農村走進城市,如今又從城市迴歸鄉村,繞了這麼大一個彎,是為什麼呢?楊威顧不得去細想,他轉身對身後的多多說,“你不是天天嚷著回來嗎?以後咱就住在這兒不走了,這回滿意了吧?”楊威說著邁步進去,多多卻在門外徘徊,搖著尾巴就是不往裡走。楊威說,“進來,看看咱們的新家。”多多遲疑著進去了。這次,多多卻沒能像以往表現的那樣興奮和依戀。多多站在天井裡,左看看,右看看,小心翼翼地邁著步子。一切的一切在狗眼裡都變成一種可怕的陌生。
晚上,楊威站在天井裡看天上的月亮。農村的月亮又圓又亮,掛在西山山巔的松樹上。月亮看上去那麼矮,站在山頂上彷彿一伸手就能摸到。風吹進院子裡,清爽而舒適。楊威衝著躺在腳下的多多說,“這回滿意了吧?這個小院多麼好,你喜歡嗎?”多多沒有回答他的話。
早上起來,楊威起了個大早。他在東西耳房裡轉悠著,捉摸著要把其中兩間建成一個書房。書房可能會小點,可是小有小的韻味。他還想在天井的中心建一個亭子,亭子的名字就叫:賞月亭。然後再去買一把搖椅,每天晚飯後就坐在賞月亭裡看西山上的月亮……
楊威在暢想著以後的生活,不覺地太陽已升起來了。他衝著南牆根下一個寬敞的狗圈喊道,“多多,該起床了!太陽曬到屁股了!”多多沒有出來。楊威又喊了一聲,就去屋裡做飯了。做好了飯,多多還沒有出來。楊威這才去狗圈看。多多不在狗圈裡。“多多,你去哪了……”楊威一邊喊著,屋裡屋外四處尋找,小院子裡找遍了也沒能發現多多的影子。楊威走出小院在大街上衚衕裡找,甚至秸稈堆裡,石堆旮旯裡……可是怎麼也找不到多多。楊威有點著急了,不足四百口人的小山村,半個小時就轉了一圈。楊威找不到多多,只好去了弟弟家,讓他幫忙尋找。弟弟說:“一隻老狗沒了沒了,找啥呢?”楊威有點不滿意,“我一定要找到它。”弟弟無奈,只好先放下手裡木工活路跟著楊威滿村的找狗。兩個人地毯式搜尋了兩次,每家每戶都去了,也沒有發現多多的半點影子。確信多多是不在村裡了,兩人又結伴去西山上找。在中午之前,他們找遍了西山山前的所有的松林和溝坎,也是蹤跡全無。
弟弟氣喘吁吁地說:“像這樣,滿山滿峪找一條狗很難。你說它很懂人事,那麼它隨便找個地方藏起來,你能找的到嗎?”
楊威皺著眉頭:“我知道多多為啥走了?”
“為啥”弟弟問。
“多多是閒我把那個舊房子扒了……那是它曾經生活的地方,不,是跟咱爸一起生活的地方……”兩人說到這裡,誰也不再說話。沉默了好一會,楊威說:“咱爸養的這條狗重情義,講感情,想想,我都不如一條狗啊!”說完,楊威大踏步向村裡走去。回到家裡,楊威吃了午飯,背起揹包上山了。楊威找遍了整座西山,又在西山周圍的丘陵溝壑裡一直轉到夕陽落山,才疲憊不堪的回到村裡。楊威一連在附近山裡找了一個禮拜也沒有結果,多多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楊威這樣疲於奔命的尋找一隻狗,漸漸引來村人的好奇和議論。弟弟也來找過他幾次,說:“現在那條狗或許早就死了,你還找他幹嘛?”楊威不理弟弟的話,他說:“我一定要找到它。”
楊威又在山村的家裡住了一個月,其間也斷不了在村裡村外轉悠,有時也進山去。慢慢地他對於能不能找到多多已變得無關重要了,但是他已無法讓自己停下尋找多多的腳步。回到城裡後,楊威再也無心上班,找尋多多的念頭一直在心頭縈繞不去。他的夢中總是重複著一個畫面:他走在山間一條沒有盡頭小路上,一條衰老的黃狗默默地跟在身後…… 那時他就會強烈的感到兒時的溫馨和幸福……每次從夢中想來,楊威總是為這樣單純的畫面和莫名的情感交集而熱淚盈眶。
楊威辭職了。他要去尋找多多。臨走前一天,他開車去另一個城市探視女兒。還是城郊那個破舊的院子,只是在畫室裡楊威沒有看到那個乾瘦如柴、滿頭茅草的印象派畫家。前妻和女兒正在吃飯。楊威一步踏進去,前妻嚇了一跳,然後驚奇的看著楊威:“沒想到你會來?”“那個傢伙呢?”楊威問。“哦……他……”前妻看上去很為難。女兒放下筷子,看著楊威委屈地說:“爸爸,你好久沒來看我了,明天帶我去兒童公園好嗎?”楊威在女兒努起的小嘴上捏了捏,點了點頭。女兒高興地跳起來,飯也不吃了,拉起楊威的袖子轉圈。楊威順勢抱起女兒在她臉蛋上親了親。前妻悠悠地說:
“看氣色你也過得不錯啊!”
楊威說:“爸爸死了!”前妻一怔,隨後歸於平靜,卻難掩心裡的悲傷。
“你跟那個畫家過得也挺好吧?”楊威問。
“我們離了!”前妻深深吸一口氣,斬釘截鐵地說。
沉默良久。楊威說:“後天我就要走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我想你和孩子還是搬回去住吧。這是房子的鑰匙。”說著楊威把房門鑰匙、汽車鑰匙和一張銀行卡放在妻子面前的桌子上。
“你要去哪?”妻子抬起頭看著楊威說。
“去找多多。”
“多多是誰?”
“是一隻狗,爸爸留下的,很老了。”
“為什麼……?”
“它重情義,重感情,它是一隻好狗……”楊威望著遠方一抹青黛色的山巒,爍爍放光,
“為一隻狗值得嗎?”前妻說。
“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是當下我最想做的事。”楊威堅定地說。
前妻低頭想了想說:
“你不上班了嗎?”
“我已經辭職了。”楊威抱起女兒在她臉上親了親說:
“明天我來接你去兒童公園好不好?”
“好,去兒童公園……”她用兩隻小胳膊摟著爸爸的脖子,天真無邪地笑著。
“辭職了,為了一隻狗……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前妻自言自語地說道。
2014-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