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1年以來,伴隨美國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速度加快和力度加大,美國的中東戰略轉向“離岸平衡”,即力圖透過塑造中東地區平衡減少中東對美國的掣肘,美國以伊拉克為中介推動沙特和伊朗兩大宿敵緩和關係,構成了美國這一策略的核心。與此同時,為適應美國的戰略和策略調整,加之長期對抗和疫情加劇導致地區國家“戰略透支”,中東地區大國紛紛調整對外政策,使中東國際關係呈現緩和跡象,尤其以沙特與伊朗、土耳其與沙特、土耳其與埃及等地區大國關係的緩和為主。儘管這種緩和尚十分微弱且仍充滿變數,但仍不失為中東形勢的積極變化。
但是,對於長期由衝突和動盪主導的中東地區來說,今年以來的危機事態也是層出不窮。如作為“阿拉伯之春”僅存碩果的突尼西亞發生憲政危機,凸顯阿拉伯國家的轉型之困,尤其是伊斯蘭主義力量與國家轉型的複雜矛盾;伊拉克選舉結果反映伊拉克國內族群政治的複雜性,以及伊拉克與美國、伊朗關係的複雜性;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斷交、與原殖民宗主國法國關係持續緊張,其實質是中東國家尚無法擺脫殖民主義歷史遺產的影響。
在“阿拉伯之春”延宕十年之後,無論是處在格局轉換、秩序重建中的中東地區,還是面臨國家建構和國家轉型雙重使命的中東國家,都面臨著如何走出“百年中東之困”的歷史使命。
一場選舉,三次危機:近期中東的危機事態舉要
最近一段時間,中東國家國內政治發展和對外關係中的危機事態層出不窮,這裡簡要分析突尼西亞、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三國內政外交的事態。
(一)突尼西亞憲政危機凸顯阿拉伯國家轉型之困
2021年7月25日,突尼西亞總統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宣佈,解除現任總理邁希希的職務,凍結議會所有職權,此後突尼西亞再次陷入政權內部權力鬥爭與民眾抗議浪潮相交織的政治危機。據半島電視臺訊息,突尼西亞總統於9月29日任命在世界銀行工作的納吉拉·布登·拉馬丹(Najla Bouden Romdhane)為新總理,拉馬丹也是該國首位女總理。儘管突尼西亞總理空缺兩個月的憲政危機在形式上得以平息,但憲政危機背後的伊斯蘭主義力量與國家轉型的矛盾並未得到解決。
自2010年率先爆發“阿拉伯之春”以來,儘管突尼西亞的政治轉型一波三折,但相對而言是阿拉伯國家中相對平穩、成功的國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世俗力量和伊斯蘭力量——復興運動黨(與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類似)達成了妥協。此前,在突尼西亞政治格局中,總統賽義德代表世俗力量,但加努希領導的復興運動黨卻在議會中佔多數席位。這是突尼西亞總統解除總理邁希希職務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邁希希領導的內閣反映的是佔議會多數席位的“復興運動黨”的意志。
在此次憲政危機前,在突尼西亞的政治轉型中,復興運動黨經歷了在制憲議會選舉(2011年)中得勢到總統選舉(2014年和2019年)中失勢,再到在議會選舉(2019年)佔據多數席位的變化。在此過程中,伊斯蘭復興運動黨與世俗力量之間既有合作,也有鬥爭,但二者基本上實現了相互包容和妥協。這種妥協也曾經被外界視為伊斯蘭主義力量與世俗力量以及民主化程序融合的成功典範,並鮮明區別於埃及穆兄會的大起大落。但此次憲政危機表明伊斯蘭主義力量與突尼西亞國家轉型的矛盾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從本質上來說,突尼西亞憲政危機仍是中東國家宗教與世俗複雜關係的反映。一方面宗教與世俗的矛盾仍將是影響中東國家轉型的重要因素,教俗兩大陣營的極化對立,構成不少國家社會分裂和對立的根源(如埃及);另一方面,溫和伊斯蘭力量探索伊斯蘭特色的道路,融入國家世俗化和民主化程序,但其中的矛盾依然十分複雜(如突尼西亞)。
(二)伊拉克選舉結果凸顯族裔政治與外部干涉之困
根據伊拉克獨立高等選舉委員會10月11日公佈的新一屆國民議會選舉的初步計票結果:什葉派宗教領袖薩德爾領導的“薩德爾運動”獲73個席位,居於首位;國民議會議長哈布希領導的遜尼派政治團體“進步聯盟”獲38席,位列第二;前總理馬利基領導的“法治國家聯盟”獲37席,排名第三。
在本次伊拉克議會選舉中,其政治力量組合繼續體現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斯蘭教什葉派佔主導、伊斯蘭教遜尼派和庫爾德人處於劣勢地位的政治格局,但也彰顯出什葉派內部分化組合的複雜性。在此次選舉中,獲議會席位第一和第三的“薩德爾運動”和“法治國家聯盟”都是什葉派團體,共同點是都反美,但“法治國家聯盟”同時主張親伊朗。
“薩德爾運動”主導伊拉克政治勢必導致伊拉克什葉派力量對比的變化。可以預見,同時持反美、反伊朗立場的“薩德爾運動”對伊拉克政治的影響將得到加強,並對伊拉克與伊朗的關係產生深刻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伊拉克人民願望的反映。因為在2019年新一波“阿拉伯之春”影響下爆發的伊拉克民眾抗議浪潮中,抗議者都明確表示既反對西方國家也反對地區國家的干涉。2003年以來西方大國和地區國家雙重干涉使伊拉克陷入了深重的災難。
伊拉克的政治危機在本質上是從薩達姆時期權力為遜尼派壟斷向後薩達姆時期權力分割(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再到當前什葉派壟斷權力而引發的危機。
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國家權力為遜尼派尤其是薩達姆家族集團壟斷,而什葉派和庫爾德人處於權力邊緣;在後薩達姆時代初期,伊拉克重建過程中遜尼派、什葉派與庫爾德人之間一度出現權力分割態勢,釀成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教派衝突和庫爾德民族分離主義的高漲。這是導致遜尼派極端力量以“伊斯蘭國”方式進行反抗、庫爾德人謀求獨立的原因所在,但二者均遭到失敗。伴隨什葉派主導伊拉克政治,當前伊拉克政治呈現出權力為什葉派所壟斷的趨勢,但更加複雜的情況是什葉派內部的碎片化及其對美國、伊朗的不同立場,將導致伊拉克政治更加複雜脆弱。
(三)阿爾及利亞外交危機背後是殖民主義歷史遺產根深蒂固
在今年下半年,阿爾及利亞外交出現兩大危機,即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斷交,以及阿爾及利亞與原宗主國法國關係持續緊張。這兩場危機的具體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本質上都與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密切相關。
當地時間8月24日,阿爾及利亞外交部長拉馬丹·拉馬姆拉(Ramdane Lamamra)在新聞釋出會上宣佈與摩洛哥斷交。拉馬姆拉指責鄰國摩洛哥對阿爾及利亞採取敵對行動,破壞阿爾及利亞國土安全和邊境安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曾在1994年因邊境衝突關閉邊界,此後雖矛盾不斷,但從未斷絕外交關係。
從表面上看,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斷交的原因是前者譴責後者支援下的柏柏爾分離主義運動——“卡比利亞自治運動”縱火導致森林火災。但更深層次的根源是兩國長期以來的政治不信任,特別是殖民地宗主國西班牙與摩洛哥、茅利塔尼亞和阿爾及利亞圍繞西撒哈拉問題的複雜矛盾。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阿爾及利亞認為摩洛哥一直在背後支援其國內的伊斯蘭武裝組織。(參見張玉友:《一場大火讓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斷交?其實是新仇舊恨一起算》)
與此同時,阿爾及利亞與原宗主國法國的關係也持續緊張。9月28日,法國政府決定大幅減少向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公民發放的簽證數量。這三個國家都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有分析指出,移民問題正成為2022年4月法國總統大選的關鍵競選議題,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中間派移民政策在右翼政黨挑戰下正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另據法國《世界報》披露的訊息,馬克龍9月30日在與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經歷者的後代會面時,抨擊阿爾及利亞在獨立後就被一個“政治-軍事集團”把持權力,且這些當權的精英還“徹底改寫了”阿爾及利亞的官方歷史論述,其內容“並不基於事實,而是基於對法國的仇恨。” (參見喻曉璇:《與阿爾及利亞鬧僵、辦峰會挨懟:法國在非洲形象自由落體?》)
10月初,阿爾及利亞被法國大幅減少簽證政策和馬克龍“不負責任的言論”激怒,決定召回駐法大使,同時禁止法國軍用飛機飛越其領空。阿爾及利亞與法國關係緊張的具體原因十分複雜,既有雙方對殖民主義時代歷史認知理解的分歧和衝突,也有殖民主義留下的移民問題與雙方國內政治相交織的複雜因素。
危機事態折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東發展之困
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世界各地區均構成了強烈衝擊,而百年來飽受磨難的中東地區更是困難重重,從2010年底以來延續至今的長週期“阿拉伯之春”便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東的集中表現。
(一)歷史遺產與現代性的矛盾困境
首先是帝國遺產。中東地區作為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曾產生了一系列對人類歷史產生深刻影響的帝國,尤其以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該地區的核心帝國為巨,而羅馬、拜占庭、俄羅斯、蒙古等外部帝國則與中東有密切互動。帝國爭霸留下的歷史遺產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當今土耳其、伊朗兩個主要地區國家的地區領導權訴求無疑與奧斯曼、波斯帝國遺產的沉渣泛起密切相關。
其次是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殖民主義對中東的深刻影響不僅在於透過肢解奧斯曼帝國強加給該地區的不合理的民族國家體系,更在於源自西方的理念、思想、制度等所謂現代性因素的輸入,並突出表現為民族主義、世俗主義對中東的深刻影響。
最後是中東傳統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歷史遺產。儘管中東存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三大一神教,但對當今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中東三大主體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共同信仰的伊斯蘭教,而源自西方的現代性則包含了源自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文化和希伯來-基督教傳統,因此西方現代性對伊斯蘭的衝擊事實上和中東地區三大一神教的“正統之爭”密切結合在一起,並由此影響了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猶太文明的複雜關係。
當前,無論是民族國家作為現代政治單位在中東的“水土不服”,還是世俗化作為西式現代化在中東所激起的宗教與世俗的尖銳矛盾,都與帝國遺產、殖民遺產、傳統文化遺產及其複雜關係密切相關。從這種角度看,中東伊斯蘭國家需要消解上述三大遺產,構建具有自身特色同時又吸收外來合理因素的現代性,亦即找到合適的政治組織、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二)自主性、開放性與依附性、封閉性發展的矛盾困境
擺脫殖民主義歷史遺產,實現自主性發展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共性問題,但是由於中東地區在地緣上與歐洲距離更近,中東地區衝突便於外部大國進行干預,多數國家在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選擇方面自主性不足,中東區域一體化和地區主義孱弱等等,都構成了中東國家發展缺乏自主性的根源。
中東國家的依附性發展或封閉性發展儘管有十分複雜的客觀根源,但無疑與其自身的失誤存在密切關係。在實現獨立後,儘管中東國家進行了長期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反體系鬥爭, 其政治力量主要體現為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義和70年代以後的伊斯蘭主義,但是二者都沒有處理好獨立自主與開放發展的關係。
例如,埃及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表,在其發展程序中始終存在對外依附的嚴重問題,納賽爾時期先依賴西方後依賴蘇聯,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時期又嚴重依賴美國和西方,尤其是落入西方“新自由主義陷阱”,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在“阿拉伯之春”中轟然倒下的重要根源;土耳其獨立後便把西方化、融入西方作為其國家戰略,但在加入歐盟嚴重受挫後開始出現嚴重的身份迷失,甚至出現“雙泛”思潮的沉渣泛起;伊朗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嚴重依賴西方,而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又走向“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自我封閉,這是今天伊朗發展之困的重要根源;更有甚者,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則在嚴重依賴西方和強烈反西方之間搖擺,進而陷入國破家亡的歷史悲劇。
簡而言之,中東國家至今尚未解決好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係,而是在依附與封閉之間搖擺。
不僅中東國家自身發展存在依附性或封閉性的弊端,中東地區也缺乏集體自力更生的地區一體化機制,其深刻根源在於地區內部對抗、信任嚴重缺失和外部大國長期強勢干預,使地區合作徒有其表,甚至出現了伊斯蘭合作組織“難合作”,阿拉伯國家聯盟“不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不和睦”的悖論,最終使中東地區成為地區主義發展最為薄弱、地區合作水平最低的地區。
因此,中東國家實現自主與開放的平衡,中東地區走向集體自力更生,才是中東走出發展之困的必由之路。
(三)國家建設與治理能力的多重困境
中東民族國家體系形成於一戰後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肢解,民族國家體系形成的外部性特徵,國家內部部落、宗教、教派、族群等傳統組織的大量存在,使得中東民族國家建設異常困難,國家治理能力嚴重不足。在“阿拉伯之春”中,共和制國家多發生政權更迭,而君主制國家則面臨深刻的轉型壓力,中東地區也成為當今世界安全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最嚴重的地區。
首先,中東國家亟待解決威權和民主的關係。“阿拉伯之春”民眾抗議浪潮的重要訴求在於民生和民主兩大訴求,但發生政權更迭國家的實際情況表明,由於缺乏獨立的領導階層和政治理念,中東國家在如何建設民主方面並無具體的方案,而當前轉型阿拉伯國家也多數重回威權體制。
其次,宗教與世俗的關係。近代以來,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呈現出世俗化不斷加深的趨勢,但世俗與宗教的關係鮮有和諧的典範,埃及始終存在穆兄會代表的伊斯蘭主義力量與民族主義政權的抗爭;伊朗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劇烈的世俗化之後轉向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斯蘭化;土耳其則在實行了百年激進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之後,出現向宗教回擺的所謂“消極世俗主義”。因此,未來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無論如何都很難徹底排除宗教的影響,實現宗教與世俗的理性平衡任重而道遠,更要面對遏制極端主義的難題。
最後,國家與非國家的關係。中東民族國家建設困難,國家治理能力嚴重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東國家始終處於超國家與次國家力量的擠壓和撕扯之中。中東地區的超國家力量並非地區合作層面的地區組織,而多是泛民族、泛宗教以及跨國教派、跨國族群等力量,次國家力量更加複雜,包括具有地區和國際滲透和影響能力宗教政治組織(如穆兄會)、宗教極端組織(如“基地”組織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和民族分離力量(如庫爾德人)。超國家和次國家力量對國家的消極影響也恰如某學者所言,“在中東,次國家和超國家認同與國家認同展開競爭,激勵著跨國運動,並限制著純粹的國家中心主義的行為。”
當前,對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大疫情下的中東國家而言,面對著遠超過其他地區的多重壓力,協調歷史遺產與現代性的關係;從依附性、封閉性發展走向自主性、開放性發展;完成國家建設和治理能力的建設,無疑是其在21世紀的三大長期課題。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sponsored links
中東睿評|地區局勢緩和充滿變數,中東走出百年之困道阻且長
分類: 農業
時間: 2021-11-01
相關文章
陳忠洲:被譽為國寶藝術家,曾為天安門創作巨幅畫作
一位書畫家,如果作品被國家機構收藏那一定是作品價值與藝術家影響力的象徵,同時如果能夠被當做國禮贈送給他國領導人,那更是有非凡的意義,而被譽為國寶藝術家的陳忠洲就得到了這樣的殊榮,今天大賞藝術就帶大家瞭 ...
專訪: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上採取了有效行動——訪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總幹事布魯諾·奧伯勒
新華社昆明10月10日電 專訪: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上採取了有效行動--訪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總幹事布魯諾·奧伯勒 新華社記者張家偉 董修竹 劉萬利 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已經採取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措施, ...

0比3廣東第4敗!遼寧的段放被中國女排低估了,發揮得當威力極大
更多體育資訊,歡迎關注"超燃女排時刻"! 全運會第6個比賽日,女排成年組迴圈賽第5輪第一場,遼寧女排對戰廣東女排. 首發陣容如上.這場比賽對於遼寧來說非常關鍵,其必須大勝才能基本奠 ...
張維為、阮儀三、李漢勤:中國古村落的保護
"實踐證明,現代化與傳統保護不僅可以並行不悖,而且可以相得益彰,保護古村落可以成為我們文化自信的非常重要的載體." "古村落是中華禮儀文化的結晶,學習傳統不僅是外部的模仿 ...

農業農村部強農惠農35條重點政策
2021年,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1號檔案精神,圍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突出保供固安全.振興暢迴圈,國家將繼續加大 ...

遼寧除了瀋陽大連,最有發展潛力的是這三座城,有你的家鄉嗎?
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龍頭,遼寧省今年上半年經濟形勢呈現了明顯的回暖勢頭,地區GDP實現12641.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了9.9%,全省一般公共預算同比增長了12.7%.從省內各市情況看 ...

生物寶庫“蜀”我多樣②從瀕危到易危“國寶”保護交靚卷
10月11日至10月15日,<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簡稱COP15)第一階段會議將在雲南省昆明市召開.四川是全球34個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之一,是中國乃至世界的珍貴物種基因 ...

湖北冷知識:推薦湖北這23個世界之最和中國之最,你還知道哪些?
寶藏湖北,時刻都美 湖北省,簡稱"鄂",地處中國中部,位於長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關於湖北,你知道關於它的哪些相關冷知識?今天小編就帶大家認識湖北這23個世界之最和中國之最 ...

劉晏含加盟讓遼寧成全運黑馬,攜手丁霞顏妮爭冠,2大頑疾已解決
女排全運會成年組已經結束了3輪比賽.老牌強隊遼寧女排展現出了黑馬之姿,以2勝1負暫列第四,極有希望晉級四強參加淘汰賽.前三場球,遼寧險勝山東.不敵天津和橫掃浙江.那麼,遼寧女排為何會在全運會上大爆發呢 ...

塔利班下令追查失蹤的國寶,看看阿富汗的國寶都什麼特徵
素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稱的阿富汗,有著跨越5000多年的歷史.在這個"十字路口"的國家,曾經有來自歐亞多個地區和民族進入這裡,數種文明在這裡交匯,產生了獨特的 ...

劉華清將軍堅持用30億購進“蘇27”,開啟了中國空軍新時代
1990年,74歲的劉華清將軍前往蘇聯購買戰鬥機,蘇方接待官很怠慢,劉老將軍住處連床墊和被褥都沒有,只得睡床板蓋軍大衣入眠-- 一場神奇的酒局,開啟了一段中國空軍的時代! 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 ...

遼寧竟然藏了這麼多大美女!這18位女星容貌卓絕,氣質出眾難複製
提到娛樂圈美女,很多人都認為北方美女最多,想刊刊放眼望去,遼寧這絕對是娛樂圈美女的大本營,多少氣質出眾,容貌卓絕的女星都出生於此. 最重要的是遼寧的美女,糅合著南北方的優點,沒有北方人的高大粗獷,卻有 ...
奇妙的朋友⑧|“國寶”褐馬雞
來源:長城網 長城網訊(記者 高航 喬婭 吳苗苗)<奇妙的朋友>以河北小五臺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佈設的紅外相機和遠端攝像頭拍攝的珍貴動物影片為素材,用一個個動物情節呈現綠水青山中動物的鮮活面 ...

評展|典藏國寶之外,古書畫的觀看視角
拿破破Napopo "林下風雅--故宮博物院藏曆代人物畫特展(第二期)"這些天持續引發關注,這樣的展覽策劃與呈現有什麼突破?對當下的書畫策展有何啟發? 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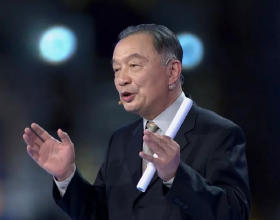
溫鐵軍:中國崛起不易,不斷被美國“吸血”,像頭牛被扒了兩張皮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她曾繁榮鼎盛.八方來朝,也曾閉關鎖國.跌落塵埃,她有上下五千年的輝煌,也有苦難深重的歷史. 從清朝滅亡到新中國成立的這段時間,中國也像周邊其他國家一樣,經歷過被歐洲殖民者狂轟 ...

新能源時代,鋰礦就是石油,美國虎視眈眈,中國如何保護海外鋰礦
前言: 如果說鐵礦石代表了現在,那麼鋰礦就是未來. 不幸的是,這兩樣可以改變世界格局的戰略礦藏,中國都儲量不足.更不幸的是,跟鐵礦石一樣,全球主要的鋰礦分佈地,又在澳大利亞,和號稱美國後花園的南美洲. ...

正義還是缺席了!世貿會議上中國遭不公平裁決,美國又得逞了
中美貿易之間的戰爭從未停息,在各行各業都進行著激烈的交鋒,然而一則訊息的出現再次重新整理人們對美國的認知.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製造商從美國手裡奪得了很多生意,特朗普時期為了能夠滿足對選民的承諾,對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