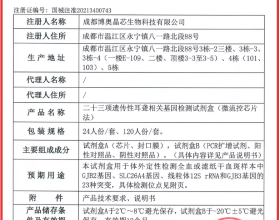外籍兵團中國兵(二十一)
軍中同袍
米丘克-奧列格是我最好的朋友,身高一米九五,人高馬大,也是一位游泳健將,是我們蓋亞那的游泳冠軍,退役後他在馬賽安家落戶,在馬賽大學做電腦維護員,夏天一直還兼職做海濱救生員。
奧列格是俄羅斯人,同父母生活在愛沙尼亞,在當地一所大學讀經濟,但因為時局和經濟原因未能畢業就闖蕩江湖,直到進入外籍兵團。他說在愛沙尼亞讀大學時最為喪氣,愛沙尼亞人說他們是俄羅斯人,加上歷史的積怨被歧視為外國人,但俄羅斯也把他們這些生長在蘇聯前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人當做外人,根本不歡迎他們迴歸俄羅斯,就是舅舅不疼姥姥不愛,裡外不是人。
所以他決定闖蕩江湖,遊走歐洲。說到他的身高馬大,許多軍中戰友都覺得這類人有時會非常危險,尤其是喝酒後耍起酒瘋來會不計後果。確實奧列格有過一次在軍團節日上喝多了大戰四名軍警的戰鬥史,結果是被投入監牢醒了一夜酒。這種事情在部隊實在是稀鬆平常,尤其是聖誕節的聚餐會經常是當兵的酒後大打出手的時候,人們經常會用打碎多少酒瓶來統計戰果。第二天我問奧列格昨天事還記得嗎?他憨厚地笑著說不記得了。還有一次他在外面喝酒多了夜裡回來同宿舍裡的一個老兵開玩笑,捏著人家的鼻子說醒一醒,結果對方鼻樑被擰斷。
我同他的交情也是逐漸發展的,一開始也是非常謹慎,但畢竟都是有大學背景,有些惺惺相惜,而且我對俄羅斯的瞭解相當豐富,我們可以大談阿爾巴特大街和維索斯基,所以彼此的戒備完全開啟,以致每次他喝醉酒我都可以隨便接近而毫不膽怯,周圍有些人則會明顯感覺心生膽怯或者是敬而遠之。確實他對他不喜歡的人也會惡言相向,但待人卻絕對分寸到家,即使是喝醉了,讓我覺得人還是有著巨大差別的,有的人酒後亂性,甚至分不清家人和朋友,在部隊上大多數都是這類人,但奧列格絕對不是,無論他如何爛醉,我都不會覺得他會對我有危險。
一次在蓋亞那河邊夜裡換崗,我接替他站崗時發現他身邊有個酒瓶子,人也飄飄然了,我說你趕緊回去好好睡覺吧,他站起來走了兩步說,啥呀,太多人了,於是就在原地的木樁上倒頭大睡。接下來當官的沒有出現,只要我不舉報,他就平安無事嘍。其實說到底人還是講究人品,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對待惡人毫不相讓,對我則禮讓有加,加上他受過高等教育,還屬於我認為的典型的聰明的俄羅斯人,而且他人也樂觀,喜歡幽默,所以在部隊裡還算自得其樂。
像兵團裡面一向認為的部隊裡面缺少不了酒和女人一樣,他也樣樣全沾。一次我們若干人外出夜裡去酒吧,他見到鄰桌一個女郎漂亮,就點了一捧鮮花獻殷勤,女郎接過鮮花後還吻了一下他臉頰作為感謝,然後抱著鮮花翩然離開。西方人在男女之間的待人接物上同我們東方人有許多不同,儘管這種差別隨著東西方的交流和全球資本化而縮小,但許多東西還是根深蒂固的潛印在人們的頭腦裡。我們的許多同胞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浸淫後,看紅樓夢都對林黛玉只有純情的遐想,當然會與外籍兵團的酒池肉林大相徑庭。儘管腦白質裡面可能有許多差異,但也不排除偶爾在酒精的麻醉後有些殊途同歸。人類的個性與共性永遠同在。
·
道道霍夫是我在兵營中另外一個好朋友,他是保加利亞人,樂天派,整天嘻嘻哈哈,但人品好。舉個例子,我們在部隊的閱兵活動極多,每次閱兵不僅要皮靴擦得鋥亮,有時還要系白鞋帶。黑皮靴子上系白鞋帶,基本上一次過後就染黑,所以要經常備好白鞋帶,但也難免有忘記的時候。我剛剛同道道霍夫一個連隊不久閱兵時,他正好沒有白鞋帶了,我就借了他一副,之後他很正式地還了我一副,於是我就看出來他是一個可以成為朋友的人,因為部隊裡不佔奸取巧的人並不多,而且還經常明目張膽,倚強凌弱,如同老兵欺負新兵天經地義,幾乎是全世界兵營的軍規。
道道霍夫是保加利亞人,所以同俄羅斯人有天然親切的因素,又會講俄語,所以他同奧列格的關係也很好,因此我們幾個週末會經常出去玩。有一次晚上我們去馬賽,在酒吧裡面酒過幾巡後都有些醉意,尤其是道道霍夫最厲害,當時還有一個他的保加利亞戰友也在,我們說要轉移到旁邊的夜總會去玩耍。外籍兵團的政策是出了兵團大院必須穿外出軍服,只有服役五年以上了才可以便裝出行。
結果在夜總會門前我們都被拒絕進入,酒意最大的道道霍夫當然不幹,沒有幾句話就動起了拳腳,我們也只好加入混戰,但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們發現幾個回合就被對方的門衛給扔出了門外,足見他們使用的保鏢也都是高手,我們都根本不是對手。後來部隊上的老兵告訴我們,馬賽的夜總會不接待外籍兵團士兵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外籍兵團士兵在那裡打鬥太多,早已是不受歡迎的人,為了有效阻止外籍兵團的粗魯士兵騷擾,所有夜總會都聘請了拳腳靈活的打手,讓這些臭當兵的佔不到便宜。後來我們談到這些事情時,有位在場的法國老兵說,你們為什麼不帶刀?看熱鬧不嫌事大可能是古今中外的通病,而平沙漠漠夜帶刀則是外籍兵團士兵的傳統。
第二天我們酒醒後還回憶說,要是馬蓋拉也跟我們一起就好了。馬蓋拉是芬蘭人,練過十年柔道,身材不高但十分結實。奧列格和道道霍夫一次跟我說,他們有一次和馬蓋拉到馬賽玩,走在一個小巷裡突然串出一條大惡狗撲向他們,馬蓋拉當即就是一拳打在狗頭上,惡狗當即翻了白眼。奧列格笑著跟我說完,道道霍夫在一旁點頭說他在場。其實無論這個故事真假,我都相信馬蓋拉確實身手不凡,因為有一次我跟他鬧著玩推推搡搡的就感覺到他一定有兩下子。
不過他的問題在於過於喜歡酒精,鬧過許多笑話,或者說觸犯紀律的事情。他曾經一度和我住在一個宿舍,有一天晚上他從外面喝醉了回來,到早上六點鐘起床號時酒還沒醒,有意思的是他也知道起床號響了就要穿衣下地,於是就抓起自己的運動短褲當做球衣往頭上套,但他是個大腦殼,從運動短褲的褲腳出不來頭,我們旁邊的人看到後不斷髮笑,結果當然是他迷迷糊糊無法正常上操,被送去做了一個禮拜的牢。不過從馬蓋拉那裡我知道了芬蘭話不在印歐語系裡面,卻是同匈牙利語相近,都屬於烏拉爾語系,所以芬蘭話同匈牙利話有許多相似處,可能像法語同羅馬尼亞語也非常相近,羅馬尼亞人通常幾個星期就學會法語了。
索博達是個說起話來好像無所不知的捷克人,他同我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服役結束後到德國去開一箇中餐館,並且和我合作,一定要體現出中西合璧的特色。還說他自己是一個職業冰球運動員,最喜歡同蘇聯球隊在冰場上打架。他還自稱到過臺灣,是為飛利浦公司出差。他還告訴我說,波西米亞著名的水晶產品質量好壞就在於鉛的含量多少。關鍵是他有一次從捷克探親回來還給我帶回一個水晶花瓶禮物。
他對中國最熟悉的人物就是毛澤東,我則開玩笑地回敬到,你一定是胡薩克的親戚,坐過267號牢房,同伏契克有淵源。我也熟知《絞刑架下的報告》,伏契克最著名的格言是:‘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他的名字索博達的意思是自由,但他對斯洛伐克民族卻有許多歧視言論,還告訴我波蘭在歷史上三度亡國,毫不掩飾對波蘭人的蔑視,還有對猶太人也極端歧視,讓我感受到歐洲民間就是一直有對猶太人的根深蒂固的歧視。
也許是猶太人的老家同阿拉伯人一樣都不是歐洲,所以信奉白人至上的歐洲人從來都不把猶太人當同類,而是一直當異類對待。加上猶太人聰明過度,被認為強取豪奪了太多的財富資源,所以歷史上一有風吹草動就首當其衝,仇富和嫉妒是人類改不了的老毛病。比如普魯東就說過‘財富就是盜竊’的著名言論。索博達還對在文學史上寫過不朽著作的猶太作家卡夫卡進行汙衊,說卡夫卡是捷克人,所以他有發言權,稱卡夫卡的生活境況根本就不像被描述的那麼窘迫,他的作品都是由猶太人幫助出版,猶太人又自行購買。我則以為索博達對卡夫卡作品的含義並不瞭解,只是從對猶太人偏見的角度來講些不敬言辭。
原創連載 期待再來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