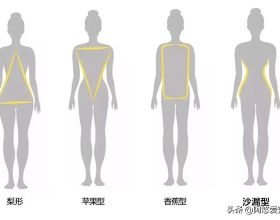曹斐 Sato攝
《曹斐:時代舞臺》展覽現場 攝影Stefen Chow
曹斐、歐寧 《三元里》(2003,單頻錄影)
今年3月,當代藝術家曹斐在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最為全面的回顧展《曹斐:時代舞臺》。展覽以“南方遊戲”“都市樂園”“車間內外”和“另類實境”4個主題展開,對曹斐過去20多年的創作實踐和藝術發展脈絡進行集中呈現與梳理,引發了業界和觀眾的極大關注。
10月2日,曹斐回到故鄉,在廣州四海城·藝術長廊,以“回到南方”為主題,與聽眾一起探討,人工智慧、虛擬實境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的新面貌與新動向。活動現場還播放了曹斐團隊打造的5分鐘短片《無人之境》,講述一位“行者”從鄉村走向城市、從現實走向虛擬、從過去走向未來的故事。
身為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曹斐出生於廣州一個藝術之家,自幼受到雕塑家父親曹崇恩及同為藝術教師的母親廖慧蘭的薰陶與培養。青年時代,曹斐就讀於廣州美術學院,在MTV流行文化和手持DV發展的影響下,她創作了反映當代美院學生生活的影像作品《失調257》,從此走上藝術道路,進入國際視野,成為活躍於國際舞臺的知名中國藝術家。
“我是一名藝術家,也是一個普通人,我所經歷的時代與所有觀眾都是一樣的,只是我運用藝術的手段將大家共同的時代經歷展現了出來。”在曹斐看來,這次展覽並不是一場“回憶錄”式的成果展,“時代”就像包羅永珍的容器,而展覽是藝術家與觀眾之間進行情感記憶交流的舞臺。
近年來,影像逐漸成為當代藝術的“當紅”形式。在曹斐看來,科技是沒有情感的,但它可以用來塑造情感,而這正是時代賦予當代藝術家的任務之一。作為影像藝術最早的探索群體一員,曹斐運用影像、戲劇、虛擬現實技術和裝置等多元媒介,以超現實的表現方法,反映了全球化浪潮下中國社會的時代變遷以及社會疾速發展對個體生活的影響。
時代與技術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藝術與藝術家如何自處?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曹斐說:“我最近第一次讀村上春樹的《1973年的彈子球》,這部小說成書於四十年前,這麼多年過去了,人類的處境、疏離和孤獨從來沒有改變。所以,重要的還是作者,以及他們留下的能震撼人類靈魂的作品。”
【線下體驗藝術家建立的“時代樂園”】
羊城晚報:今年在北京展出的“時代舞臺”是您在國內的首次個展,也被認為是對您此前藝術的一次梳理和回望?
曹斐:“時代舞臺”的策展人將展覽分為了五個部分,其中一個部分叫“南方遊戲”,裡面有很多作品都來自我在南方、在珠三角的生活經歷和思考,比如2003年的作品《三元里》、2006年的《誰的烏托邦》等;而在展廳設計上,也體現了像工棚、茶餐廳、綠植這樣的“南方符號”。
我在和策展人討論的時候,就明確提出,我才四十多歲,不能把展覽做成八十歲那樣的個人回顧展。所以展覽最後沒有像傳統的回顧展那樣有明確的時間線和既定的觀展路徑,而是任由觀眾自由選擇與不同時間創作的作品偶遇。有人說這個展覽無意間成為了“網紅展”,我想,年輕一代人大多在線上成長起來,但他們也需要線下體驗。甚至有人覺得,它像一個由藝術家創建出來的時代樂園。
羊城晚報:很多人都說,從您的展覽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看見的“時代”。
曹斐:過去不少人對我的作品可能只停留於道聽途說,而在本次展覽中我幾乎一次性地把所有作品拿了出來,也包括對我影響深遠的個人成長物件。這些展品、物件都記錄著我所身處的時代,它們呈現了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的種種場景,因而觸動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們。
時代是一個容器,包羅永珍,我的初心是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到更多普通觀眾。
搭建展廳的工頭和我同年出生,他看見展出的我小時候聽的音樂卡帶、收藏的偶像老海報後,很感慨,無形中覺得我和他之間的距離其實很近。觀眾可以看到,作為藝術家的我也是和大家在一個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有的人成了白領、成了老師,有人成了工頭,只是我成為了藝術家。
【“桌面時代”更需要走進“田野”】
羊城晚報:您覺得“代際”對於藝術家和藝術創作而言,有怎樣的影響?
曹斐:我現在擔任不少獎項的評委,面對的參評者裡90後已經是主力,甚至有00後的。從我過去被別人評,到今天評年輕人,藝術界永遠追求新的人、新的東西、新的表達。在我看來,無論哪一代人都有其自身的語言表達、侷限和價值觀,都受到時代的塑造,沒有好壞之分。現在更年輕一代的作品,藝術媒介已經發生了轉變,如果說今天是一個“桌面時代”,則網路經驗和美學很大程度上已經佔據了他們的表達。
羊城晚報:“桌面時代”……但您常提到藝術創作要到“田野”去,為什麼強調“田野”?
曹斐:藝術家要感知和表現世界的變化,就需要去“田野”,即現場,而不是停留在二手經驗和螢幕經驗。現在獲取資訊的渠道越來越多,透過影片、播客等等,但我們要不要去求證,要不要釐清資訊和事實之間的誤差?在體驗、考察之後形成自己的見解,轉換成真正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
我曾經到一些西方藝術院校訪問,看見很多年輕創作者窩在自己的工作室裡足不出戶、埋頭“創作”,我給的建議是鼓勵他們多出去走走、看看,在“田野”裡可以接觸到不同階層的人,鍛鍊溝通的能力,增強我們協調自身和外部世界平衡關係的能力。
我年輕時候在廣美上學都要下鄉,要和村民們同吃同住,這是非常好的體驗,透過與他們的交流,瞭解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生存方式的差異。當藝術家要表現一個物件,並不能靠憑空虛構出來。
羊城晚報:廣美和廣東是您的出發點。這裡給您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曹斐:這裡不得不提及我的父母,他們上一代藝術家用寫實的、凝聚的方法表達我們的歷史、英雄和偉人,我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長大的,也深深受益於此,親眼目睹我父親如何用這樣的藝術方式去表現時代變遷。我的第一部DV機是父親送給我的,我在美院的時候還沒有影像專業,只有國、油、版、雕等傳統專業。
很多人問我和父母一輩有什麼不同?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我和他們都是一樣的。他們記錄時代,我也在記錄時代,媒介不過是一種手段,要表述的事情是一樣的。
有人曾說我是“亂棍打死老師傅”(笑)——不是電影科班卻去做片子,不是攝影出身卻拿了攝影獎。這可能跟我生於南方、長在藝術家庭有很大關係,我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養分,這也讓我的創作沒有邊界,不設限反而讓人可以超越某些圈子裡俗成的、先驗的東西。
【虛擬創作如何使人得到共情】
羊城晚報:今天影像已經成為藝術界常見的手段,甚至是潮流。影像藝術是否也形成了某種固化、俗成的定式?
曹斐:2000年我剛開始做影像的時候,大多展覽還都主要由架上作品組成,出現一兩個電視機,已經很難得。而今天,已經有人說抖音短影片這麼風行,會不會對影像創作有衝擊?事實上,無處不在的螢幕和影像已經將我們的視覺體驗稀釋了。今天年輕人的影像很多已經不是講故事了,甚至它成為了新的“顏料”。
然而,如果現在說固化,可能為時尚早,相反影像將會更加普及,媒介的衍生會成為擁有更多未來可能性的“顏料”。反而是藝術家不能“固化”自己,要往前走,找到準確表達我們當下的途徑。但是,我們也並不能簡單認為繪畫、雕塑、攝影是“落後”的媒介,只要你對自己使用的媒介有足夠自信,做得足夠好,藝術最終都是殊途同歸、觸動內心、通向靈魂的。
我最近第一次讀村上春樹的《1973年的彈子球》,這部小說出現在四十年前,這麼多年過去了,人類的處境、疏離和孤獨從來沒有改變。所以,重要的還是作者,以及他們留下的能震撼人類靈魂的作品。
羊城晚報:您在創作中與流量明星合作,使用VR、AR等新技術,甚至將作品放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的高樓上。這些“破圈”之舉有什麼特別的意味?
曹斐:當時我受委託在香港的地標最高的貿易大樓外表面上創作LED影片作品,最終我呈現了“吃豆人”,源自小時候玩的電子遊戲,它能喚起很多80後同齡人共同記憶。
對我來說,這是超越美術館的創作。到美術館參觀的人可能只有兩三萬,但維港的“螢幕”面向的是上百萬人。對於一個普通的香港人,他不知道作品是曹斐的,並不重要;但在他某天下班,在巴士上,在渡輪上,看到這麼的一幕,想起小時候玩過的遊戲,會心一笑,或驚訝,或好奇,對我而言已經足夠。
像我和流量明星的合作,也不會把他們拍得有多完美、多好看,當這些作品出現在美術館之外的公共場所,引發破圈的話題與討論,可能會更有趣。
科技不一定有情感,但如何能用虛擬創作使人得到共情呢?在VR作品《永不消逝的電波》裡,我著重嘗試讓觀眾體驗到來自虛擬媒介的情感敘述。對我而言,藝術就是塑造情感,無論這些情感是和過去關聯的,還是連線未來的。
圖/受訪者提供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