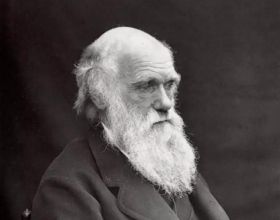作為寫作者,今年43歲的徐則臣不算年輕,但2019年他憑藉《北上》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成為這個四年一屆大獎最年輕的獲得者之一。
談及寫作的初衷,古往今來,每一個寫作個體依然會有自己獨特的理由。比如加西亞·馬爾克斯說,他寫作是為了讓朋友更喜歡他;博爾赫斯說,他寫作是為了使時光的流逝讓他安心;莫言說,他寫作是為了頓頓都能吃上餃子;智利的大詩人聶魯達說,成為一個詩人是他從小就有的願望。徐則臣則有著不同的理由——到世界去。
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生活在別處”,自幼生活在一個偏遠小村莊的徐則臣,一度認為四十里外的縣城,是想象到的世界上最遠的距離。“那是一個鄉村少年遙望世界的夢,我覺得我在世界之外,縣城就是那個繁華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乃至世界的盡頭。我一直想要到世界去。”徐則臣說。
少年時,徐則臣有個鄰居,每天騎摩托車去縣城的一家工廠上班。聽鄰居說最快十五分鐘可以騎到縣城,徐則臣羨慕得口水直流,認定摩托車是世界上最快的交通工具。此後很多年裡,徐則臣一直夢想擁有一輛自己的摩托車,想象著騎上去一定很拉風;後來他來到美國,在高速公路上看見一支年齡均在六十歲以上的老同志組成的哈雷摩托車隊,他們確實很拉風。
當鄰居騎摩托車每天去縣城時,徐則臣正在放牛,每天騎著牛晃晃悠悠到野地裡給它找草吃。後來,他終於去了縣城念高中,覺得縣城真大。為了防止迷路,他把每條路都記得清清楚楚。印象如此深刻,以致後來到了更大的城市,總是轉向,總覺得人家南北主幹道方向不對,應該是東西路,只因縣城最重要的一條路是東西走向的。
到了縣城後,徐則臣發現它不是世界的中心和盡頭時,便想去更大、更遠的地方了。“生活還是應該在別處。我要繼續到世界去。”他解釋。
高考之後,徐則臣去了一座小城市念大學。唸完大一、大二,他又想到更廣闊的世界去,經過四輪考試,大三、大四到了南京讀書。本科畢業工作兩年,他的病又犯了,想到北京去,然後又考了研究生到了北大,留在北京。這不是結束,他開始一次次出國。伴隨著不斷地到世界去的,是寫作、是自我表達。“我需要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疑難所困惑坦率地說出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寫萬言文。”徐則臣說。
“如果以寫作論,到遠方去、四處遊走、周遊列國,可以算作是身體的寫作;而寫作,卻是一種精神的旅行。當你沒法及時地到世界去時,寫作滿足了你出走的、到世界去的慾望。”徐則臣說,當自己輕描淡寫地說,曾不斷地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時,“聽眾可能會覺得我一直在路上,就沒停下來,到世界去的慾望也從未被憋屈,事實肯定並非如此。兩次位移之間總是擠壓了漫長的時光,如此之漫長與煎熬,我必須透過文字去完成一場場想象中的旅行。”
在徐則臣看來,文學歸根結底是一場最為經濟的精神之旅,既可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也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這些年,我用文學當摩托車,一直行進在到世界去的路上。當然,當寫作成了一種職業和日常生活,你會發現,你已經離不開寫作了。寫作成了你自我表達的需要,成了你自我確證的前提,成了你之所以是你的必要條件。”徐則臣說,就像亞里士多德說的,寫作是你的“是其所是”。
“一個人寫作,是因為他有話要說,不說真的會憋死。有話要說,因為他對這個世界還有激情,還有不滿,他希望這個世界能好一點、再好一點、更好一點。”徐則臣認為,一個人可以為人生而藝術,可以為藝術而藝術,但說到底,他不得不為“社會”而藝術,因為從內心中會自發地追求寫作及物、有效,在眾多可能的指標上立竿見影。
徐則臣認為,遙想、不平則鳴都不能概括寫作本身,寫作還是思考、探尋和發現的最重要的方式。以近年來的寫作經歷為例,他突然發現,經由寫作,對“到世界去”“生活在別處”有了新解,而這個新的解釋同樣成為他繼續寫下去的理由。
為闡釋新解,徐則臣分享了一個故事:一個年輕的窮光蛋,一直想尋到寶藏。一天夜裡夢見一個老神仙告訴他,你要出門去,你要左走、右走,過山、過海、過大河、過森林,然後左轉、右轉,一直走。有一天你來到一個地方,你在那兒開始挖,你就能挖出財寶。這個年輕人就按照這個老神仙的指點,左轉、右轉,左轉、右轉,然後翻山過河,穿過森林和草原,一圈下來,鬍子一大把,頭髮也白了,走成了一個老頭,終於來到那個老神仙指定的位置,開始挖。問題是他來到那個地方時,發現那是自己的家,在自家的屋簷下挖出了財寶。
有人會問,既然財寶就在家門口,有什麼必要出去?“這是個好問題。只是,倘若沒有這一圈周遊世界,你永遠不會知道財寶就在家門口。你從來都認為,家門口是不會有財寶的。這是你根深蒂固的偏見與盲區。”徐則臣說。
有人也提出另外一種猜想,對最後變成老頭的這個年輕人來說,挖到財寶當然是一件高興事兒,要沒挖到呢?他是不是會一屁股坐下來,抱著腦袋痛哭,後悔耽誤了工夫?徐則臣認為未必如此。變成老頭的年輕人也許會發現,最大的意義與樂趣其實是在路上,他會自豪於半生漫長的尋找,經驗大千,閱盡人世,見了多少好東西,就算沒沾著財寶的邊兒,這輩子也值了。
“這其中,有故鄉與世界的別樣的辯證關係。我們通常的理解裡,世界就是遠離故鄉的地方,所以生活總在別處;但闖蕩過世界的那些人,回到故鄉他們可能會發現,一直孜孜以求的世界,正在家門口。故鄉也可能是世界。寫作於我,已然成了思考和探尋自我與世界的方式。”徐則臣坦言,自己尚有疑惑,且有話要說,那就寫下去。
來源: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