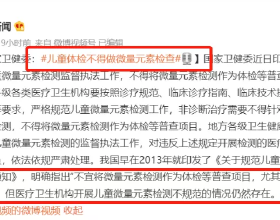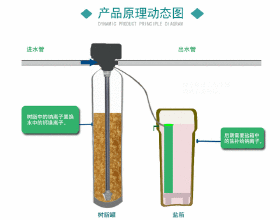“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生於繁華、終於落拓的曹雪芹自然深諳其味,他一生“酒渴如狂”、寓居香山黃葉村時仍難改嗜酒“習性”,著書作文必要以美酒相伴。歐陽修言“醉翁之意不在酒”,曹公“佩刀質酒”作書,亦不在乎山水之間,而在澆胸中之塊壘,一如《紅樓夢》第三十回回末總評:“愛眾不常,多情不壽。風月情懷,醉人如酒”,可作全書主旨看——酒在《紅樓夢》中,不僅僅是一種飲料,更是對歷史文化與世俗風情的反映,可敘人間富貴,可感人情盛衰;紅樓一夢,溫柔鄉中,酒之流金閃爍,亦可沉醉無數看客。
無酒不成席
周汝昌嘗評曹公之作:“他寫喝酒的場面是不少的,唯對酒的名色、特點、有關情況,一字不談,這一點特別令人詫異。”詫異歸詫異,可以肯定的是,《紅樓夢》的世界沒有啤酒,所用之酒多為黃白二類:白酒即燒酒,亦為高粱酒;黃酒則說的是米酒。
“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曹公,在書中追憶的是“無酒不成席”的往昔榮華歲月,雖也寫王狗兒因家中冬事未辦而喝悶酒、閒尋氣惱;寶玉獨自喝酒、眼餳耳熱之餘續寫《莊子·胠篋》;或雨村在揚州,從智通寺出來,村肆中偶遇冷子興,對飲並“演說榮國府”;又有鳳姐擺酒為賈璉接風洗塵的對飲,但更多的是集體群飲的盛況,被精心安排、集中描述的飲酒情節不下二三十次;可以說,在榮國府——確切地說,在大觀園之外的與酒相關的場面,通常都不那麼文雅,甚至很不堪。
第二十八回馮紫英在家中宴請寶玉、薛蟠、蔣玉菡等,“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讓妓女雲兒唱曲;寶玉遂說“如此濫飲,易醉且無味”,遂發一新令,以“悲愁喜樂”四字填詞唱曲,同是《女兒悲》,馮紫英的唱曲反映市井平民的情趣,雲兒道出妓女們的喜怒哀樂,寶玉的《紅豆曲》抒發深摯的相思,而這場酒戲,卻更是薛蟠的“主場”,他的搞笑、黃段子和“哼哼韻”,形象塑造了淺薄無知、鄙俗下流的“薛大傻子”。
還是這位“活寶”,第四十七回,在賴大家花園,酒後想和年輕貌美的柳湘蓮調情,亂叫亂嚷“誰放了小柳兒走了!”——如畫。氣得柳湘蓮故意慫恿他,喜得呆兄“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已八九分了”,後柳湘蓮引他騎馬直出北門,找個“人跡已稀”的葦塘痛揍他——這一鬧劇的直接結果是呆兄為避人耳目到江南學做買賣;不過,曹公之意不在酒,而在於請香菱入園學詩——風雅之事,才最要緊。
薛蟠從江南迴來自然也是死性不改,只有等到喜歡以油炸雞鴨焦骨下酒的夏金桂來“降服”他——第七十五回,八月十三,他與賈珍、邢夫人的弟弟邢德全等一干人在寧府飲酒賭錢,孌童奉酒,眾人醜態百出。
不似“傻大舅”邢德全的“沒心腸,喝了兩碗,便有些醉意”,第七回焦大著名的醉罵:“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酒後吐真言,焦大雖醉,罵的卻句句是醒語。同樣“尚義俠”的醉金剛倪二,也是在醉酒後二話不說借給賈芸十五兩三錢有零,幫他渡過難關。
同樣是酒後談錢,“傻大舅”酒後醉罵姐姐邢夫人“若提‘錢勢’二字,連骨肉都不認了”“就為錢這件混賬東西”,也從另一側面透露出邢家與賈府每況愈下、經濟拮据的崩潰趨勢。就在同一章,第二天,八月十四,賈珍攜妻妾家人在寧國府會芳園叢綠堂飲酒賞月作樂,到了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嘆之聲”,復又聽祠堂槅扇開闔,“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悚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前明朗。眾婦女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醒了一半”,寧國府的“異兆發悲音”極具恐怖片效果,正在渲染豪門貴族“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悲慘結局,此時再讀秦可卿房中對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竟似恍然一夢。
滿紙酒飄香
不似只有門口石獅子乾淨的寧國府,酒在榮國府的出場,通常伴隨著賞月、賞花、賞雪、賞戲、年節、祝壽、慶生,場面繁盛熱鬧,不愧為花柳繁華地與富貴溫柔鄉,讀來“滿紙酒飄香”。
盛大筵宴必有佳釀。第十七至十八回元妃省親,黛玉應制詩中有句“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金谷在今洛陽西北,有水流經,謂之金谷水;晉石崇有金谷園,李白亦有《春夜宴桃李園序》:“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後人借金谷園斗酒典故,以金谷澗水釀酒而得名,並非指酒,黛玉詩就是指大觀園開筵賦詩。
第五十三回“榮國府元宵開夜宴”,提及賈府過年習俗,祭祀祖先用“屠蘇酒”。此酒相傳為華佗所創,內有肉桂、大黃、陳皮、白朮、赤小豆、桔梗等多味中藥材,有強身健體的功效。南朝梁宗懍的《荊楚歲時記》載:“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屠蘇酒……”相傳飲屠蘇酒能辟邪氣、保健康。北宋王安石《元日》中“春風送暖入屠蘇”膾炙人口,南宋陸游《除夜雪》中亦寫“半盞屠蘇猶未舉,燈前小草寫桃符”,可見飲屠蘇酒的風俗早已有之,至清代更相沿成習:《紅樓夢》曾細緻描寫榮國府大花廳設合歡宴,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果、如意糕,一夜人聲嘈雜,語笑喧闐。
也就在此處,寶玉依次為大家斟酒,“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杯來,放在寶玉唇上邊,寶玉一氣飲幹。黛玉笑說:‘多謝。’”寶黛歷經多次誤會、爭執、“識分定”“愈斟情”,到此時看似已經“塵埃落定”,可以公然文雅地“撒狗糧”,可惜此時距賈家頹敗已經愈加迫近了。
入大觀園之前的賈寶玉,放在當代也應該是個朋克養生的放浪少年——對於酒,“我只愛吃冷的”,第八回在“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薛家初入京時居住的梨香院裡,他這樣發出豪言,但旋即被博學多識的薛寶釵柔情“訓導”了養生之法:“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遂命人暖來方飲,於是黛玉沒吃多少酒,也要“含酸”了。
自此之後,《紅樓夢》中的每次宴飲都要熱酒,第五十回寶玉與眾姐妹爭聯即景詩,“怡紅公子”不出意外地落第,李紈罰他去櫳翠庵乞紅梅,臨行前湘雲熱起壺酒,黛玉遞杯,寶玉吃了遂冒雪而去,呼應梨香院“喝熱酒”之舊事。榮國府花廳合歡宴上,寶黛的親暱舉動曾引起王熙鳳笑說“別喝冷酒”,寶玉說“沒有吃冷酒”,鳳姐又笑:“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一句“白囑咐”,滿含無限深意,又可見世家大族飲酒有道,並非一味貪杯。
有文雅地飲酒,自然就有把飲酒飲成“狂歡”事件的——在曹公寫來,這些醜態畢露的“狂歡”更具美學意義。認定男兒濁臭逼人的寶玉,根本不會想到自己“綠蠟春猶卷,紅妝夜未眠”“如同小姐繡房”般的怡紅院會劫遇母蝗蟲:賈母在秋爽齋宴請劉姥姥,後又到綴錦閣行酒令,姥姥自覺“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遂兩手捧著黃楊根整摳的大杯一氣喝完,又吃茄鯗等油膩食物,加之喝了幾碗茶,便在大觀園東北角“通瀉起來”,撞進怡紅院,最終“扎手舞腳的仰臥在床上”“鼾齁如雷”,襲人來時,“只聞見酒屁臭氣”。
劉姥姥醉酒,自有“醜陋美”的狂歡氣息,而鳳姐酒後撒潑,更具市俗熱鬧的喜感,這場戲也是從大花廳“開演”的:第四十四回鳳姐生日,祝壽酒宴上,尤氏、眾姐妹、嬤嬤、丫鬟們,一如尤氏戲語“趁著盡力灌喪兩鍾”,直把鳳姐灌醉,“心裡突突的似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於是發現同樣酒後的賈璉和鮑二家的私通,鳳姐酒醉潑醋,屈打平兒,又與鮑二家的瘋狂廝打,賈璉這個“海王”也倚酒三分醉,大逞威風踢罵鳳姐,男男女女一團混戰,因醉酒,演出潑醋的大鬧劇。
“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第六十五回,珍璉二兄弟於國孝家孝之際,在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新房子”調戲尤氏姐妹,被尤三姐醉後怒斥:“喝酒怕什麼,咱們就喝”,自綽壺斟了一杯,自喝半杯,摟過賈璉的脖子就灌:“我和你哥哥已經吃過了,咱們來親香親香”,唬得賈璉酒都醒了。尤三姐不愧是酒中豪傑——“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灑落一陣,拿他兄弟二人嘲笑取樂,竟然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對比兩回後的“聞秘事鳳姐訊家童”,同樣潑辣,卻各具不同的雷霆之勢——好想看王熙鳳和尤三姐的“巔峰對決”,可曹雪芹是定不會寫的:那勢必會奪走黛玉葬花或寶釵撲蝶的登峰造極的紅樓情韻,而且那更像“三言二拍”甚至《水滸傳》裡的故事了。
名士與光棍
曹雪芹少年時代在江寧度過,寫紹興黃酒本就無可厚非。多鐸五世孫裕瑞曾從舅父明義、明琳那裡聽說雪芹戲語:“若有人慾快睹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即為之作書”——有紹興酒和燒鴨又怎麼樣,還不是“紅樓夢未完”,空留文學史上一個巨坑未填。
雖然賈寶玉平時也喝西洋酒——廚師柳嫂就把“胭脂一般的汁子”的玫瑰露錯認為寶玉常喝的紅葡萄酒,但賈府上下飲用最多的卻是曹公最愛的黃酒。“鳳姐潑醋”翌日,賈璉認錯謝罪,賈母啐他:“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屍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黃湯自然非白酒亦非啤酒,只能是以大米及黍米為原料的“液體蛋糕”——黃酒了。《呂氏春秋》載,春秋時期紹興地區已經產酒;到南北朝後更有“越酒行天下”的說法,18世紀《紅樓夢》成書的年代,紹興黃酒更是遠銷各地,成為上流社會互相饋贈和貴族之家宴飲之佳品。清代文人袁枚在《隨園食單》中言:“餘常稱紹興酒為名士,燒酒為光棍”,又言“紹興酒如清官廉吏,不摻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長留人間,閱盡世故而其質愈厚”——賈府這樣的“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自然要親“名士”而遠“光棍”,多用“味甘、色清、氣香、力醇”的紹興黃酒。
第二十六回薛蟠、寶玉、馮紫英等人宴飲,“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馮紫英站著,一氣而盡”——若非度數低的黃酒,則這位神武將軍公子必不能“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一翅膀”而掛彩,非得三碗不過岡打只老虎才能了結了。第六十三回為寶二爺慶生助興,襲人亦明言:“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也只有紹興黃酒溫婉的口感,才適合大觀園特別是怡紅院“女兒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的香軟氛圍,若在“黃酒價貴買論升,白酒價賤買論鬥”的當時,紅樓眾女兒開懷暢飲老白乾或者“小二”,那畫風也太過清奇。
賈府所飲並非只有黃酒,大觀園中,最令人矚目的恐怕是第三十八回的“合歡花浸的酒”:在藕香榭的螃蟹宴上,黛玉只吃了一點便覺心口微微地痛,自斟了半盞酒,見是黃酒不肯飲,說“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便命丫鬟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詩人氣質的瀟湘妃子與花香濃郁的合歡花酒,組合成大觀園中頗為風雅的意象,同時也證明林黛玉並非一味弱不禁風、多愁善感,她更是好酒的豪爽女子:怡紅夜宴,丫鬟小燕最先想到“把寶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會子”,寶玉亦道“咱們三姑娘也吃酒”,一個“也”字,說明最善吃酒、能玩鬧的是釵黛二人;加上此番紅樓中獨飲燒酒,林黛玉算是真正的酒客了。
合歡花是合歡樹上所開小白花,所浸泡之久不僅能祛除寒氣,且有安神解鬱之功效;以合歡花入酒古已有之,清康熙年間,以合歡花葉釀酒亦成士大夫階層的雅事,曾與雪芹祖父曹寅唱酬交遊的高士奇所作《北墅抱甕錄》載:“合歡葉細如槐,比對而生,至暮則兩兩相合,曉則復開。淡紅色,形類簇絲,秋後結莢,北人呼為馬纓……採其葉,幹之釀以酒,醇釅益人。”而燒酒,明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谷四·燒酒》中記載:“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麯釀甕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以林黛玉的體質,平時飲用黃酒最為適宜,但此時螃蟹宴在背山臨水的藕香榭舉行,吃口熱熱的燒酒才正好緩解寒氣和心痛之症。而曹公在此處寫此酒,並非僅向讀者展示他的養生知識,而是自己對前塵往事的追憶——庚辰、己卯本此處有批:“傷哉!作者猶記矮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更以此酒透露重要寫作年代資訊。
如果說紅樓中奪目之“酒”是合歡花佳釀,那麼最著名的飲宴場景非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莫屬。宋淇在《紅樓夢識要》中認為,此回是全書製造歡樂氣氛的頂峰,之後劇情急轉直下,不如意事接二連三而來——大觀園最後的輝煌頂點,安排在怡紅院為怡紅公子慶生的一場酒宴之上。
此場繁華所用之酒,早在上一回已由襲人言明是紹興酒,但好酒的芳官更“饞”家鄉的惠泉酒:“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著我,我要盡力吃夠才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這產於江蘇無錫惠山的“惠泉酒”,也稱“三白”,以清澈純淨、唐人陸羽評為“天下第二泉”的惠泉之水釀製而成,酒質甘潤醇美。從元代開始,用“二泉水”釀造的糯米酒,稱為“惠泉酒”,明代此酒已聞名天下,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曾記錄過“惠山泉酒”一詞,李東陽在《秋夜與盧師邵侍御輩飲惠泉酒次聯句韻二首》中寫:“惠泉春酒送如泉,都下如今已盛傳”。清初惠泉酒更成為貢品,這在書中亦有暗指:第十六回王熙鳳為自蘇揚回京的賈璉接風,邀賈璉之乳母趙嬤嬤一起吃飯時就說:“媽媽,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席間更由元春加封賢德妃即將省親,而引出當年太祖皇帝南巡往事,賈府能飲此酒,也預示“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由此展開。
芳官在怡紅院雖沒喝上惠泉酒,卻也邊喝酒邊唱了《賞花時》:怡紅眾人與釵黛探紈湘菱等在炕上圍坐,行了全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酒令——佔花名。紅樓世界中多有對行酒令這個勸酒行為的文明化表達的描述——擲骰子、划拳、擊鼓傳花等,而最風雅的莫過於佔花名,它不但是大觀園最後的繁華景象,眾女子所佔花名也都對應了各自的情性與最終的結局:黛玉的花籤“風露清愁”,詩為“莫怨東風當自嗟”,來自歐陽修的《明妃曲·再和王介甫》,詩的前一句簡直令人心驚:紅顏勝人多薄命。
夜宴到四更時分,“老嬤嬤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罈已罄”的小細節,加速了盛宴的散場,“開到荼靡花事了”,自此夜宴的巔峰之後,大觀園諸芳最終流散,已是無可挽回的結局了。
泉香而酒洌
“壽怡紅”的夜宴之上,湘雲抽中海棠花,題為“香夢沉酣”,詩為蘇軾的“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說應改“石涼”二字,笑她在白天“醉臥芍藥裀”:寶玉、寶琴、平兒、岫煙四人同天生日,在大觀園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眾姐妹丫鬟射覆划拳飲酒取樂,“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一時獨不見了湘雲。眾人找到于山石僻處石凳子上業已香夢沉酣的她,“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穰穰的圍著她,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吃了酒才有詩”的枕霞舊友,睡中猶說席上自己提出來的高難度酒令:“泉香而酒洌(歐陽修《醉翁亭記》),玉盌盛來琥珀光(李白《客中行》),直飲到梅梢月上(骨牌名),醉扶歸(曲牌名),卻為宜會親友(曆書上的吉利話)。”
紅樓醉態種種,確實獨湘雲最美,“看湘雲醉臥青石,滿身花影,宛若百十名姝抱雲笙月鼓而簇擁太真者”,美的意境與美的夢囈,構成“湘雲醉臥”這個永恆的藝術形象;醉酒的表現,又活襯出她那“英豪闊大寬宏量”的個性特徵——就連她聚落花為裀,亦是典型的舊時名士作風。
“你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象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第七十六回“凹晶館聯詩悲寂寞”,也是“霽月光風”的湘雲這樣寬慰黛玉,山中笛聲助興,二人遂在捲棚底下近水賞月聯詩。促使她們最終作出“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的讖聯的,是“高雅生活鑑賞家”賈母攜眾人在山上賞桂花飲酒時“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的安排,於是“桂花陰裡,嗚嗚咽咽,嫋嫋娜娜,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涼”,“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賈母年老帶酒之人,聽此聲音,不免有觸於心,禁不住墮下淚來。眾人彼此都不禁有淒涼寂寞之意”,飲酒賞月的賞心樂事,卻因淒涼笛聲,溢位的是孤寂悲愴之情,照應的更是“運中數盡”的末世光景。
《紅樓夢》八十回,酒事以中秋夜酒終,亦是以中秋夜對飲開始的:第一回,中秋之夜甄士隱邀賈雨村至家,“真假”對坐,“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絃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甄士隱醉臥,直至紅日三竿方醒,開始了“絳死瑛僧,旨匿形外”的紅樓敘述。
從蘇揚到京城,從貴族府邸到失落樂園,以“天祿”為名之酒,勾連了眾多細節與故事;而對金陵十二釵乃至普天下眾女兒的命運作出綱領性暗示評點的酒宴,不在凡塵之中,卻在太虛幻境之上:小丫鬟擺設酒饌,“瓊漿清泛琉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洌,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麯釀成,因名為‘萬豔同杯’。”
“萬豔同杯”即“萬豔同悲”,它是作者虛構的酒品,亦是女兒所代表的美好逐一毀滅的殘酷現實。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在臺灣大學教授歐麗娟看來,警幻用來招待寶玉的茶“千紅一窟”、酒“萬豔同杯”、香“群芳髓”,以視、味、嗅覺全方位感官之美把少女象喻化,展示所有美好女子都會面臨“哭泣、悲哀、破碎”的命運。
寶玉在《四時即事詩》中寫下“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而最終盛景難再;通觀紅樓,一如王夫之所言:“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繡帳,寓意則靈。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檻。”在“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的眾多酒事,“沉酣之夢終須醒”,邁過門檻、逃出塵網,才得以“紅樓一夢,萬境歸空”。
張亞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