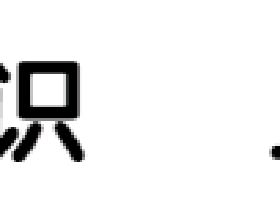蔡元培【安斯坦博士來華之準備】,《北京大學日刊》 1922年11月14日
《相對論淺釋》,夏元瑮譯
愛因斯坦等在上海梓園合影
1917年
知識界一場誤打誤撞,“相對論”初現中國
1917年這一年,於中國乃至世界歷史而言,都是相當特殊的一年。這一年新年伊始,陳獨秀應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新青年》編輯部隨之移至北京,有了《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的北大,也迅即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前沿陣地。
這一年開年新刊,元旦之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5號中,陳獨秀以“記者”名義同時轉載了兩篇演說詞《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和《蔡孑民先生之歐戰觀》。前一篇演說詞,乃是蔡元培剛剛抵達北京,準備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之前的一次重要講演記錄,集中體現了其治學治校的基本宗旨,自然備受社會各界矚目。除了在北京有《新青年》首發演說詞之外,3月15日,又被上海《東方雜誌》轉載,一時間傳遍京滬,南北皆知。
然而,就在《新青年》首發演說詞一個多月之後,百忙之餘的蔡元培抽空翻檢雜誌,卻發現演講詞中有一些記錄錯誤之處。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讀與誤解,遂於2月19日致信《新青年》編輯部,明確指出了這些錯誤,並逐一表述了修訂意見。十餘天之後,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迅即刊發此信,算是對之前刊發的演講詞做了及時更正與宣告。
蔡氏信中首先糾正了關於“宇宙觀”的一段演說詞,併為之特意指出,當天在講演中應當是這樣說的:
“在科學發達以後,一切知識道德問題,皆得由科學證明,與宗教無涉。惟科學所不能解答之問題,如宙之無涯涘,宇之無終始,宇宙最小之分子果為何物,宇宙之全體果為何狀等。是舉此等問題而研究之者,為哲學。”
不過,那未經修訂的演說詞,畢竟已經公開發布兩個月之久,其傳播之廣泛,可以想見。包括講演者本人蔡元培、《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在內,恐怕誰也不曾料到,正是因為演說詞記錄稿中的一些錯誤,竟然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愛因斯坦學說的爭論與國內流行之熱潮。
原來,時為1917年4月,由中國留日學生建立的“丙辰學社”(後改名為“中華學藝社”)的社刊——《學藝》雜誌,在日本東京創刊發行。這一雜誌的創刊號中,赫然刊有一篇題為《批判蔡孑民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並發表吾對於孔教問題之意見》的文章,作者為一位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名叫許崇清。
為此,蔡元培即刻致信許氏,告知演說詞記錄有誤,“而累足下為此不經濟之批判,甚可惜也”,而發表了其糾正之語的《新青年》第3卷第1號,“想足下尚未之見”,“今奉油印本一通,鄙人本意可見大概”。
孰料,收到了蔡氏致信,又讀到了演說詞修訂稿的許氏,並未就此罷休,迅即又於《學藝》雜誌第2期上,撰發了《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會演說之訂正文並質問蔡先生》一文,依舊不認同蔡氏的觀點與思想立場。許氏反對與質疑的蔡氏觀點,竟然也包括了前述那一段蔡氏致信陳獨秀,特意加以糾正了的關於“宇宙觀”的一段演說詞;並明確拈提出了當時科學界前沿最新研究成果之下的“宇宙觀”,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學說。文中稱:
“方今自然科學界,關於時空(即宇與宙)之研究,則有Einstein於1905年發表之‘相對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為前提,其一則為‘相對性之假定’,其二則為‘光速不變之假定’。艾氏據此以時間相對性之定義,而牛頓力學所懸設之絕對空間絕對時間幾至不能成立。”
雖然在與蔡元培論爭的這篇文章中,許崇清只是拈提了一些狹義相對論的基本假設和概念術語,來加以哲學層面上的闡發與表述,還並沒有從科學理論角度加以專業解析,但這些隻言片語,卻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關於“狹義相對論”的中文介紹。
1919年
北大理科學長曾是愛因斯坦家中常客
話說時年50歲,長許崇清20歲的,剛剛履新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這一場年齡、地位、閱歷都頗為懸殊的,隔海通訊式的論爭中,並沒有為之大感惱火與鬱悶,反倒因為得悉愛因斯坦學說而深感快慰,併為這一新奇學說的獨特魅力所吸引。隨後,即有意邀請愛因斯坦來北大講學,開始多方聯絡籌劃,為之緊鑼密鼓地安排佈置。
當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傾力發動並全力推進“新文化運動”之際,早在蔡元培掌校之前五年,即已出任北大理科學長的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也隨之同步走向了時代前沿——為引介與傳佈科學新知,尤其是在普及愛因斯坦學說及邀訪通聯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個人貢獻。
就在“五四運動”這一年,即1919年夏,夏氏出訪德國並以訪問學者身份入柏林大學從事學術活動。也正是在此時,夏氏透過其師,著名物理學家、量子力學重要創始人馬克斯·普朗克,結識了愛因斯坦並常到其家中研討各種問題,與其家人也逐漸熟絡起來。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人際關係基礎,夏氏還促成了向以傳佈新知、再造新民為己任的著名學者梁啟超,與愛因斯坦的一次面晤。
據夏氏後來憶述,就在其成為愛因斯坦家中常客“幾個月後,梁任公先生到柏林”,夏氏即“請他同愛因斯坦夫婦晚餐”,“席間梁先生問相對論的真義,愛因斯坦詳為解釋”。當時,夏氏“擔任雙方翻譯”,因“談話久,而進食的時間少”,“還引起愛氏夫人的不滿”。不過,愛因斯坦對梁氏印象不錯,曾稱“梁先生真聰明,略有解說即能明白”。
1921年歸國之後,出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夏氏,又開始頻繁在北大校內外撰發文章,力圖以較為通俗簡明的講解方式,向國內知識界普及愛因斯坦生平及其學說。愛因斯坦於1916年所撰名作《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淺說》,夏氏迅即著手譯成《相對論淺釋》書稿,於1922年4月交由商務印書館初版,對於那個年代對這一新奇學說想要有所瞭解的中國讀者,不啻於一部案頭必備的入門“寶典”。
當然,並不是所有熱心於引薦、介紹愛因斯坦學說的中國學者,都具備如夏氏那樣的專業背景與知識修養,更不必說“親炙”面晤愛因斯坦的機緣,亦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所有這些客觀條件的限制,並不妨礙同時代大量非專業領域內的中國學者,甚至是非理科專業背景的中國學者,去接觸與親近愛因斯坦及其學說。
1920—1922年
“後浪”才俊齊上陣,“跨界”推介愛因斯坦
譬如,後來成為著名音樂家、教育家的王光祈(1892—1936,筆名若愚),1920年赴德國留學時,就以兼任上海《申報》《時事新報》與北京《晨報》駐德特約記者的身份,向國內讀者多次引介愛因斯坦及其學說。
早在1920年11月5日,《時事新報》就刊發了由王光祈所撰,題為《德國科學界的大論戰》的“駐德特約通訊員”專稿。當時,愛因斯坦的中文譯名尚未統一,僅據音譯還稱之為“安斯坦”,稍後又有“恩斯坦”“愛恩斯坦”之謂。王光祈在此文中激贊稱,“安斯坦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現在的奈端(牛頓),是科學中一個大革命家。”1921年3月2日,《時事新報》又刊發了由王氏所撰“德國特約通訊”專稿,文中首次披露了“發明相對論的安斯坦將遊中美兩國”的獨家訊息,並捎帶透露了其友人魏時珍正著手翻譯“通俗相對論”的訊息。
1922年2月1日,由李大釗、王光祈發起主辦的《少年中國》雜誌第3卷第7期,以魏氏所譯《相對論》與王氏所撰《我所知道的安斯坦》為主體內容,將這一期雜誌特別命名為“相對論號”,向國內讀者隆重推出。
然而,可不要以為這一期《少年中國》雜誌,即是中國第一本“相對論號”雜誌了。因為早在約十個月之前,於1921年4月15日,由梁啟超主編的《改造》第3卷第8號,就已然被命名為“相對論號”,這才是國內首創之舉。
這一期“相對論號”的封面頭條文章,是詩人徐志摩所撰長達15個頁面的“雄文”,實在是令略微瞭解徐氏生涯的當世或後世讀者,都驚訝莫名的罷——“相對論”的風靡一時,可見一斑。
略微翻檢一遍,可知徐志摩解說的“相對論”,乃是逾越了文理科界限的,帶著濃厚人生觀與價值觀意味的泛哲學理論。這一個性化解說,有著全然“跨界”不顧,深入淺出且又諧趣橫生的通俗啟蒙之效。開篇這樣寫道:
“字是一個個都認得的,比喻也覺得很淺顯的,不過看過之後,似乎同沒有看差不多。我可也並不著急,因為一則我自己科學的根柢本來極淺,二則安斯坦之說素,原不是容易瞭解之東西……我也不再請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幾本書幾篇雜誌文字。結果可不能說完全失敗,雖然因為缺乏高深數學的緣故,不能瞭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過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麼一回事。”
接下來的十餘個頁面,主要就是去講述他透過自己感悟理解的,終於知道了的“那是甚麼一回事”了。徐氏雖不知其“所以然”,卻終於“知其然”的結論,大致是這樣的:
“‘相對說’根本沒有玄想的意味,因為他完全脫離人生的感情意氣經驗種種,是純粹唯物的性質。尋常哲學多少總脫不了以人心解釋自然,‘相對說’是澈底澈面拋開人間世的理論。我們人類一部智識史是發源於以宇宙中心一直到放棄個人觀念,這‘相對說’可算最後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後勝利,其範圍之廣為從前所未曾夢見。”
徐氏文中還有提及,約於1920年秋,著名學者任鴻雋、饒毓泰,以及正在訪華的英國著名學者羅素,均已在南京的學術講演中,主題論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的相對說”,可知當時不僅有以蔡元培為首的北大學術群體,南京及滬上的各路學界精英,也都對愛因斯坦學說投以熱切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於1931年11月因飛機失事不幸身亡之後,各界痛悼詩人遇難之際,林徽因所撰《悼志摩》一文裡,又再次言及徐氏對“相對論”學說的熱衷與自得,文中這樣寫道:
“志摩的興趣是極廣泛的。他曾經譯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寫過一篇關於相對論的東西登在《民鐸》雜誌上。他常向思成說笑:‘任公先生相對論的知識還是從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來的呢,因為他說他看過許多關於愛因斯坦的哲學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1922年
愛因斯坦“快閃”上海,“失約”北大
與一浪高過一浪的國內“相對論”流行熱潮同步,1921年初,赴歐洲考察的蔡元培,遍訪西方學界名流,在法國巴黎訪晤伯希和、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學者之後,又於3月16日,與夏元瑮等在德國柏林面晤愛因斯坦。當蔡氏表達了邀請其訪華講學時,“答甚願,但須稍遲”;甚至還談到了在華講學應用何種語言的問題,蔡氏“告以可用德語,由他人翻譯,夏君(元瑮)即能譯者之一”。
此次面晤愛因斯坦的情形,被簡要記錄在了蔡元培本人的日記中。
答以“甚願,但須稍遲”訪華的愛因斯坦,果然於一年多之後,於1922年11月13日,抵達中國上海。然而,此行並非專程訪華,而是赴日本講學,次日即啟程離去,經停上海只此一天罷了。
雖則如此,上海各大媒體的報道,還是連篇累牘而來,各路訊息,還是接踵而至了。報端各種行程預報及行蹤簡報,確切的與不那麼確切的資訊都有,可靠的與不那麼可靠的訊息都有。不過,愛因斯坦離滬次日(11月14日),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同時刊發的相關報道,雖一簡一詳,但二者內容基本可以相互映證,應當可以採信。
內容較為詳盡的《民國日報》報道全文700餘字,乃是目前已知的,關於愛因斯坦初次抵滬報道中篇幅最大者。這一天的行程,其安排之周密,佈置之緊湊,人員之繁雜,環節之多樣,報道中都已經基本予以呈現。尤為難得的是,當天的晚宴之後,在作為中方東道主的著名書畫家、實業家王一亭的私人宅第“梓園”之中,還留下了一幀全體出席者的珍貴合影。這一合影照片,至今仍珍藏在一所國際研究機構——李奧貝克研究所(LeoBaeckInstitute)之中。
就在上海報道同日,只有四個版面的《北京大學日刊》,當天也用了一個半版面的可觀篇幅,刊發蔡元培所撰《安斯坦博士來華之準備》一文,正式公佈了校方邀請愛因斯坦來華講學的往來函電內容,並宣稱“今安斯坦氏已由香港赴日本,不久可來北京,故特布其顛末”。
然而,因種種原因,那一場蔡元培等諸多前賢后進籌劃已久,令北大內外滿懷期待的學術盛會,終究未能如約舉辦。1922年12月31日,赴日講學已畢的愛因斯坦,雖再度乘船經停上海,卻只是在滬上度過了1923年元旦之後,於次日即刻登船返回歐洲,從此再未步入中國。
1937年
愛因斯坦聯名致電蔣介石,請求釋放鄒韜奮等人
遺憾歸於遺憾,因緣歸於因緣。愛因斯坦的中國因緣,卻還並未因為1922年的這一場“失約”戛然而止。即便只是在上海經停的短暫時光裡,愛因斯坦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也可謂入木三分。其婿所撰《愛因斯坦傳》,據其當時的旅行日記,對其短暫經停上海的中國印象予以了這樣的表述:
“上海的訪問,使他對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種看法。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指1919年的五四運動)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僕。……他們是淳樸的勞動者,歐洲人所以欣賞他們的也正是這一點,在歐洲人眼裡,他們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離開上海不到五年之後,時至1927年2月間,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愛因斯坦迅即致信會議主辦方,明確表示支援大會主旨,堅決反對歐美列強掌握世界大權的國際格局,號召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團結,反抗不合理的國際霸權。
之後不久,又值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公然踐踏國際約法,攫奪我國東北三省主權。日軍還接連製造“一二八”事變,將戰火轉移至遠東大都會——上海,更令當時在上海居住的各國人士,對日軍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曾經在上海有過短暫經停,更在此轉赴日本有過專程講學之旅的愛因斯坦,對此深感震驚憂憤,在一次廣播演說中,拍案而起,奮起呼籲,“主張對日經濟絕交以促日本停止對華之侵略”。
及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終於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又接連製造“八一三”事變,戰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愛因斯坦與曾訪華講學的著名學者杜威、哲學家羅素等聯合發表宣言,“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壞,為維持和平道德,特倡議各國人民,組織對日貨之自動抵制,不售戰爭材料,凡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項,當停止合作……今當以種種之可能的援助,給予中國,而使日本撤退在華所有之軍隊,放棄其對華侵略政策”。
在個人積極聲援中國抗戰期間,1937年初,愛因斯坦還與杜威、孟祿等15名美國學者,聯合致電蔣介石與孔祥熙,請求釋放被抓捕入獄的鄒韜奮、章乃器等“救國會七君子”。電文中稱,“中國處境困難,至表同情。我們以中國的朋友的資格,同情中國聯合及言論結社自由。對於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位學者被捕訊息傳到美國,聞者至感不安……”
抗戰勝利後,1947年12月16日,曾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顧問的中國學者羅忠恕,應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階研究所之邀,於當日上午與愛因斯坦面晤。此次晤談,距“安斯坦”之名閃現中國,恰恰整整三十年過去。
時值二戰硝煙散盡不久,二人的談話,自然而然的涉及到了科學應為人類造福,科技應用中的善與惡等學術宏觀主題。羅氏後來在《與愛因斯坦先生的談話》一文中憶述稱,談話的氣氛友好而親切,不知不覺間竟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臨別時,二人還合影留念。約八年之後,1955年4月18日午夜,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寓所中,於睡夢中猝然離世。至此,約八年之前,羅氏與愛因斯坦的那一次意味深長的晤談,以及那一幀彌足珍貴的合影,也就此成為愛因斯坦與中國學界所有過往交集的最後“定格”。
供圖/肖伊緋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