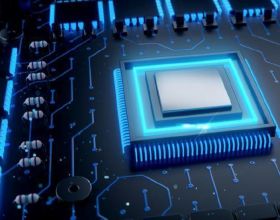◎遠村
2006年的一天,晚間閒聊,有個來自鄭州鞏義市的大學同窗曾自豪地說,他的老家是詩聖杜甫的故里。一個雙休日,我們幾個校友就坐了西去的客車,疾馳百餘里想去瞻仰一番詩聖的老家。
那天,是個初冬的上午,我們下車後,由鞏義的同學帶著,走了一段土路,就到了位於鞏義市站街鎮南瑤灣村的杜甫故里。在一處黃土坡上,一棵老樹下有頭黃牛正在反芻。四處逡巡,除了幾處農舍,只有一座青磚砌成的碑樓兀立著,碑樓裡的石碑,因受風剝雨蝕,倒是更顯滄桑。石碑上鐫刻著一行大字:唐工部杜甫故里。明證了此地乃詩聖故里的不虛。
再往上走,記得有4孔窯洞,最右邊的一孔,據說就是杜甫的誕生窯。當時,這幾孔磚券的窯洞均窯門大開,每孔約有20多平米。窯內一股黴味,空空如也。史傳,杜甫的曾祖曾為鞏縣令,祖父杜審言是著名的初唐詩人,父親杜閒也做過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按說杜家算是官宦人家,而名垂千古的詩聖生來呼吸的第一口空氣,竟來自於這裡的一孔窯洞,想想也很有些反差。
我們當時就有些遊興闌珊。而鞏義的同學卻說,這杜甫故里據老輩人說還很佔了些大好風水。往大處看,這裡嵩嶽、邙山對峙,黃河、伊洛河、泗河三河匯流,連《詩經》裡也響徹著它們的濤聲;往細處看呢,這裡的幾孔窯洞,背靠的山體也大有意味。
“這窯洞後的山叫作筆架山。像不像?”經這位同學一點化,我們就往窯洞上方望,但見一座長著矮樹荒草的土山,橫亙著向兩邊排開,中間是兩道豁口,遠望能依稀看到更遠處的山巒。大家就覺得,這山真有些形似筆架,也只有杜甫這樣的詩聖,才配得上把他的如椽大筆放在這以天地為書房的“筆架”上吧!
雖說那天我們實地探訪了杜甫故里,還是因其太過寒酸寂寥,有些乘興而往,掃興而歸的況味。
然而,時隔一年,那位鞏義同學就眉飛色舞地告訴我,鞏義市政府竟一下子投入1.5億元,要按照國家AAAA級景區的標準,大力打造杜甫故里了。我揣摩著此舉不外乎“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也就哂然一笑,沒再多言了。
可是,今年國慶假期,老同學聚會,我還是去杜甫故里重遊了一次。此時的杜甫故里,佔地達200多畝,整個園區遍佈紅白相間的唐代建築,要收每人50元門票,已是今非昔比了。
進入園區大門,標直的詩聖大道遊人如織,大道深處,巍然矗立一尊高達9米的銅像,但見詩聖左手握卷,右手扶山,二目遠望,神采煥發。聽導遊說,這塑像再現的是詩人24歲時登上泰山的神態。我也隨之想起了杜甫的《望嶽》中“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名句來。觀此塑像,詩人當年望嶽後應是登上岱宗“凌絕頂”了。
而實際上,儘管杜甫日後仕途多舛,命運坎坷,以致“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到了靠友人接濟過活的境地,但他還是依然登上了一座座無形的山峰,仰觀四極,細視八荒,胸懷社稷蒼生的憂患安危,悲天憫人的情愫,憤世嫉俗的氣概,將那一如黃河激流般的詩情,汩汩地流瀉於筆端。最終,他也在無意中站在了煌煌唐詩的巔峰之上。
隨了導遊,我們來到了詩聖堂,瞻仰了老年杜甫的漢白玉坐像,又重溫了詩聖的十多首代表作。這裡,既有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圖大志,“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國破之痛,又有詩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悲情憂思,“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頓足控訴;這裡,也有詩人“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羈旅之思,還有“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的春夜喜悅,“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短暫歡愉……
真性情的詩聖,字曰“子美”,在他的詩句裡,卻蘊含著大美!
而觀看著景區的旋轉投影紗幕,隨著那渾厚的配音朗誦,詩聖《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名篇中的畫面也次第呈現:“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耳聞目睹著詩聖代表作中的精華之餘,我就想,為什麼杜甫被後人尊稱為“詩聖”呢?是不是他的詩作,內中體現的是一個“大我”呢?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談到杜甫,人們總會想到和他同時代的大詩人李白。有人認為,杜詩整體風格為“沉鬱頓挫”,李詩大致風格為“狂放飄逸”,由此,就把詩聖歸為現實主義詩人,把詩仙劃為浪漫主義詩人。
然而,我再來觀瞻杜甫故里後,倒是覺得,詩聖骨子裡是位更富浪漫主義情懷的熱血男兒。你只從他客居破茅屋,在狂亂的秋風中追逐飄舞的茅草時發出的大祈願便可判定,他即使十分寒酸潦倒,還是能想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辟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而若是到了此種理想境界,他便“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了。
這是何等灑脫浪漫的獻身精神,有此思想境界的詩人,他不是詩聖又有誰是的呢!
凝望著詩聖的雕像,回顧我們新世紀以來在華夏大地上建起的無數高樓大廈,想到無數的家庭已得以安居,我就想,若是詩聖在天有靈,應會捻鬚微笑了吧。
有此一念,我在隨之遊覽杜甫故里的杜公祠、瞻雪閣、壯遊園、三友堂、懷鄉苑等景點時,想到富裕起來的國人而今越來越推崇傳統文化,敬仰“詩聖”等文化名人,也就快慰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