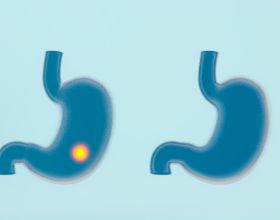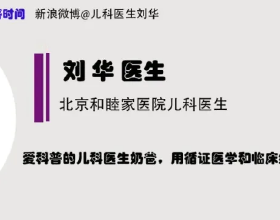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林芝怎麼都想不到,自己對“有孩子”這件事能有如此深重的執念。
今年42歲的林芝本科、碩士都就讀於名牌大學,畢業後進入北京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工作,是典型的“當代女性”。曾經,她也自認為想得開,“孩子嘛,有當然好;沒有,好像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很難說清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或許從林芝和丈夫決定備孕那一刻就開始了。“越要不上,越想要。”過去7年時間,求子而不得讓林芝和她身後的家庭身心俱疲。
有時她也會假裝釋然。今年“六一”兒童節前夕,三孩生育政策公佈時,林芝笑著說,如果能生出頭胎,我一定聽國家的話拼出三孩。
一旁的丈夫和父母都跟著笑了,但誰也沒說話。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在不採取避孕措施的情況下規律性生活嘗試懷孕,超過12個月未能實現妊娠,即為不孕不育。
不久前,生殖醫學專家、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喬傑院士在醫學雜誌《柳葉刀》上釋出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不孕不育發病率已上升至18%,這意味著每5.6對育齡夫婦中就有一對面臨生育困難。
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最佳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正式釋出,作出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的重大決策。
《決定》專門提到,要以規範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開展不孕不育診治服務。
1988年,中國大陸首例試管嬰兒出生,此後30多年間,試圖依靠醫療和技術手段實現生育的家庭越來越多。只是這個過程中,並非每個人最終都能得償所願。
明明很健康,怎麼就懷不上孩子
從催婚到催生,再到意識到女兒“生不了”,這些年,林芝的母親幾乎見廟就進、見佛就拜。她四處託人打聽哪裡有治療不孕不育症的“大師”或“神醫”,給女兒女婿求回各種調理身體的秘方。
苦得倒胃口的藥沒少喝,但林芝的肚皮就是一直沒動靜。
後來林芝自己也急了,拉著丈夫到醫院做了各種檢查,可結果顯示,兩人的“硬體”都沒什麼問題,完全具備自然受孕的條件。
“大人明明很健康,怎麼就生不出孩子?”像林芝夫婦一樣,許多患者在走進生殖醫學中心時,都抱著相同的疑惑。
隨著醫學進步,導致懷孕困難的諸多原因正逐步被揭曉。據統計,輸卵管問題、卵巢功能退化等是女方不孕的主要因素,而男方的癥結則大多在於精子質量不佳。
結婚後一直沒有懷孕,單晨30歲時從醫生口中得知自己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徵。“簡單來說,就是你的‘土壤’不好。”見單晨有點蒙,醫生打了個比喻來解釋,“宮腔環境類似於孕育種子的土壤,土壤足夠肥沃才能讓種子生根發芽。”
陶昕的丈夫被診斷患有弱精症,醫生告訴他們,男方前向運動的精子少於10%,基本上沒有自然受孕的可能。
除此以外,據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人類精子庫主任、中國性學會會長姜輝教授掌握的資料,在不孕不育的案例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夫婦依然查不出具體原因。“長期精神壓力大、飲食不健康、作息不規律、環境汙染等因素都可能造成人類生育能力下降。”姜輝說。
在諸多與生育困難可能相關的因素中,有一個為業界所普遍認同——人們不斷推遲的生育年齡。
2019年釋出的《中國生育報告》顯示,從1990年到2015年,我國育齡人口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主要初育年齡從20~27歲推遲到22~29歲。在一線城市,這個年齡段還要再往後推。
林芝碩士畢業時26歲,此後幾年她一心撲在工作上,升職、加薪、攢錢買房。32歲時她和戀愛半年的男朋友結了婚。跟身邊大多數同事、朋友相比,林芝的人生節奏並不算慢。
然而,她依然錯過了醫學界公認的適合人類生育的“黃金期”年齡。
研究表明,女性最佳生育年齡為25~28歲、男性最佳生育年齡為25~35歲。對女性來說,年齡增加,卵子的質量會變差,難以受精,就算形成了胚胎,出現流產的風險也會增加。對男性來說,儘管精液質量不會因年齡增加明顯下降,但也有學者認為,男性生育年齡與孩子出生缺陷或患精神疾病的風險程度呈正相關。
從事臨床工作20多年,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輔助生殖醫學科主任李文明顯感覺到前來就診的患者平均年齡在不斷增長,“現在女性患者平均年齡為三十四五歲,幾年前還在30歲左右。”李文表示,結婚晚、備孕晚,發現生育困難問題的時間自然也就晚了。
不顧雙方父母催促,林芝和丈夫在婚後維持了近3年的二人世界。她第一次諮詢試管嬰兒相關事宜時,正好是35歲。
公立排不上就去排私立
每天上午廖希都很忙。剛看完上一個病人的檢查報告,下一位患者就已經坐到了她面前的椅子上。再加上穿插其中的手術,有時候她甚至抽不出時間去趟衛生間。
廖希是北京一家專注於輔助生殖臨床治療的民營醫療機構的業務院長。雖然與公立醫院相比收費較貴,但仍有不少患者從外地趕來求診。
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每年誕生的試管嬰兒人數在30萬左右。隨著有包括試管嬰兒、宮腔內人工授精等輔助生殖醫療需求的患者人數不斷增長,國內相關醫療機構的數量也在連年攀升。
在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是一項限制性准入技術,對場地環境、裝置、科室設定等都有嚴格的要求。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國經批准的具備相關資質的醫療機構總共有536家。
和其他科室一樣,出於對更好醫療資源的追求,來自全國各地求子心切的夫妻讓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輔助生殖科門診總是人滿為患。
根據北京市衛健委2021年6月公佈的資料,北京市已批准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設定人類精子庫的機構共12家(不含軍隊醫療機構),目前約有4萬對夫婦有人類輔助生殖治療服務需求。此外,北京市還承擔著部分外地疑難重症患者的診療任務,一些輔助生殖機構接診的外地患者數量甚至達到了總數的60%~70%。
著名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位於院本部外一棟單獨的小樓裡。這裡是中國大陸第一例試管嬰兒的誕生地。
近三年來,該中心門診量近180萬人次,完成新鮮IVF(體外受精)週期55萬餘個。名聲在外,也讓這裡長年“一號難求”。
“公立排不上就去排私立,這家不成功就去試另一家。”這是很多選擇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夫婦都走過的一條路。
家住河北的單晨經人推薦到北京一家醫院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為了專心備孕,她辭掉了老家的會計工作,在醫院附近租了房子住下來。丈夫因為工作不能一直陪在她身邊,每一個治療週期的大部分時間,單晨都是自己度過的。
選擇透過試管嬰兒技術助孕的夫妻,需要經過制定方案、促排卵、取卵、準備精子、受精胚胎培養、胚胎移植、抽血驗孕等多個步驟。順利的話,整個治療過程大約需要兩個月時間。不過,如果受精卵培養失敗或是移植不成功,整個流程又要從頭再來。
“相比起來,以前掛號問診、吃藥調理都顯得再輕鬆不過了。”林芝數了數,光是準備階段,她就經歷了子宮評估、常規婦科檢查、宮腔探測、性激素檢測、卵巢功能檢測等一系列檢查,“這還沒算B超、心電圖、胸片等常規專案”。
更麻煩的還在後面。到了正式治療期,取卵前要打10天左右的促排卵針,移植胚胎前後要打很長一段時間的黃體酮針。而在每一個階段,林芝還要按醫囑口服不同的藥物。
人多資源少,每一次檢查、打針可能都要跑一次醫院。為了避免來回折騰,許多像單晨一樣的外地患者選擇就地住下。於是,面向準試管嬰兒媽媽們的短租房也成了醫院附近的一門生意。
26次移植,還是沒成功
第一次躺在受精胚胎移植的手術檯上時,大概是林芝既有人生中最虔誠的時刻。整個過程中,她一直在祈禱:一次成功,不要再遭罪。
那一回在林芝的強烈要求下,醫生給她植入了三個受精胚胎。她說希望能成活兩個,生一對雙胞胎。
接下來的日子是最煎熬的。
移植完成回到家,除了必須的活動,絕大部分時間林芝都臥床休息,連翻身也小心翼翼,唯恐那幾個胚胎不能著床、不肯認她當媽媽。
求子以來,林芝聽說了太多關於試管嬰兒的故事。有人說移植的胚胎不如自然受孕的胚胎穩固,準媽媽打個噴嚏都能流產。“那時候,科學、常識都拋在腦後了,反正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一般來說,受精胚胎移植7天后患者就能用早孕試紙測試是否懷孕。但林芝覺得,再晚幾天,測試的準確率會更高一些。
移植10天后,林芝完成了檢測。事後回想起來,她形容當時自己像手拿一張沒開封的鉅額中獎彩票,又像是握著一紙死亡判決通知書。
在安靜的衛生間裡,林芝狠狠閉著眼睛醞釀了許久,又猛地睜開眼。她看到的是一條紅槓。
沒有懷孕。
短暫的失落後,林芝心裡升起一絲僥倖,“萬一是寶寶調皮跟我躲貓貓呢?”又過了4天,她一早就去醫院抽血檢查。
化驗結果徹底澆滅了她的希望——移植失敗了。
單晨第一次移植的胚胎也沒能著床。看到化驗結果,她先是大哭了一場,接著開始反覆回想過去一週的細枝末節,“是我太緊張心跳過快,還是飲食不夠營養、休息不夠好導致了失敗?”
從1978年世界首例試管嬰兒在英國誕生,這一輔助生殖技術在臨床應用已有40多年。隨著技術進步,試管嬰兒成功率也在不斷上升,但這並不意味著每一次取卵、移植都能百分之百讓患者生出孩子。“制定的方案是否科學、移植時宮腔環境是否良好、醫生的操作手法是否得當等因素都會影響到成功率。”廖希解釋道。
在網路上流傳的一張“試管嬰兒養成”流程圖裡,從最初的身體檢查到孩子出生,準父母們要闖過的關卡多達15個。任何一關出了問題,都可能前功盡棄。
廖希曾經接診過一位患者,從40歲到48歲共做了26次移植手術,花費百萬餘元,最終沒能成功。廖希分析,患者治療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年齡過大,卵子質量難以達標。
在廖希所在的醫院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女性患者中,35歲以下一次性成功率約為60%,40歲以上成功率顯著偏低。
對於那位“高齡”病人,廖希曾建議採取供卵的方式懷孕生子,“但患者堅決反對,她希望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孩子”。
“傳好孕”和“接好孕”
從2017年起,廖希開始給自己的患者建微信群,“成功的人可以分享經驗和喜悅,路上的人也不孤單”。
4年下來,這樣的微信群已經有20個。除了諮詢問題和相互交換“攻略”,微信群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傳好孕”。
“本來想繼續做試管,結果自然懷上了,這些藥全都用不上啦,哪位美女需要,低價轉!”10月一個工作日的傍晚,一條好訊息讓其中一個本來安靜的微信群炸開了鍋。
“恭喜!幾周了?”
“恭喜姐妹!順便接好孕。”
“恭喜!接好孕。”
……
不到5分鐘,群裡“接好孕”的隊伍就排起了長龍。“傳好孕”的準媽媽小蕾此前備孕兩年沒有懷上,後來又做了兩次受精胚胎移植手術,均以失敗告終。
“親身經歷告訴各位,一定要忙起來,不想這個事,自然就懷上了。”開心的小蕾在群裡分享了自己的“懷孕玄學”,又得到了一波點贊。
儘管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已越來越普及,但對大多數就診夫妻來說,“生育困難”依然是他們難以向外人吐露的苦楚。這種情況下,“同病相憐”的人就成了彼此的慰藉。
在北京求醫期間,單晨也認識了很多病友,一些經驗豐富的姐妹會主動給她出主意讓她少走彎路。更重要的是,相互間的傾訴還是獨在異鄉的單晨釋放壓力的一種方式,“知道在這條路上不止我一個人,多少能好受一些”。
第一次移植失敗後,單晨接連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植手術,結果都不理想。第四次移植手術用到了屬於她和丈夫的最後兩個受精胚胎。如果再失敗,就要重新經歷一次促排、取卵的流程。
手術檯上,醫生為了讓單晨放鬆,跟她開起了玩笑:“這次無論結果如何,你都出去玩一圈放放風吧。”當時,單晨反而不像前幾回那麼忐忑了,她笑著回應:“對,我都想好要去哪兒浪了。”
以往移植手術結束,單晨都是小心翼翼地在醫院門口打車,但那一次,抱著 “破罐子破摔”的心態,她選擇走路回了出租屋。
人世間的劇情似乎總是這樣出乎預料。移植手術後第10天,單晨跳過試紙測試環節,直接到醫院抽血化驗。
醫院門診大廳永遠人聲鼎沸,然而當單晨取到化驗單那一刻,全世界都安靜了。
她反反覆覆看了幾遍,沒錯,自己懷孕了。
孕後第一次B超檢查是母親陪單晨去的。走出診室,單晨向等在外面的母親伸出兩根手指,“兩個!”
在河北老家工作的丈夫接到訊息後非常高興,電話還沒結束通話,單晨就聽到他激動地跟身邊的同事說:“我老婆懷了雙胞胎!”
從30歲到35歲,求子5年,兩年試管助孕,4次移植手術,“好孕”終於降臨到了單晨頭上。
當然,幸運無法眷顧所有人。經過一年多治療,受丈夫精子質量不佳影響,陶昕始終沒能受孕。後來,經全家人商量同意後,夫妻倆在醫院精子庫借精並經試管助孕有了一個兒子。年齡更大的林芝為了專心治療,辭去了高薪工作,卻依然沒有等來早孕試紙上的兩條紅線。
為了更優質的生育
最近幾年,廖希的患者中多了一個群體——來拼二胎的夫婦。隨著三孩生育政策的到來,又陸續有因年齡、身體等原因無法再自然受孕的夫妻前來向她諮詢試管助孕的相關事宜。
“有患者藉助試管嬰兒技術成功得子,幾年後又回來想如法炮製生二胎。”在廖希看來,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靠輔助技術生育正在逐步成為正常的社會現象。
2019年4月15日,同樣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我國大陸首例試管嬰兒鄭萌珠產下一名男嬰。當時,該院院長喬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過去許多生殖科患者不願意用真名就診,部分女性因沒有後代承擔著巨大的壓力。如今越來越多的夫妻正以更開放的心態、更理智的思維接受不孕症的評估和治療。“現在,中國輔助生殖技術及其衍生技術,正轉向攻克單基因遺傳病以阻斷出生缺陷、實現優生優育的方向。”
今年8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新增了醫療衛生機構應當“規範開展不孕不育症診療”的表述。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將不孕不育診療納入醫保範圍。“一次全流程治療花費在5萬元左右,幾乎全是自費。”林芝說,現在家庭開銷全靠丈夫一個人的收入,在精神壓力之外,兩人也逐漸感覺到了經濟上的壓力。“在我認識的病友中,類似情況並不鮮見。”
9月15日,國家醫療保障局對“關於‘不孕不育症’輔助治療納入國家醫保提高人口增長的建議”進行了答覆。答覆指出,醫保部門將符合條件的生育支援藥物溴隱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納入支付範圍,提升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用藥保障水平。同時,在診療專案方面,將指導各地,立足“保基本”的定位,在科學測算、充分論證的基礎上,逐步把醫保能承擔的技術成熟、安全可靠、費用可控的治療性輔助生殖技術按程式納入醫保支付範圍。
如今,單晨已是兩個淘氣寶寶的媽媽。手機裡,過去她每天都要關注的試管嬰兒群被各種寶媽群代替。
在單晨曾經走過的求子路上,林芝還在堅持。在內心最深處,她依然存有一個信念:最後的最後,自己會遇上一股“好孕氣”。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林芝、單晨、陶昕、小蕾為化名)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