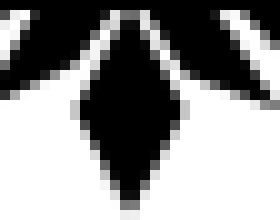引子:在電影結束時,你會得到一些本質的東西。剩下的,全部都是愛。
《鈦》由朱莉亞.迪庫諾導演執導,獲得了法國電影節金棕櫚獎,作為史上第二位斬獲金棕櫚的女性,她在影片中為我們塑造了一場巴洛克式的視覺盛宴,酷兒主義在她的影片中用視聽語被表現,主人公的暴力被救贖消解,孤獨和尋找被愛解構,喜劇的微微點綴,讓觀眾在影片中獲得一種既美好又黑暗的樂趣。
人的本性只有暴力和性,影片開篇10分鐘就用非常絢麗的色彩論證了這個觀點,在充滿節奏的舞蹈中艾麗西亞在的熱舞是她第一次關於身體的對話,作為被男性凝視的舞臺中央,充滿性暗示的舞姿,聲音和一切視覺元素的精心的篩選和處理,與連環炮一樣炸開的情節把觀眾拉進一個充滿質感的,有機與無機、軟與硬相交融的世界。
之後導演用用力拔出掛在乳釘的頭髮和在熱吻中殺死對方兩個簡單的設計,消解了被凝視的主人公形象,用暴力和對性的的厭惡重新構造她的新世界,暴力被理所當然的抬上舞臺。我們熟知的一些暴力美學電影往往用暴力的方式消解暴力,《鈦》不同,她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就要展現十足的暴力,暴力在他眼中反倒成成為一種狂歡,一種舞蹈。
暴力的狂歡可以從主人公父親的缺席中中找到原因,主人公小時候那場車禍,她的生是由鈦賦予,她的情感是有那個他和車的擁抱得到,他沒有一個真實屬於自己的家庭的歸屬感,愛的教育也就缺失了對人性本身的思考,她就像金屬般冷冰冰,沒有生命力,對他來說,暴力殺人只是一場對抗社會的遊戲。
關於和車做愛哪一場戲導演的處理非常神聖化,肅穆的音樂,沐浴乾淨的女性帶著毫無披褂的身體,從鏡子中反射的主人公轉到主人公本身,用肅穆的音樂捆綁的身體和帶有節奏感的音樂對主人公的女性身體從此處閹割,女性的固有特徵變成他的累贅,她變成了我們世俗中所謂的“怪人”。消防站作為一個毫無女性味的場域,他作為兒子的中性形象與女性形象的身體形成強烈對比,無論怎樣勒住乳頭和孕肚。隨時出現的全身的血痕和突兀的黑色石油都在提醒觀眾主人公的怪異和格格不入。
與暴力和孤獨一同伴隨主人公的是他的尋找,他曾在之前採訪說過,“作為一個女人,我根本不希望我的性別來定義我。當人們說我是一個女導演——這總是有點令人討厭,因為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導演。我拍電影是因為我是我,而不是因為我是個女人。我是我自己。 ”影片中的艾麗西亞成了導演在影片中的投射,他希望擁有一個屬於她自己的認識,無關性別。不知所蹤的尋找在文特森帶他去拯救老人生命後得到答案,在文特森給予的她的愛中得到答案。他常對主人公說誰也不許傷害你,即使這個人是我自己。生命的意義對於他不再是以往的刻板印象,因此面對倒地的文特森他選擇剃掉自己另一半頭髮和對於爸爸的稱呼作為儀式感的認同,在男權社會中她得到屬於她的愛和承諾,一個不是因為她是作為女性個體的承諾,而是她作為她自己的愛的承諾。
影片的構建角度是酷兒式的,酷兒文化理論對男女同性戀本身身份提出質疑,批評一種靜態的身份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觀念,他們把身份視作彌散的、區域性的、變化的。
影片的巧妙之處在於將酷兒理論與視聽語言相結合,用燈光、排程共同完成對於性別印象的結構和解構。影片開端影片將鏡頭放置在男性視角,用男性凝視的視角和目光去審視女性,她創造了一個屬於她的性感的、迷幻的世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消防站大家共同的舞蹈中,主人公用了同一曲舞蹈,只是隨著他的身份的改變,大家對於他的舞蹈態度產生極大的變大,迷惑不解甚至父親的憤怒。他的身份以及周遭人對他的態度不再由他本身的行為所定義,而是被性別直接二分,導演用這兩個鏡頭的對比向觀眾丟擲思考。
對於她的生活轉變沒有采用傳統的三幕劇,而是頗具實驗性,運用和車做愛這種富有想象力的畫面,她的生活也隨著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企圖透過弒父行為找到自己的男性身體,縱然透過父權被定義的定義詞已經消逝,但是難逃的是身體的特徵。如果說前半段萬完全是關於女主人公關於反叛意識的塑造嗎,那下一部分就是一種被迫迴歸二元性別評價體系之中對於女性問題的直接反問。
沒有比懷孕和生育更能體現女性氣質的了,影片最後半人半機器的孩子降生結束。半人半機器的孩子擁有著賽博格之軀體,真正的成功的反叛者並不是女主,而是那個孩子嗎,他是真正的酷兒,是機器和人的混合體,是非父親與母親非社會一切就可以被包容的定義者,他處在結構之外,卻又在某種程度上包容了所有性別、所以形態的身體,。生育過程沒有血淋淋的場面,血在導演的設定中變成了石油,黑色的低飽和度的顏色給人一最後的喘息,留給我們的是女主人公滿身的血痕和孩子出生的痛苦。用黑色和現實的生育場景區分,反而給了我們脫離生活本身的思考。究竟什麼是女性?究竟為什麼是女性的反問向我們逼來。
與《生吃》不同,《鈦》的衝擊力直接來自於暴力、疼痛以及對於刻板印象的直接粉碎,也許它最大的優點真的不在於他講述了什麼,而是在於他什麼也沒有講述,只在製造了一個雌雄同體就把現有的制度和性別認知撞個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