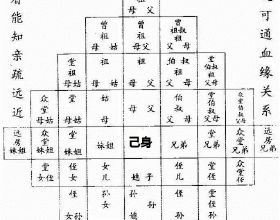作者:林好男
小說《野豬渡河》講述了南洋華人在二戰期間的一段血淚史,同時將地方風物、靈異傳說與宗教秘儀等元素融入其中,充斥著神秘的魔幻氣息。文中刻意模糊了真實與虛幻的分界線,這使得天馬行空的幻想非但沒有沖淡沉重的結局,反而疊加了一絲恐怖色彩。
小說《野豬渡河》封面
一言以蔽之,《野豬渡河》是一本從開卷起就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讀者全部感官神經的書。蔓延叢生的意象憑空編織起一片活色生香的砂拉越雨林,將所有主角與配角網羅其中。復仇、背叛、縱慾,人與動物共生共存又互相殘殺。讀者需艱難跋涉於煙靄盤旋的荒山僻嶺與羊腸曲徑,才有可能通向幽暗的歷史深處。
在選擇此敘事風格的同時,作者也必須直面一個問題:如此疊床架屋的意象堆砌是否有炫技之嫌?理解的關鍵在於,《野豬渡河》並非傳統意義上站在某個族群或個體角度上書寫歷史傷痕的小說。在這個並不複雜的故事裡,在地風景的一草一木,豐沛雨水滋養的萬物生靈,共同將人從敘事的聖壇中心拉了下來。
換言之,這是一部“多中心”或“無中心”的小說,同時也解釋了書名希望表達的意思:野豬曾是豬芭村的原住民,一度以較為穩定的種群方式繁衍生息,卻因為人類的拓殖被無情驅趕,成為無所皈依的林間走獸。“野豬渡河”象徵著一種難以遏制、無法預知的衝撞力量,既張揚著兇猛的生命原初之力,又挑戰著入侵者貌似牢不可破的權威。
“渡河”是動物本能,同時意味著對既定秩序的反抗。張貴興對中文語彙的爆破式使用,也意味著對讀者的挑戰:當萬物之靈長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在野豬的狂濤怒蹄下被粉碎,人降格為弱肉強食的自然世界之普通一員,讀者必須採取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理解人與萬物的關係。這個蠻荒天地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是遙遠的邊疆,但對張貴興卻是難以迴避的原鄉。
特殊的文化背景與個人審美取向,共同決定了這本書濃墨重彩的自然風物描寫,在此基礎之上則是同樣飽滿的人物群像。《野豬渡河》採用了不斷切換視點人物的寫作手法,不同章節經由不同主人公進入故事,最大限度增強了歷史的縱深感與層次性。不同於主旋律戰爭文學中的英雄人物,張貴興筆下的豬芭村抵抗者們,就是一群被逼到生死存亡之際的普通人,既缺乏系統化領導抵抗的韜略與頭腦,也並非為著共同目標被緊密捏合在一起的共同體,這無疑是一種大膽的顛覆。
面對突然降臨的戰爭,這些普通人被迫拿出賴以謀生的看家本領。作者無意於拔高這一行為,也沒有賦予任何人主角光環。平心而論,書中的人物無法激發讀者太多壯懷激烈的情感,讀罷只覺意難平,但這正是作者希望實現的另類抗戰書寫,也是宏大革命敘事背面另一種叩問歷史的可能。
承認文化背景與生存環境的巨大差異,正視無名之輩身上的弱點與陰暗面,是尊重歷史的先決條件。它無損於抵抗行為本身的正義與光榮,也令故事更細膩可感、真實可信。在書寫死亡時,作者將白描用到了極致。在日軍橫行的三年八個月裡,觸目驚心的屠戮幾乎令天地變色。張貴興像手握手術刀的醫生,不動感情地將歷史的傷口一一呈示。槍決、梟首、斷肢、剖腹,還有更多不忍卒讀的凌辱虐殺。死亡來得普遍、急促而不加掩飾,描寫越細緻冷靜,越令人頭皮發冷,在這種強烈的視覺加心理衝擊面前,已經不需要其他多餘的煽情了。
在直面戰爭的同時,張貴興用貫穿全書的“面具”意象由實及虛,再次拓展了文字的深度。作為玩具的塑膠面具,被孩子當成惡作劇時的偽裝,天狗、九尾狐、飛天人頭……看似人畜無害的面具背後,潛藏著當地詭譎幽暗的神話傳說。弔詭之處在於,孩子不甘日常生活的庸俗,紛紛戴上面具遮蔽身份,渴望藉此加入神話譜系以獲得超自然力量,卻無一人可以成功。需要隱藏真實身份與不堪往事的人,無需面具仍可遊走世間,比如朱大帝、小林二郎、愛蜜莉。童稚的爛漫藏在面具背後也還是童稚,最恐怖的不是面具上的神鬼,而是一個人就站在面前,你卻不知道他/她的真實面目。“抓內鬼”作為故事暗線借面具這個意象延續到結尾,帶出的真相出人意料,也讓這本書多了一層濃重的推理色彩。
這是一部拒絕迎合市場需求並自設門檻的嚴肅文學作品,繁複華麗的語言和時空錯亂的敘事,給閱讀帶來了不小的困難,難以觸達更廣泛的讀者群體。在語言與地域之外,故事的主題並未脫離入侵-抵抗的舊傳統,反派的形象過於臉譜化,無法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對歷史的反思則是淺嘗輒止。
諸多不完美之處,顯示了馬華作家群在文學突圍中面臨的挑戰:怎樣既保留個體/群落特色,又不令鮮明的地緣特徵成為噱頭;如何處理國族認同與身份焦慮,在不被歷史吞噬的同時介入新的現實。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條文學寫作與現實生活雙重意義上的荊棘之路,但荊棘之上必有王冠。(林好男)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