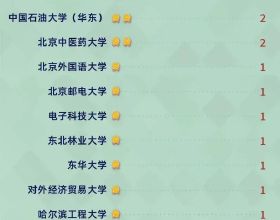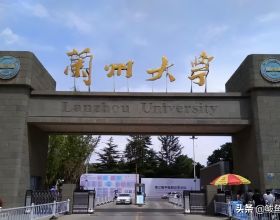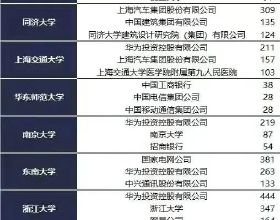女博士趙可心和自己的母校“槓”上了。
2021年7月底,在華中科技大學一路讀完本碩博的趙可心在直播中宣稱,“像我們這種有關係的,哪怕你的分數不夠華科的線,你就上一個二本學校,後面都可以轉學轉過來的。”
靠著一場效仿演員仝卓的“自曝”,趙可心迅速將母校和自己捲入輿情。
華中科大本科生院在7月30日釋出宣告表示,趙可心言論不實,趙於2008年報考該校並被錄取,錄取符合高考政策,其父母非該校教職工。但華中科大未回應是否有教職工子女轉學。
2015年5月釋出的《關於進一步規範普通高等學校轉學工作的通知》,收緊大學生轉學範圍,規定了10種不得轉學的情形。這份通知到了2018年1月宣告廢止。 (視覺中國/圖)
事件引發了輿論對大學生轉學的關注。實際上,這一制度很早就有,1990年國家教委頒佈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就允許確有專長、入學後發現某種疾病或生理缺陷和確有某種特殊困難的學生轉學。日後,轉學制度經歷了多次調整,在鬆緊之間搖擺。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缺少公開和監督,轉學制度中滋生出影響教育公平的現象。趙可心之前,最大的爭議事件發生在2015年,17名從外校轉入湖南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被撤銷轉學,隨後,教育部迅速收緊大學生轉學政策。
女博士“自曝”之後
對於自己在直播間的行為,趙可心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為“刻意為了引起關注”。前述“自曝”前,她已和華中科大就大學生轉學一事有過幾回合“較量”。
事情的起點,趙可心稱是一次招聘。她在深圳成立的公司,在2021年5月招聘時,發現有應聘者的高考錄取學校是其他一本高校,畢業學校卻是華中科大。
趙可心說,在她本科期間,身邊就有同學是透過轉學入讀,且是從比華中科大錄取分數低的學校轉入,她懷疑背後有“暗箱操作”,因此一直關注轉學問題。
隨後,趙可心以企業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華中科大和湖北省教育廳分別申請了資訊公開,申請公開內容為該校2010-2014年五年間所有轉入、轉出的本科生、研究生名單。
趙可心展示的郵件截圖顯示,5月26日,華中科大資訊公開辦公室向她的公司拒絕了申請,回覆為“因涉及個人隱私,該資訊不屬於應公開範圍”。
7月5日,湖北省教育廳也拒絕了,理由同樣是“涉及個人隱私”,且“經審查,該政府資訊公開後會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
為何是申請資訊公開而不是舉報,趙可心解釋,按照當時施行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如果確有特殊困難,從分數低的學校轉到分數高的同批次學校是合規操作”。
這份出臺於2005年的檔案規定,學生如患病或者確有特殊困難,無法繼續在本校學習的,可以申請轉學。同時規定了幾種不得轉學的情形,其中包括“由招生時所在地的下一批次錄取學校轉入上一批次學校、由低學歷層次轉為高學歷層次的”。
轉學的始終是少數人。以湖北為例,湖北省教育廳2008年出臺的《進一步規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轉學工作的意見》提出,對每年轉出轉入學生實行總量控制,中央部委高校、省屬本科學校原則上不突破上年錄取學生總數的3‰。
花五萬就“鑽了空子”
儘管受關注度不算高,但大學生轉學其實一直在進行。
比如四川省教育廳2021年7-8月分5次公佈了共14名大學生的轉學情況,當中有10人是因“身體原因”轉學,另4人因“個人原因”。14人的高考分數,都高於轉入學校生源地當年的最低分。
其中有一人原為清華大學2019級高分子材料與工程系學生,因身體原因,他轉入電子科技大學軟體工程系就讀,並“留級”一年。
按照規定,大學生轉學要經所在學校和擬轉入學校同意。正常流程是:學生聯絡打算轉入的高校,提出申請、說明理由,擬轉入學校負責稽核轉學條件及相關證明,認為符合培養要求且學校有培養能力的,經學校校長辦公會或專題會議決定,便可轉入。轉入學校在公示通過後,報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備案。
跨省轉學的,還要由兩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商定。
轉學流程運轉多年,但趙可心對轉學存在“暗箱操作”的質疑,確有現實案例作為基礎。教育系統內,有多名落馬官員的違紀違法情節中就包括為他人在大學轉學上提供幫助。
曾擔任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黨委書記的張立奎2014年落馬,經法院查實,張立奎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共計191萬餘元,被判受賄罪,處以有期徒刑八年。
裁判文書顯示,在張立奎的受賄款項中,有一筆5萬元的款項就是在幫人轉學中收取的。2012年下半年,張立奎利用擔任鄭州航院黨委書記的職務之便,向時任教務處處長“打了個招呼”,幫助內蒙古赤峰學院的一名學生轉到鄭州航院。
甚至教育系統內的一個處長也能幫人解決轉學問題。2005年,時任浙江省教育廳高等教育處處長方永平,接受浙江理工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院長助理沈某的請託,為其朋友的小孩從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轉學到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提供了幫助。
一些腐敗官員則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讀更好的大學”。
陝西省委統戰部原副部長唐勇於2020年6月落馬,他曾擔任陝西省略陽縣縣長、縣委書記。根據唐勇自己的說法,2008年6月,其子參加高考後,錄取到了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但之後其子想轉去別的學校。2008年下半年,唐勇和略陽縣商人鄧偉朝吃飯時,提起此事,鄧提出幫忙。
鄧偉朝透過運作,找到四川師範大學時任校長周介銘,2008年9月,鄧偉朝等人宴請周介銘,席間悄悄送出10萬元現金。5個月後,在周介銘幫助下,唐勇的兒子轉入四川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就讀,該校是川師大對口的“專升本”院校。之後在2011年5月,唐勇兒子成功透過“專升本”,進入川師大航空港校區讀本科。同年8月,鄧偉朝以答謝為由,又送周介銘2萬元現金。
也就是說,一共花了12萬元,鄧偉朝成功幫唐勇的兒子完成了轉學並就讀本科高校的願望。
操作大學生轉學時,相比轉入學校,轉出校的稽核要寬鬆很多。裁判文書顯示,2015年,四川井研縣高考生陳某被錄取到了攀枝花醫學院(編者注:裁判文書原文如此,攀枝花醫學院應為攀枝花學院醫學院),她的母親託人找到一名叫李雪瓊的女子,託其幫助陳某轉到成都醫學院就讀。
辦理轉出手續時,李雪瓊偽造了一份寫有陳某名字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門診部的虛假病情證明書,讓陳某家長以此找學校辦理轉學手續。“經不住陳某家長的執拗”,攀枝花醫學院為陳某辦理了轉學手續,還作了轉學公示。
但陳某的轉學事項在成都醫學院卻不太順利,該校多個部門拒絕了陳某的轉學。事情沒辦成,李雪瓊卻收受了12萬元“好處費”,後來李雪瓊被判詐騙罪,被處以有期徒刑三年。
哪些大學生能轉學
四川井研縣的陳某想操作轉學時,教育部門對轉學的規定已經比之前嚴格了許多。
李雪瓊詐騙案在審理過程中,時任成都醫學院公共衛生系黨總支副書記阮衛明作了證,他說,大學生轉學必須是同級別同專業,高考分數必須達到轉入院校的最低錄取分數線,然後轉入學校開校長辦公會討論同意報省教育廳審查通過後才能轉入,任何一個環節不滿足都不行。
哪些大學生可以轉學?
最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於2017年修訂,其中規定,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難、特別需要,無法繼續在本校學習或不適應本校學習要求的,可以申請轉學。同時也規定,有六類學生明確不能轉學,其中就包含了高考成績低於擬轉入學校相關專業同一生源地相應年份錄取成績,以及由低學歷層次轉為高學歷層次的學生。
回顧歷年轉學政策的修訂,允許轉學的學生範圍經歷了先寬鬆後限制再放寬的過程。這一變化背後,存在著幾個關鍵時間節點。
2015年前,轉學政策相對寬鬆,當時施行的是2005年出臺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其中對轉學的限制條件是“不能下一批次錄取學校轉入上一批次學校”,也就是說不能從二本轉入一本,但一本高校之間可以互相轉學。同時,該規定也未要求公示轉學資訊。
2015年1月的湖大事件是一個轉折點。當時,湖南大學被曝一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轉入,轉學理由有“飯菜太辣”“油畫過敏”“不適應氣候”等,公眾質疑轉學環節或存在腐敗。事件發酵後,教育部派出專項督查組進行調查,取消了17名學生的轉學資格,並對湖大領導作出處分。
短短三個多月後,教育部辦公廳就下發《關於進一步規範普通高等學校轉學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相比已執行十年的規定,新的檔案將不得申請轉學的學生類別由原來的五類擴大到十類,增加了“高考分數低於擬轉入學校相關專業相應年份錄取分數的”,不允許同城轉學、跨學科轉學等。此外,以患病理由轉學的還需提供指定醫院的檢查證明。
此後,大學生轉學流程需要經過更多行政層級同意、簽字。最關鍵的是,這份通知增加了過往沒有的公示環節,要求高校公示擬轉學學生資訊,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公示轉學結果。
這一通知的出臺,收緊了轉學渠道,也引起了一些反彈。
曾參與2005年版規定研究和修訂工作的北京大學教務部原副部長盧曉東就撰文質疑,新規讓學生幾乎無法開展正常的學籍選擇,因為實際中願意從高往低轉學的學生幾乎為零。此外,接受轉學學生本來就是件麻煩的事,高校並不願意,現在限制更多,責任更大,高校不接受轉學是最簡單的回答。
盧曉東認為“轉學對於人才成長十分重要”。他舉例稱,語言學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保亞,1977年參加高考進入華西醫科大學,就讀期間閱讀了很多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以及語言學的書籍,對理論語言學產生興趣,後轉學到西南大學中文系。“陳保亞是跨學科轉學,如果放在現在,不會再有‘陳保亞們’了。”
2015年11月,教育部辦公廳對《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進行修訂,並向各高校徵求修改意見。這次修訂稿中,不予轉學的學生類別縮減為八種,轉學申請的行政稽核步驟也有所減少。
修訂在2017年透過並沿用至今,不予轉學的學生最終縮減到六種,只比2005版多一種,即要求研究生擬轉入學校、專業的錄取控制標準不得高於其所在學校、專業,從政策層面上堵死了“由低轉高”的渠道。
與2015年下發的《通知》相比,2017年版規定允許同城轉學、跨學科轉學、非高考方式錄取的學生轉學,是一個顯著的放鬆訊號。在公示環節方面,保留了對學校的轉學情況公示要求,而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只需備案,無需公示。
不過,與2017年版規定有所矛盾的《通知》,到了2018年才宣告廢止。2018年1月,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宣佈一批不利於“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最佳化服務”改革的規範性檔案失效,其中就包含了上述《通知》。
透過考試插班轉學
2015年湖大事件後出臺更嚴格的轉學規定,目的應是為了填補可能滋生腐敗的漏洞。而之後的政策放鬆,又為大學生流動重新放開了“口子”。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從行政流程和政策規定上來說,轉學的難度比較大,這些年高校轉學學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因此,他認為以非常規手段操作轉學不能視為普遍問題,轉學制度規避權力尋租,最重要的還是資訊公開化,公示轉學的正當理由。
“從這些修訂過程來看,大家還是希望有轉校機制來修補高考的制度、大學的招生制度,”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我們應該鼓勵轉學,而不是說嚴控轉學,要建立起自由申請入學制度和自由轉學制度。”
2014年遼寧文科狀元從香港大學退學復讀再考北大,曾引發關注。高校學生退學復讀再考的例子不時傳出,反映出高校間轉學流動的困難。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看來,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涉及招生方面的指標都是嚴格限定的,“高校本身沒有獨立的招生權,也沒有完整的學籍管理權,招生人數還必須跟畢業生學位能夠對應得上,所以轉學起來比較難”。他提到,哪怕是由高轉低的學生,也會遭到重重阻礙。
“所以說現在陷入一個困境,”熊丙奇談道,“嚴格執行轉學制度,一群人的轉學需求就無法實現,而一旦放寬,又擔心有人利用漏洞,運作到更高的學校。”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高校去行政化。“轉學是行政操作,就可能受到行政和利益的影響。”
有意思的是,“轉學難”雖是大背景,但有的地方早已常規化開展高校公開招考式轉學嘗試。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同意上海開展普通高校插班生工作試點,至今已推行21年。這一試點的初衷是“發揮高等教育立交橋的功能”,給部分高考發揮欠佳、志願填報不當的考生重新選擇的機會。
這一制度允許包括復旦、上交在內的上海12所院校在部分專業中招收“插班生”,上海所有高校的大一年級新生只要成績合格都可以報考,甚至民辦院校的學生也能參加。
多所上海“插班生”試點高校的相關負責人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如被錄取,“插班生”可以辦理轉學手續,學籍也能轉入被錄取高校,並能在被錄取高校獲得畢業證和學位證。2020年,上海被允許轉學的插班生為257名,2019年是264名。
部分高校對插班生的條件有所要求,如同濟大學要求考生高考分數須達到一本投檔分數線,華東理工大學則要求必須是相近專業才能報考。
多所高校都強調了插班生考試的公平性,尤其強調有公示流程,華東師範大學的相關負責人還表示,插班生考試試卷由出題學校統一批改,往年考題都不會流傳出去。
南方週末記者 張笛揚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劉岍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