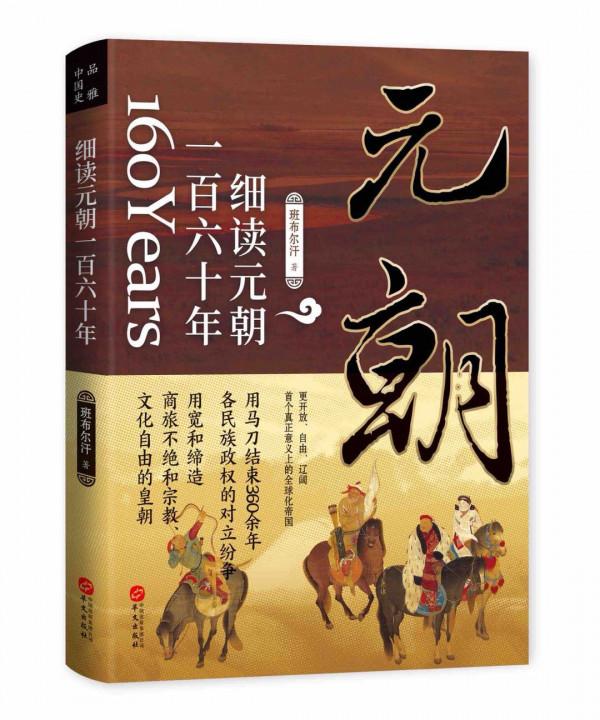文/班布林汗
對中國人來說,元朝是一個奇異的存在。在學術界,元史可算是各斷代史中被研究得最為透徹全面的,大師輩出,名著充棟,用纖毫無餘來形容都不過分。但學術與民間的隔閡,使得元朝在民間總是一種大而化之、模糊不清的印象,各種傳說誤解多如牛毛。不論是早已有之的“人分四等”“九儒十丐”“十戶用一把菜刀”,還是網路文學興起後產生的“初夜權”“摔頭胎”等等,都將之描繪成一個黑暗壓抑的恐怖時代。
近年來,隨著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日本學者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戰》等書的熱銷,元朝又被他們描繪成一個大有現代化風格、有著全球化思維、締造了全球化商業網路的時代。
也許,黑暗也好,全球化也罷,都是人們有著一個先入為主概念,將元朝視之為一個特殊的時代。而因為視之“特殊”,便總是會尋找、描述乃至放大其特殊。似乎這個由遊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另類,對其在中國歷史上該處於什麼樣的位置而予以忽略,於前無繼,於後無續,異軍突起,又迅速消失於歷史中。
歷史是複雜的、立體的、豐富的,有著不同的面向和層次。用“特殊”來看待一個時代,貌似深刻,實則有些偷懶。我其實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簡單、清晰、黑白分明的答案。這會讓自己有一種看清一切的自信,可實際上除了“特殊”的噱頭之外,並無所得。看元朝,便要先放下這“特殊”,用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去了解其複雜,才能不吹不黑,得到些真東西。
前所未有局面下進行各種除錯
元朝政策多變、皇位更迭頻繁、施政寬縱怠惰這些缺點,與社會環境寬鬆、文化多元開放、商業繁榮、宗教自由等優點,都來自於元朝處在一個“除錯時代”,其盛其衰,其成其敗,其興其亡,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下進行各種除錯的結果。統治地域囊括前代未能達到的區域,內部多種文化並存,中原帝制與草原封建的傳統都要顧及,因此需要雜糅各法,元朝的所謂行漢法和維持漠北舊制的矛盾,其根源即在於此。“人分四等”這樣的誤解,便是在這除錯時代所遺留的問題。
這種除錯時代,在歷史上不乏先例。例如人們通常將“秦皇漢武”並稱,而兩位帝王之間的時代便是除錯時代。秦始皇統一六國,結束了延續近千年的封建,而代之以集權皇權,將周制變為秦制,何嘗不是空前的大變局,即使以當時已知世界各文明相比,都算得極為特殊了。可這步子邁得太大,並不能短時間內完成。秦朝二世而亡,漢朝繼起,雖然要堅持集權皇權,但也不得不有所倒退,還是要保留封建。最後使得封建再不足以合理合情地威脅集權,則是漢武帝時代最終完成。
而另外並稱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興科舉,是將選官的權力完全收歸皇帝,而不再如之前那樣,皇帝只有任命權,察舉權卻在世族。畢竟世族尚未完全衰落,唐朝的科舉並未完全實現“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設想,世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體系。直到宋朝,經過黃巢之亂與五代十國,世族徹底衰落,宋太祖及其子孫才真正用科舉做到選官任官皆出自皇帝。
至於在最終完成之前,除錯時代總免不了混亂。秦朝短命而亡;漢初異姓王之亂、七國之亂便是封建走向集權的代價;而唐朝科舉難以真正公平,關隴、山東、江南親疏有別,乃至藩鎮之亂、宦官亂政,也都不能不說是世族走向衰落,皇權進一步加強過程中的代價。元朝也如秦、唐一般,在除錯中摸索前行,最終帶著除錯未能完成的遺憾而崩潰。後來者汲取其經驗,完成了除錯。它其實並不特殊,只是歷史走到一個階段時必經的過程。
種種誤解和溢美
這本《細讀元朝一百六十年》便是無視元朝的特殊,將之作為與其他朝代一樣,既有其特色,又有著歷史傳承的朝代來撰寫的作品。在將其歷史掰開揉碎呈現給讀者的同時,把曾經的種種誤解和溢美都予以澄清。
人們會看到,被神化的蒙古鐵騎,並非是亙古未有的天降神兵。其耀眼的戰力與戰績,是結合著草原民族的特點、超強的組織手段和大力吸收歷史與其他民族文明成果,才鍛造出來的。若非所有人被完全動員起來成為這架軍事機器的一部分,全力為戰爭服務,蒙古人的行動式給養方式,以及快速機動的作戰方式,最多隻能自保,要想衝出草原去征服世界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生滅國無數,締造戰神傳說的成吉思汗,也有著眾多無奈和妥協。他雖是自己締造的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須臾間可決定千萬人的生死,但因為傳統的力量,“形式上權力和帝國歸於一人,即歸於被推舉為汗的人,然而實際上所有的兒子、孫子、叔伯,都分享權力和財富”,而這些無奈和妥協也決定了蒙古帝國與元朝的命運。
面對祖先的帝國不可避免的分裂,忽必烈看似繼承,實則開創,變蒙古帝國為元皇朝,“定官制,立紀綱”,“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但在其煌煌威儀,赫赫武功之後,也有著無力感,因為他和他的子孫算得走一步看一步,並無現成的治國方法一勞永逸。從他開始,元朝便在蒙古法、回回法與漢法之間進行調和,以適應空前的大一統形式。除錯意味著動與亂,而動與亂之間有巨大的自由空間。
歷朝歷代都重農抑商的政策被改變,元人對經商趨之若鶩,“工商淫侈,遊手眾多,驅壟畝之業,就市井之末”。不但“小民爭相慕效,以牙儈為業”,原本對商業嗤之以鼻計程車大夫,也認為“胸蟠萬卷不療飢,孰謂工商為末藝”,大加讚賞從事商業,認為是具有“仁、智、勇、斷”的“四德”的事業。南人北上經商,北人南下行賈,乃至出國經商航行萬里,人口流動頻繁,規模巨大,朝廷對社會的管控就形同虛設。以至於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評價元朝之亡,認為“其失在於縱馳”,所謂縱馳,就是管控不善。
人們會了解,元朝尊孔重儒,在孔子原有的“至聖文宣王”之上加“大成”二字,使孔子在中國歷史上達到至尊至聖的地位。歷代儒門先賢都被賜以封號——“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程朱理學被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氏、朱晦庵批註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學。”至於講授儒學的書院,“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
與此同時,科舉卻不興盛,讀書人大多哀嘆“空巖外,老了棟樑材”,以至於後世有人堅信元朝“八娼九儒十丐”。儒士地位很低,這其中的矛盾與原因究竟何在?大量文人從象牙塔走出,在市井中尋找自己的出路。繼唐詩、宋詞之後,中國進入了更自然、更接地氣的元曲時代。王國維先生評價元曲的特色,曾說:“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為什麼“最自然”?因為那時是文人最“沒人管”的時代,不僅是現實中用官爵名利來進行“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管理,就是在思想上也化解了不少“治國平天下”的自我期許,於是便徹底“自然”了。
摒棄看似複雜實則將歷史簡單化的心理
人們會知道,在那個時代,君王和將軍們金戈鐵馬、開疆擴土確是舞臺主角。但在主角周圍還有更多人物,甚至比主角更為傳奇,留下的影響更為深遠。以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與成吉思汗留下“一言止殺”佳話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將禪宗帶入蒙古,並將自己弟子留給蒙古皇室,使之成為一代名臣的印簡海雲法師;將少林寺修建到漠北草原,死後被尊為國公的雪庭福裕禪師;將藏傳佛教東傳,並使得徒子徒孫都成為大元帝師的薩迦班智達;來自義大利,在元朝成為中國第一個天主教總主教的孟高維諾;在印度、波斯、元朝、高麗之間折衝樽俎,掌控海商的傳奇豪商孛哈里;以一己之力兩次遠航,途經二百多地區與國家,直達非洲東海岸,並留下詳細記錄的儒生旅行家汪大淵,還有“曲聖”關漢卿、色目大詩人薩都剌等等人物,讓那個時代精彩紛呈。
人們更會發現,一些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其實也遠不是那麼簡單。蒙古帝國和元朝的關係究竟如何?究竟元朝的時間該如何計算?元朝的疆域是否空前絕後?是否真的可以超越之前的漢唐和後來的清?元朝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是否真的是高峰後的低谷,沒能恢復到前代的水平?元朝徵日本與安南失敗,真的是因為“神風”和熱帶雨林氣候嗎?現代蒙古人天天離不了的蒙古奶茶,是從元朝就開始喝的嗎?也許看完本書,讀者會有原來如此的感嘆。
當然,讀史不是為了獵奇,一本不吹不黑的元史作品也並非執著於“翻案”與“澄清”。我所希望的,是讀者能夠透過這本書摒棄那種看似複雜實則將歷史簡單化的心理,看到一個曾經真實存在、有特色而並無所謂“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繼承了前人的成果與錯誤,也將新的成果和失誤留給了後人。
今天的我們,不得不承受歷史留下的負擔,也順理成章享受著歷史留下的果實。那我們回望歷史時,就如爬上山坡的時刻回望曾經的路,看清坎坷,看清坦途,領略風景,然後才有真的自信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