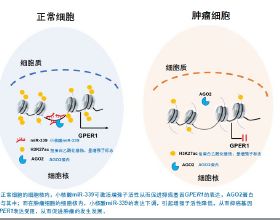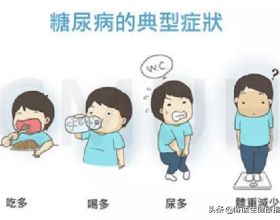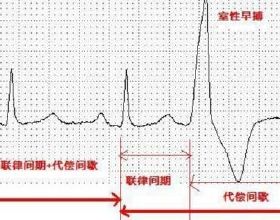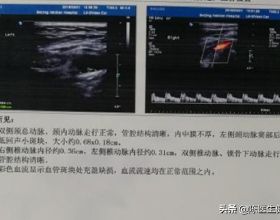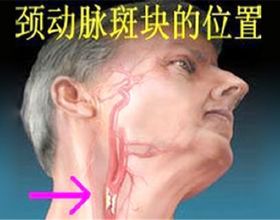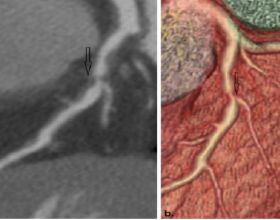1996年的夏天,我在南八仙拍攝一部講述養路工故事的紀錄片《與荒原對話》。那片亙古不變的荒原給我帶來的感動,至今不能忘懷。
南八仙
1955年的一天, 新中國的八名女地質隊員在這裡考察時遇到沙暴,迷失了方向,再沒能走出這片荒原,從此,便有了南八仙這個地名。隨後這裡有了唯一的居民——養路工。
南八仙位於青海西部的柴達木盆地腹地。在這裡,除去一條蜿蜒的鹽漬路,就是千年不變的赭黃色的雅丹地貌。在這裡,就連七、八月份猖獗的蚊子、牛虻都會讓養路工欣喜若狂。在這裡,養路工看一眼陌生人的面孔,聽一聽陌生人講話,是一種做人的享受。
我們第一次到南八仙養路段是八月份的一個傍晚,夕陽餘暉灑滿了那個孤單的院子。南八仙的居民們好奇的看著我們。在這群人裡,我第一次見到了有些傳奇色彩的南八仙公路段黨支部書記王子華。他正站在門口拍打身上的塵土。
王子華59歲,中等身材,粗粗壯壯很結實的樣子。他有些冷漠的看著我們。王子華是老柴達木人。在柴達木開了30多年汽車。1991年快退休了,海西總段領導說:南八仙總搞不好,你去南八仙當書記吧。他就來了。後來知道,王子華祖籍安徽。
您是哪一年參加工作的?
58年4月28號。
對於這個30多年前的日子,他似乎是不用想就說出來了。
第一次當勞模是哪一年?
記不清了,反正當過好多回。
王子華靦腆地一笑,說:有一回領獎,發獎的人把我的名字念成“王了華”。當時挺有意思,現在也忘了是哪一回了。
他講話很慢,似乎是在努力適應談話環境。
那天吃晚飯時,王子華從自己辦公桌裡拿出一瓶“互助頭曲”。
他說:我喝不多,你們多喝。
只兩三杯,王子華果然臉色酡然。他又說:我原來不喝酒。我是開車出身,開車不能喝酒。後來因為腿傷,醫生叫我喝點虎骨酒,就慢慢地喝一點了。
1961年,那時的王子華還是個毛頭小夥兒。那年冬天特別冷。王子華開車給大柴旦段送菜,大清早就上路了。高原的天氣說變就變,出來時長空如海白雲如絮,走了才幾十公里就下起了大雪,風颳得像刀子一樣。汽車拋錨了。司機冒著大雪去叫救援,留下王子華看車。
王子華躲在駕駛室裡,裹緊棉大衣。開始兩三天,他還想吃東西。雪不停地下,風越刮越緊。王子華感到頭重腳輕,走路輕飄飄的,那感覺就跟走在棉花垛上一樣。到了第六天,救援的人才趕來。他們把王子華抬到屋裡,給他做好熱麵條。他不想吃只想睡覺。
王子華說:從那以後,這腿傷就留下了,陰天下雨就疼。還算萬幸,我保住了這條命。
最後他拍了拍那條傷腿:這兩年好多了。
我很好奇,當時車壞在什麼地方?
王子華不好意思地說:就在石門附近。車上拉著全段職工的給養,丟了可不是小事。
後來,我們採訪路過石門,才知道這個地方離柴旦並不很遠。
第二天,我們在五道班見到和工人一起幹活的王子華。但當我們架好攝像機拍攝時,發現原本認真整理邊溝的王子華停下手裡的活,背對著我們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等我們把鏡頭對準其他養路工時,他又彎腰幹了起來,等鏡頭轉過來,他又停下來,站在那裡不動了。那一刻,我看著風沙裡的王書記,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背對我們站立的身影,眼淚奪眶而出……
十四日下午,王書記陪同我們去冷湖鎮採訪。他的家就在冷湖鎮,一個戈壁灘上的石油小鎮。
那天剛下過雨,鹽漬路上有些積水。王子華不停地囑咐司機:靠邊走,靠邊走。
從南八仙到冷湖120公里,公路在被稱為“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中穿行。這段路是鹽漬路。鹽漬路是青海養路工人因地制宜的一大創造,它用柴達木盆地取之不竭的鹽鹼土鋪成。晴天時,路面平整堅硬,暢行無阻。但每逢下雨下雪,路面就形成一個鬆軟層,汽車走在上面,不但容易出車禍,而且損壞路面。這段路的每一個道班房上都寫著:“鹽鹼路面雨雪後不通車”。
王子華開啟車門,探出半個身子看著剛剛軋過的路面。他像是在自言自語:鹽鹼路沒有水養不成,水多了也養不成。下點小雨挺帶勁兒。當他看到車輪在路面上軋出兩道泥溝時,他著急地說:拉壞了拉壞了,靠邊靠邊。司機也心疼路:我也沒辦法。王子華一聽火冒三丈,瞪著眼珠子喊:你也是養路的,你沒辦法,我看你就是犟得很。停下,等路乾點再走。
十五日,我們的採訪結束了。這時是上午十一點半。王子華拿起門後的編織袋和我們一起出門。編織袋裡裝著一些蔬菜。他每次回冷湖家中,都要帶些蔬菜回南八仙。開始我們以為王書記是在送我們,一再讓他留步。他一句話不說,固執地往外送。
他的愛人肖大彩從屋裡追出來:你回來吃飯嗎?
王子華:我走啦。
……
當天晚上,王書記和我們一起回到南八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