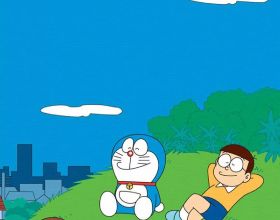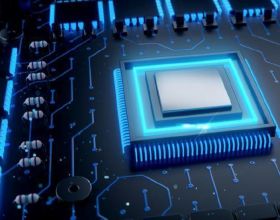壹
是夜,狂風驟聚,風雨飄搖。四方客棧來了位奇怪的客人。
男子頭立青箬笠,只露出稜角分明的下巴,玄色錦服下襬沾染了些許泥漬,身上攜著風塵僕僕的味道。
男子手中死死攥著一把劍,低沉清冷的聲音在客棧裡緩緩響起:“住店。”
小二被驚得一哆嗦,“這位客官,實在對不住,小店已經打烊了。”
男子抬頭,深眸緊緊盯著小二,俊朗立體的五官慢慢露出不悅的神色。他手指輕挑,長劍猶如甦醒的青龍脫鞘而出,還未等小二反應過來,攜著泠泠幽光的冷劍已經橫在他的脖頸。
小二腿腳直抖,顫顫巍巍的看著眼前之人。
“哪來的客官,竟如此狂妄。”
慵懶魅惑的聲音猶如柔軟又尖利的貓爪,一字一句,輕輕的撓在人的心口。
小二聽到聲音,鬆了口氣,轉頭看向緩緩下樓的女子。
“叮鈴鈴,叮鈴鈴。”
女子腳踝繫著一顆銀鈴,鈴鐺聲在寂靜的客棧裡顯得尤為清晰。她烏雲秀髮,柳枝瘦腰,眉如春山淺淡,眼若秋波宛轉,勝似海棠醉日,滿目皆是迷惑人心的妖魅。
一身紅衣猶如展翅欲飛的赤蝶,紅色紗裙兩擺叉開,讓修長的雙腿若隱若現,愈顯得她妖嬈嫵媚。
男子看著越走越近的女子,突然一愣,好似有種熟悉之感,但這種感覺僅一閃而過。他眉頭微皺,眼中透露出不耐。
他最是討厭滿身煙塵味的女人。
“掌櫃的......”小二求助的看著女子,聲音微顫。
女子無視男子眼中的冷漠,笑得嫣然耀目,彷彿想把對方的魂勾了去。
她將手中的紅色羽扇一展,慢慢靠近男子,“客官是要住店?”
男子看著快貼到自己身上的女人,眉頭皺得更緊。他默默收了劍,板著臉點了點頭。
女子輕睨了一眼窗外,一道白光閃過,墨色天空彷彿被撕裂了一口子,隨後便迎來震耳欲聾的雷聲。
她展開扇子掩嘴一笑,魅人的桃花眼波光瀲灩:“小店原已打樣,但閣下俊逸非凡,模樣甚佳,我就勉為其難為你破一次例。”
男子面色鐵青,很是不悅。
女子繼續笑著,踮起腳尖突然貼近男子的面容,一陣幽香便鑽入他的口鼻,讓他心神一晃。
男子一怔,隨即後退一步,黑著臉將一袋數量不少的銀子扔在桌上,面容似乎有些惱怒。
女子輕笑一聲,對他伸出手:“年綰綰。”
男子無視她伸出的手,眼裡有幾分輕蔑。他徑直越過她,對著小二冷冷出聲:“房間在哪?”
小二又是一抖,不知所措的看著年綰綰。
“給這位客官安排最好的天字房。”
年綰綰轉過身,慵懶的扇著紅色羽扇,頗有深意的盯著男子。
男子冷漠的轉身離開,避開年綰綰的視線。很奇怪,他只要看見這女人的眼睛,總會心神不寧。
“沈戎。”
他的腳步一頓,指尖微動,電光火石之間,青劍脫鞘,直指年綰綰眉心。
沈戎墨色的眸子裡透出濃濃殺意,“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小二看到命懸一線的掌櫃,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但年綰綰好似並未被眼前之景所嚇,她慢條斯理的擺弄著青絲上的簪子,隨後懶懶的用羽扇將劍慢慢推開。
“劍鞘上寫的。”
沈戎緊緊擰著眉。
“要隱瞞身份就換把劍。”女子戲謔的說道,“你說對嗎?一品監察史大人。”
客棧內靜謐得可怕,年綰綰接著說道:“不過客官且安心待著,我年綰綰混跡江湖兩年有餘,自然懂得江湖那一套規矩。更何況......你現在除了這裡,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又是一記閃電,映得客棧忽而一亮,外面狂風暴雨,絲毫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沈戎就這樣靜靜的盯著年綰綰,一言不發。
二人靜靜對視了一會兒,年綰綰忽然對他挑了個眉,故作嬌羞的嫣然一笑:“官家莫不是是瞧上奴家的面容,竟這般盯著小女子。”
沈戎嘴角一抽,嫌棄的轉身離開。
果然是煙塵女子,絲毫沒有閨中女子的矜持淑德,禮儀姿態。
貳
“沈戎,一品監察史,最年輕的殿閣大學士。”
年綰綰逗著籠子裡的黃鶯,嘴裡輕念出聲。
不過,據年綰綰所知,監察史沈戎三日前受太子牽連,被皇帝親自罷黜。
皇帝已到垂暮之年,僅僅吊著一口氣。太子和四皇子是皇帝最為欣賞的皇子,二者之間猶如楚河漢界,各領文臣武將,表面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湧動了多年。
眾所周知沈戎乃太子麾下第一大臣,二人從小一起長大,情同手足。
按理來說,縱使四皇子蹦躂得再厲害,待皇帝駕崩,太子還是能名正言順的登基。但就在三日前,太子忽然被彈劾私通外敵,禍亂朝綱。氣得皇帝隨便指了座邊陲小城給他封了王,將他打發了。
太子一黨,均受牽連,包括沈戎。
年綰綰停下手裡的動作,開啟房門,正好遇見了手持食盒的雜役。
“掌櫃的。”小役對她打了聲招呼。
“去哪兒?”
“天字房的客人要求將飯食送到屋內。”
年綰綰朱唇輕啟,饒有趣味的問道:“這些日子,他都沒出過門?”
“是。”
年綰綰接過食盒,“這次我去送,你去忙。”
雜役一聽,黯淡的眼睛頓時升起星光,剛剛還是如臨大敵的苦瓜臉頓時佈滿喜色,好似壓在肩上的千斤石頭忽然卸下。
他激動的看著年綰綰,彷彿看見了救世主:“謝謝掌櫃謝謝掌櫃!”
鬼知道天字房那位脾氣差到何等地步,除此之外還得受著被那把青劍威脅的煎熬。
年綰綰一笑,看著雜役瘋狂加快的步伐,心裡頓時瞭然。
天字房是客棧最好的房間,一共就兩間,其中一間還是年綰綰的屋子。想住天字號房,全憑她的心情。
來到他的屋子,年綰綰抬手正準備叩響房門,忽然想到了什麼,白皙修長的手停在半空。她嘴角閃過一絲玩味,突然將門一推,走了進去。
古色古香的擺設、內斂沉沉的香薰、高雅精美的壁畫和.....
裸著上身的美男!
年綰綰沒想到會瞧見此等美豔場面,僵直愣在原地。
沈戎白皙的臉簡直要黑出墨汁,他將上衣一披,惡惡狠狠的越過她將房門一關,眼中滿是戾氣。
“年掌櫃進屋都是不敲門的?”
年綰綰回過神,將食盒放到桌上,嬉皮笑臉的說:“要是敲了門我還能看到這種場面嗎?”
“......”
“話說回來,沈大人的身子著實不錯。”年綰綰腰肢一扭便慵懶的坐在椅子上,臉上居然還有些意猶未盡。
“舉止輕浮,不識大體。”沈戎的言語間帶上了些咬牙切齒的味道。
年綰綰也不惱,嫣然一笑:“多謝誇獎。”
沈戎氣得無話可說,板著臉請她離開。
“好啊。”
正當沈戎還在懷疑她這次怎麼如此聽話的時候,只見年綰綰慢慢悠悠起身,“哎呀”一聲,便往他的身上倒。
沈戎想避開之際,年綰綰已經死死抱住他的腰,“哎呀,差點就摔倒了。”
聲音如水蛇般酥軟撩人,彷彿要鑽進心口裡。
沈戎咬緊牙關,“你給我讓開。”
年綰綰見好就收,離開之際還不忘狠狠的摸了他一把,“多謝官人。”
一雙攝人心魄的桃花眼熠熠閃爍,正牢牢盯著沈戎。
沈戎深吸了口氣,黑著臉將她趕出了房間。
年綰綰走之前用她那雙惑人的眼睛給他拋了個媚眼,“官人若閒來無事,隨時可以來找小女子一敘。”
“......”
叄
年綰綰是個十分煩人的女子,沈戎已經忘了他是第幾次這樣感嘆。
他來客棧一月有餘,日日能見著年綰綰。為了防止她再次對他伸出“魔爪”,沈戎破例去樓下用飯。
原以為能避開這個討厭的女人,沒想到遇見她的次數不減反增,活像個追債的。
沈戎撫額,抬眼瞥見那個嫋娜的紅色身影伴隨著一陣鈴鐺聲,正緩緩向自己靠近,沈戎熟練的抽出一雙木筷,放到對面。
“早上好。”年綰綰笑容淺淺。
沈戎懶得理她,獨自用飯。
年綰綰環視了四周,“今日生意不錯。”
沈戎一言不發。
年綰綰繼續唸叨:“近日廚子阿蠻跟我說想做些新菜式,讓我嚐嚐鮮,隨後便做了個很特別的餅,味道與北夷的菜式甚是相似,讓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家鄉......”
“食不言。”
年綰綰一頓,眼裡閃過了一絲異樣的情緒。
隨後她驟然一笑,微彎的眉眼染上魅色,委屈巴巴的道:“官人真是不解風情。”
年綰綰一語罷,竟聽話的不再多言。
耳邊是旁人碗筷相碰、觥籌交錯的喧鬧之聲,唯獨他們這一桌,安靜得有些詭異。
沈戎心生煩躁,安靜的年綰綰竟然讓他感到了些許不習慣。
過了許久,沈戎悶悶的開口:“你腳踝上的鈴鐺很是別緻。”
年綰綰一愣,眼睛閃過蒼茫,彷彿在回想遙遠的過去。
她嘴角輕勾,苦笑一聲,直直盯著沈戎說道:“一個很重要的人送給我的,是他親自給我係上的。”
沈戎聽到這,心裡升起一股莫名的不悅。
飯局再次陷入安靜,直至結束。
陽光穿過窗欞洋洋灑灑的氤氳進來,照得客棧暖洋洋。四方客棧位於長安城外的一片竹林旁,遠離長安的世俗喧鬧,只餘寧靜。
空中的塵埃在陽光下肆意舞動,化為柔指纏繞在沈戎骨節分明的手指上。沈戎盯著手掌靜靜發呆。
他有些煩躁,自來到這裡後,熟悉之感愈來愈強,尤其是年綰綰那雙攝人心魂的眸子。腦袋忽然傳來一陣絞痛,他伸出手拍了兩下,靜待痛感過去。
“篤篤篤”
房門傳來敲門聲。
沈戎恢復了一貫的冷靜,起身去開門。
只見一個鳥籠忽然在他的瞳孔前放大,一隻金黃色的毛球撲騰起來,發出陣陣“嘰嘰喳喳”的聲音。
鳥籠背後探出一個絕美的面龐,不是年綰綰是誰?
她笑得妖媚,朱唇微勾:“它叫小七,你幫我養幾日。”
沈戎皺著眉,很是不悅,這嘰嘰喳喳的小東西簡直跟年綰綰一個樣。一個他都受不了,現在居然又來一個?
還未等他反應過來,鳥籠已經待在他懷裡,眼前只餘年綰綰的紅衣背影。
塞鳥籠、逃跑,一系列動作做得行雲流水,完全不給他拒絕的機會。
沈戎黑著臉把黃鶯拿進了屋子。
六月的仲夏夜充盈著蟬鳴,偶爾飛過幾只螢火蟲,閃閃發光之間好似星辰降臨。潔白的皎月彎成鐮刀,散發著清冽的白光。
靜默的仲夏夜,最適合賞月飲酒。
於是乎,年綰綰軟磨硬泡了許久,終於將沈戎連哄帶騙的拐到了客棧屋頂。
二人並排而坐,玄色錦衣與紅色煙裙相纏相繞,在月光的照拂下攜上了些曖昧。
年綰綰將一壺酒塞到沈戎的手裡,“喝。”
月光為女子披上了一件柔軟的紗衣,妖媚之間又攜著溫柔,眉眼之間顯著江湖俠氣。沈戎看了她一眼,接過酒,仰頭喝了一口。
“我等了一個人兩年。”
沈戎一頓,心裡又升起莫名的燥火。
年綰綰話語一轉,對著他拋了個媚眼,嬌媚的說道:“但現在遇到了官人,奴不想等那個人了,官人就收了奴家吧。”
沈戎不悅的答:“我絕不會喜歡你這樣輕浮風塵的女子。”
年綰綰一愣,眼中閃過落寞。
隨後故作輕鬆的飲了口酒:“大人若是喜歡溫柔賢德的女子,奴家也是可以演的。”
沈戎再次冷漠的打斷她:“只要是你,我都不喜歡。”
耳邊傳來女子的輕笑,再無它言。
肆
沈戎來四方客棧已經兩月有餘,聽聞長安城近日可謂黑雲壓城、風雨將至。
皇帝病入膏肓,駕崩之日近在咫尺。
太子遠在邊疆,羽翼皆無,四皇子登基可謂輕而易舉。
今夜客棧十分熱鬧,臨近子時,仍然燈火通明,人聲鼎沸。
一群男子圍著年綰綰,觥籌交錯間,年綰綰那張禍國殃民的臉揚著笑意,她的臉頰浮著微微淡紅,眼裡卻清明萬分。
“幾月不見,綰綰愈發動人。”為首的男子半闔眼眸,沉迷的看著紅衣女子,不老實的手攬住她的腰。
年綰綰不經意的避了避,笑魘更甚:“趙大人謬讚。”
男子大笑幾聲,又給她斟滿了酒。
周圍的人齊齊鬨笑,爭先恐後的給年綰綰敬酒。
年綰綰笑容淺淺,一一飲下。
酒過三旬,眾人依舊興意闌珊。為首的男子似是不小心拂過年綰綰的香肩,白皙的左肩便暴露在眾人眼前。
年綰綰的眸子頓時冷了下來。
她收斂起眼中的寒意,笑著拂起紗衣,耳邊突然傳來男子的慘叫。
沈戎黑著臉,眼裡的寒氣似乎比一月寒潭還冷上幾分。他居高臨下的擰過男子的手腕,臉上滿是戾氣。
他隨後將腳一踹,男子便狼狽的倒在地下。
年綰綰愣了,其他人也愣了。
這這這不是那個四皇子下通緝令抓捕的沈戎嗎???
年綰綰轉了個頭,拉起沈戎的手就往後門跑,“小二!多叫幾個人攔住他們!”
身後傳來激烈的打鬥聲。
夜幕之下,明鏡般的月亮懸掛在天空之上,把清如流水的光輝傾瀉到廣闊的竹林,夜風輕拂,便傳來沙沙之聲。
“你怎麼出來了?”年綰綰喘著粗氣,“你不知道他誰?”
“知道。”
四皇子的黨羽,他的死對頭,戶部左侍郎趙擴。
年綰綰無奈:“那你還出來?”
沈戎撇過頭,悶悶的答:“吵。”
“......”
四周寂靜,只剩蟬聲。
“哎,反正太子也倒臺了,要不你就跟我混吧。”年綰綰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道。
沈戎不答。
“你娶了我,不僅能獲得大美人一位還白送一家客棧,穩賺不虧。”月色下的年綰綰笑容嬌媚。
“我說過......”
“不就是大家閨秀麼,我也可以嘗試嘗試這種風格。”年綰綰打斷他。
沈戎語塞。
過了許久,他轉身向客棧走去,“我不會喜歡你的。”
年綰綰苦笑著看著他漸行漸遠的身影,腳踝的銀鈴“叮鈴鈴”的迴響在寬闊的竹林之中。
寂寥又孤獨。
三日後的一夜,狂風暴雨再次降臨。
天空黑得像塊沉重的墨硯,一道電光劃破天際,發出驚鳴,隨著狂風吹過,雨簾從後山漫過來,頃刻之間就把天地變成白茫茫的一片。
閃電猶如鬼魅,年綰綰站在窗欞前,看著沈戎埋進雨夜之中,身影逐漸模糊。
他走了,沒留下一字一句。
身旁的黃鶯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年綰綰的雙眸逐漸模糊,眼角似有淚光微閃,那個離去的背影,跟兩年前一模一樣。
伍
兩年前,北夷。
北夷位於邊疆之地,有醉人的暮靄,沉沉的星光,低吼的蒼鷹,四溢的煙火。
“阿爹!那裡有個人!”
十八歲的年綰綰一襲紅衣騎在馬背上,一陣風恣意的吹過,吹得她衣袂飄然,她正好奇的往前方瞧。
年拓騎著馬緩緩走到年綰綰身旁,摸了把鬍子,“近日倭寇橫行,萬一......”
年拓話語一頓,他的那個寶貝女兒已經跑到那個男子身旁。
他嘆了口氣,默默上前。
四月正是草長鶯飛之際,眼前男子身受重傷,華貴的玄衣被大片的血漬所染。他俊朗的面龐十分慘白,正奄奄一息的躺在河水畔。
“阿爹......”
年拓蒼老的面容上滿是警惕,“綰綰,此人來歷不明,若他是倭寇,恐遭殺身之禍。”
年綰綰清澈的眼眸靈活一轉,懇切的求道:“他的配劍上寫的漢字,阿爹,我們救救他。”
年拓終是拗不過,板著臉點了點頭。
年拓是北夷有名的馬商,他的內人在幾年前便早逝,他獨自帶著年綰綰長居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中。
沈戎醒來看到的,便是一雙清澈靈動的桃花眼,水波瀲灩間存著天生的魅色。
她嬌俏的對他一笑:“你叫什麼名字?”
沈戎皺著眉,淡漠的眸子被她的熱烈融化了幾分,他幾乎鬼使神差的答:“沈......”
“嗯?”年綰綰捧著臉看他。
“沈七”
“我叫年綰綰,你叫我綰綰即可。”
沈戎嘴角微勾,緊繃的弦也在不自覺間鬆了下來,“多謝搭救。”
“不客氣。”
天蒼蒼,野茫茫,草原為大地鋪上地毯,牧歸的駿馬從遠方而來,在碧綠的地毯上鑲上花朵。豪放的風吹盡滄桑,只留清明。
沈戎剛來的時候戒備極重,年綰綰十分清楚。
於是她熱情的拉著他四處轉悠,拉著他在餘暉織成的晚霞下策馬狂奔,在靜夜裡燃起篝火,喝著烈酒,直到微微醺醉。
沈戎臉上的笑意越來越多,他開始跟年綰綰講長安的繁華,並笑著跟她說,“綰綰若來長安,我必好生招待。”
平靜的日子總有驚喜降臨。二人在某次馴馬時撿到了一隻受傷的幼鶯,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堪堪將黃鶯救回。
“起個名字。”沈戎說。
“小七。”
“嗯?叫我?”
“我說它叫小七。”
沈戎使壞的攬住年綰綰,威脅道:“還是叫綰綰妥當。”
“我不,就叫小七。”
“......”
“小七,小七,小七”
“好吧。”
北夷的日子總是平淡而恬靜,綿遠悠長,並無憂慮。
“綰綰,北夷的夜空是可以看到星星的。”沈戎跟年綰綰說。
“長安看不到嗎?”
“看不到。”他溫柔的笑著。
“小七,我可以把星星抓下來哦。”
“嗯?”
年綰綰轉著狡黠的眸子,伸出手往空中一抓,“你過來。”
沈戎配合的靠近她籠著的雙手,她慢慢開啟,一隻微閃的螢火蟲攜帶著流螢般的微光在他身旁轉了一圈又飛向遠方。
沈戎一愣,隨後低低笑了起來。
“既然你送了我一份禮物,我也應禮尚往。”
沈戎拿起身旁的青劍,將系在劍尾的銀鈴解了下來。
“沈戎?”年綰綰看著刻在劍鞘上的字,疑惑的問道。
沈戎一怔,笑著說:“我是沈戎,也是小七。”
精緻的銀鈴在月光下閃著柔柔的白光,紅色絲線穿過鈴鐺,猶如鮮豔的紅色花芯。
沈戎低下頭,溫柔的將鈴鐺系在年綰綰的腳踝。
“叮鈴鈴叮鈴鈴”
清脆的鈴鐺在夜裡反覆迴響。
陸
沈戎離開的那日,是個暮靄沉沉的傍晚。
他緊緊盯著年綰綰,眼中滿是複雜神色:“綰綰,等我回來找你。”
蒼穹的蒼鷹低吼了一聲,年綰綰哭得流淚滿面,親自看著他的背影愈走愈遠。
沈戎走後沒多久她的阿爹慘遭族人算計,他們霸佔了年拓的戰馬,年拓氣急攻心,永遠沉睡在一望無際的北夷。
頃夜之間年綰綰一無所有,手裡只餘年拓為她留下的一筆銀子。
按小七所言,長安暮雨,處處新澤,宮苑傍山明,雲林帶天碧。華美之景令她心之嚮往,她決定去長安。
長安有他。
年綰綰一路南下,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吃了不少苦。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年綰綰看著眼前之景,想到了沈戎曾經念過的詩句。這裡,便是長安了吧。
她問遍行人,無人識得沈七。
終於,當她問出沈戎的時候,方才有人告訴她那是一品監察史,朝廷的權臣。
那日陽光刺眼,她站在沈府外躊躇了許久,均不敢向前一步。
正當她發愣糾結之際,一架華貴的馬車停在她的身旁,下人熟練的撩起馬車的錦簾,一雙玄色金絲鑲邊的錦靴優雅的落地。
精雕細琢的五官上一雙眸子疏遠而淡漠的撇了她一眼,徑直入府。
“小七!”年綰綰急急一喊,驚得腳踝的鈴鐺泠泠作響。
沈戎腳步一頓,抬眸向她看去,眼裡全然陌生。
“打發走。”
他低沉冷漠的出聲,再不看她。
年綰綰手足無措的站在原地愣神,腦袋一片空白,直到沈府的硃紅大門重重關閉。她的眼角還是不爭氣的揚起淚光,滿是委屈。
後來年綰綰又來過幾次,每次均以慘淡的結尾收場,刺得她早已麻木。
“監察史大人在前段日子頭部受過傷,變得陰晴不定,姑娘還是莫要再來了。”沈府一位好心的掃地婆婆跟她說道。
她苦笑著說:“不來了,再也不來了。”
年綰綰用念拓留的銀子開了家四方客棧,安定於長安城外的竹林旁。
臨春夏秋冬,看日升月落,識江湖俠客。
一眼萬年,往事隨風而散。
年綰綰回過神,燭火微微顫抖,眼前仍是電閃雷鳴,傾盆大雨,沈戎早已走遠。
“掌櫃的。”
翠雲將衣服蓋在年綰綰身上,“擔心著涼。”
年綰綰莞爾一笑,“聽說皇帝駕崩了?”
“是的,長安城都亂了套。四皇子登基之際突然殺出個太子,兩方正對峙得激烈。”
年綰綰沉默不語。
“掌櫃的,您為何不驚訝?”
“自他來到這的那一刻起,我便了然他們不會就此放棄奪權。暗自謀劃,靜待時機,一朝反撲,一擊斃命。”
天邊又掠過一道白光。
“他們勝券在握。”
柒
天元四十七五年,皇帝駕崩,諡號長德。
四皇子與太子的奪嫡以太子手刃四皇子而落下帷幕,太子登基為帝,改國號為天啟。
一間茶香氤氳的亭子裡,新皇優雅的執起茶盞,往白玉瓷杯裡斟了杯茶,茶香四溢,水霧朦朧,他順勢將杯盞往玄衣男子的方向一推。
沈戎斜躺在軟榻之上,有些愣神。
“阿戎在想什麼”
沈戎回過神,揉了揉額頭,心裡有些煩躁。
皇帝輕笑,“聽聞這兩個月你與一女子交往甚密。”
沈戎腦海裡又情不自禁浮現出透紅的紗裙、妖媚的笑魘,他鬱躁的將茶一飲而盡。
“若你娶了她,朕定當給她封個誥命夫人。”皇帝打趣他。
沈戎彆扭的轉過頭。
“哦對了,朕的那個四弟之前給你下了蠱毒,導致你忘了些事情。”皇帝將精緻的錦盒推到他的面前,“朕親自為你取了解藥。”
沈戎一愣。
皇帝懶懶的起身,金黃龍袍漸漸消失在眼前。
“快些服用罷,朕擔心你服晚了,辜負了一場深情。”
四方客棧熙熙攘攘,小二靈活的敲著算盤,頭也不抬的問:“客官要住店嗎?”
焦慮又急切的嗓音還微微喘著氣,“綰綰呢?”
小二一抬頭,頓時腿腳軟了八分,又是這個瘟神!
他深吸了口氣,掩住眼裡的害怕,故作鎮定的說:“掌櫃的已經換人了,綰綰姐五日前就走了。”
沈戎眼眶充滿血絲,不客氣的上前抓住他的衣領,修長的手微微顫抖,“她去哪兒了?”
小二慌得找不著北,心驚膽戰的道:“掌櫃沒說,聽她說是要回家收拾她的族人,拿回她的東西。”
沈戎滿是戾氣,眼裡的寒幾乎將小二凍成冰塊。
“掌...掌櫃還給您留了話。”
沈戎將手一鬆,急切的問:“留了什麼?”
“掌櫃說,待她找到良人,會親自.....給您發喜帖,邀你飲喜酒一杯.....”
小二看著他越發陰沉的臉,聲音越說越小,細若蚊聲。
“呵,北夷是麼,就算把整個北夷翻過來我也要把她找到。”
尾記
一年後。
馬背上的女子手拿一壺清酒,勁風吹得紅衣飄飄揚揚,好似草原上翩翩起舞的蝴蝶,鈴鐺微微作響,清脆而悠遠。她攝人心魄的雙眸染上些許迷離,正低頭看著前方的男子。
“綰綰,我來接你回家。”
文/十小姐 純分享,侵必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