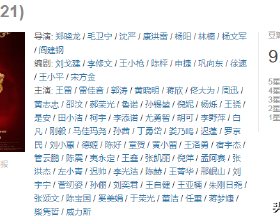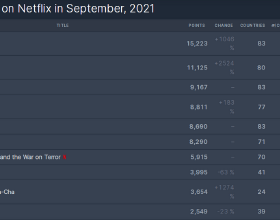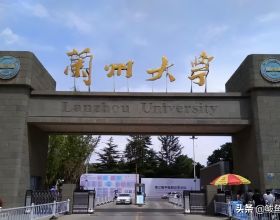第二天就有十幾只貓聚集到南園裡,一齊用爪子在地裡挖著什麼,其中也有咱家的貓,而且看樣子還是它們的首領。它們從早上開始,一直幹到將近中午,咱家的貓“喵嗚”一聲令下,貓們便散開了,各回各的家。到下午大約四點鐘起,它們準時集合,又接著幹開了,一直到暮色降臨為止。一連幾天,這群貓都在幹著這項工作。幾天過去,園子裡便多了一個長方形的坑。我們都很納悶,這些貓究竟在搞啥名堂?
直到坑有一米多深時這群貓才停止了這項令人莫名其妙的工作。這一天,家裡又賣掉了幾棵樹,買主領著六七個小夥子來伐樹,他們商議了一陣便兵分兩路,操起斧頭,木鋸幹了起來,就在這時我看到咱家的貓從東屋出來,嘴裡還含著本書,遠遠望去,單憑封面我就知道那是一本我剛買的《王朔小說精選》,貓走到靠著窗戶的電視天線杆子下面停了下來,嘴裡嗚嗚叫著,接著便用爪子和嘴撕起書來,我急忙趕過去,剛走到貓跟前,前邊園子西南角上的大楊樹被伐倒了,不偏不倚,正好朝我站著的那個方位倒了下去。當時我正面對著貓,對背後所發生的一切毫無察覺,結果呢,可想而知——樹砸在了牆上,樹梢被折斷後又繼續往下落,準確無誤地砸在我的頭上,我慘叫一聲,只來得及看見幾顆星星在我的眼前閃爍,旋即便轉入一種暫時性的樂天知命的安詳......當我又回到現實當中時已經躺在了家裡的床上,自下頜至頭上纏了一層厚厚的紗布,咱爸和買主正坐在桌子跟前商量著什麼,見我醒來便問:“頭還疼嗎?”,被他們這一提醒,我立刻感到頭疼欲裂,連忙舒服地呻吟著並齜牙咧嘴輔以痛苦的表情算是代替了回答。
原來,我被樹砸暈後,眾人慌作一團,買主急忙將我背到了村裡的衛生所廣瑞那(由咱爸帶路),到達衛生所時血已流了我一臉,好不威風!駭得廣瑞趕快採取搶救措施,剪髮,清洗,消毒,縫針,掛吊針一氣呵成,然後又把我揹回家,最後我就醒過來了。
接下來,我在廣瑞那掛了三天吊針,並換了幾天的藥,一個禮拜後拆了線,那位倒黴的買主還專程提著東西看了我一次,他買的蛋糕和罐頭被我幾天的功夫就消滅個乾乾淨淨,最後我用暖壺裡的開水將罐頭瓶涮了涮,將略帶點甜味的涮瓶子的水喝進了肚子,然後看著已經空了的蛋糕包裝盒,悵然若失地發了一會呆,尋思著這人真他孃的小氣,我的身體還沒補過來呢,東西已經沒了,唉!我真是好生命苦!......我雖然遭了些罪,但總歸是有驚無險,尤其幸運的是,大腦也沒受到任何損傷,廣瑞還得意地宣稱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手術。
按說一切都應該萬事大吉了,可不知怎的,我的內心深處竟隱隱生出一絲不安,常情不自禁地回憶起那天的情形,總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可具體哪兒不對勁我也說不上來。
而且自那件事後,貓也嚇得不知躲哪去了,好幾天都沒露面。直到有一天晚上咱爸到東屋小煤房裡拿煤時才發現它正臥在煤堆上,於是便將它手到擒來又拎回了我們住的房子。貓雖然又回來了,但不知為什麼它的性情從此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常常在一個僻靜的角落一動不動地臥上半天,即便我逗它也是愛答不理的,只泠泠地瞟了我幾眼便又閉目養起神來,而且人們吃飯時,它也不湊過去要食吃了。“這貓咋回事?不如以前歡了?”爸媽奇怪道。而我內心的不安則越來越強烈,我模模糊糊地感覺到這種不安也許就源自於這隻貓!這隻詭秘異常的貓!
這天,村裡的一個老鄉家裡辦理喪事,爸媽都過去幫忙去了,家裡就只剩下我一個人。晚上,我吃過飯後,就打開了電視繼續看電視連續劇《慾望》,趁著一集剛演完中間插進廣告的空兒我出去解了個大便,便後返回途中經過那個貓挖好的坑時我停了下來,仔細揣摩了一會,突然驚恐地發現這個坑似乎剛好適合我。念及於此,我跳了下去拿自己的軀體一驗證,不大不小,正好!頓時我身上的毛髮根根豎起,與此同時,在坑沿的四周又出現了那十幾只貓,齊齊地拿冒著綠光的眼睛盯著我,我大吼一聲,翻身站起,接著雙手撐在坑沿,借力一躍,跳出坑來,我順手抄起一根棍子舞得呼呼生風,一邊嘶聲喊道:“你們想幹啥?滾!滾!”,貓們一個個跳躍躲避,張牙舞爪,併發出“哇哇”叫春般的聲音。我一鼓作氣衝出重圍,衝出園子,衝進屋裡,家裡的那隻花貓正坐在窗臺上往外“喵嗚”叫了幾聲,然後迴轉身來面對著我。我倚在門框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心怦怦地直跳,一眼瞥見花貓正用綠幽幽的目光刺著我,便一步竄到案板跟前掂起了菜刀,獰笑著一步步地逼向花貓。就在這時門“吱扭”一聲被推開,咱爸回來了,他見我拎著菜刀,驚問道:“你要幹啥?”“噢!不幹啥,削個蘋果”。說著我便順手從碗櫃的第二層拿了一個蘋果削起皮來。“我也吃一個蘋果”爸爸說著也拿了一個蘋果邊吃便進到裡間坐在床上看起電視來。貓騰地跳下,臥在爸爸旁邊打起了呼嚕,爸爸用手撫摸著它說:“這貓現在又歡了,它又開始打呼嚕了。”
我之所以沒敢將實情告訴家裡人,並巧加掩飾,是因為我感覺到這貓僅僅是衝著我來的,自己的事情自己了斷,我可不想在家裡造成更大範圍的恐慌。
電視演完時,咱媽也回來了,說了會幫忙的事,我們便各自熄燈就寢了,貓還像往常一樣往我被窩裡鑽,被我一巴掌扇到了一邊,它便怏怏地臥在被子上面進入了夢鄉,我先還是惴惴,慢慢地倦意湧上,竟不知不覺地睡著了。半夜裡,我突然被驚醒了,覺得被子上有什麼東西在刺溜溜地動彈,忙起身開了電燈,我心驚膽顫地看到貓正在床上飛快地旋轉著,轉速越來越快,以致於只看到一個黑白色的圓環,最後貓“哇——唔——!”淒厲地長叫一聲,停了下來,整個身子也癱成了一團泥。
裡間的爸媽被驚醒了,連聲問道:“貓咋了?”“不知道咋回事,這貓好像是得了神經病,它發狂了!”
媽媽的聲音又從裡間傳來:“是不是吃了老鼠藥了,趕快拿味精喂喂它還能餵過來。”
“我覺得不像是吃了老鼠藥,它又沒吐白沫”,我答道,同時仔細地扒拉著貓身上的毛試圖找到傷痕什麼的,結果在它的脊背上赫然見到一塊大小約為5x5平方毫米的花紋,我仔細辨認了一番這個花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整個身子也顫慄起來,因為那竟然是一幅影象,而影象的內容則是我記憶深處的某個片段!——一個人正舉著一把斧頭往一隻狸貓身上砍去,那人身後一隻母貓悲憤交加地朝著大狸貓嘶叫著,母貓身邊有一隻用柳條編織的框子,框子斜倒在一邊,墊在裡邊的麥草都撒了出來,麥草上鮮血淋淋,零零散散地躺著幾隻小貓崽子的屍體,有兩個屍體的頭也不見了。
這個情形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當年俺家有一隻母貓下了一窩貓崽子,沒想到卻在一天深夜被一隻外來的大狸貓尋上門來,大狸貓把剛出生不久的小貓全部咬死,接著又試圖非禮母貓,母貓的慘叫聲驚醒了我和俺三叔,俺三叔見到眼前的慘狀勃然大怒,抄起斧頭就奔著大狸貓去了,經過一番搏鬥,把大狸貓當場砍死,為母貓報了血海深仇。
難不成那隻死去的大狸貓,陰魂不散,轉世到了俺家,想要了解前世的恩怨?
就在這時,貓忽然抬起了頭,兩眼慢慢睜開,眼光起初略微有點畏縮、猶豫,不過隨著時光一分一秒地流逝,它的眼光變得越來越充滿自信,而且銳利。它的眼光也不再是綠幽幽的了,而是閃出水晶藍色的光芒,這種眼光,讓人聯想起一個獵人的眼光,一隻翱翔的老鷹掃視曠野、尋找獵物的眼光。
一股涼颼颼的恐懼傳遍了我的全身,我無暇細想,一個箭步衝出房門,來到院子裡,操起了一把靠在南牆上幹農活用的鐵鍁,我突然發現那十幾只貓不知何時已經聚集到院子裡,正呼嚕呼嚕地念著貓經,於是就在這個夜晚的三更天,咱家的院子裡響起了一片誦經聲。
咱家的貓也跟著出來了,它親切地看著我,步履輕鬆地向我走來,咱家的狗被驚醒了,忠心耿耿的狗看出了事情不對,它汪汪叫著橫在了貓的跟前,擋住了它的去路,貓默默地看著狗,看著這個昔日的戰友,突然閃電般地撲向了狗,利爪穿透的地方,狗的喉嚨被撕裂了,熱呼呼的鮮血,如泉湧而出,狗連一聲都沒來得及叫出,就抽搐著倒了下去。
出手如電,迅疾無息,貓現在的身手當真猶如鬼魅!它舔了舔嘴角的狗血,抖了抖渾身的毛,仰面朝天,深深吸進清爽的空氣,體味著體內無窮的力量,大地的生機,生命的氣息,哦!這才應該是我的生活,是誰喚醒了我?
我癱倒在地,都說貓有九條命,今日始知此言不虛,只是令我搞不清的是當年被幹掉的明明是一隻狸貓,怎麼就變成了黑白花貓呢?
我哆嗦著嘴唇:”想不到十年過去了,你還是找上來了,可是當年動手殺你的是俺三叔呀!我只是在一邊觀戰而已,你要找也不應該找我,冤有頭債有主,你應該去找俺三叔說道說道,敘敘舊呀!他前年就回了江蘇老家,要不,我告訴你他的確切地址,你找他聊聊去,ok?......“
那一夜,冷月如鉤,繁星點點,夜空如洗!
久勝,咱家這隻怪貓的故事我就講到這兒了,至於那隻狸貓和咱家的恩恩怨怨,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應該記得我多年前寫的一個短篇《深夜大戰》,在那部小說裡我詳詳細細地記載了咱三叔大顯神威,捕殺大狸貓的事蹟。惜乎後來那個短篇不知何時給弄丟了,時隔日久,好多細節都想不起來了,以致於我現在幾次試圖重寫這個短篇,竟是一直未能成功!不免是件憾事。
後記:各位看官,天山的雄鷹作證,我絕對不是為了保全自己,而向那隻貓畜生出賣了俺三叔,只是我這個人太實在了,實在得連一隻貓都不忍心欺騙,這個......可能我不說貓也知道當年是誰幹掉了它,我就是提醒一下它而已。俺家那隻忠誠的狗雖然犧牲了,令人欣慰的是在那件事前不久,它結識了一隻俏麗的,有著一身光滑絨毛的黑母狗,倆人,噢!不!說錯了,是倆狗日久生情,不知何時有了肌膚之親,使得那隻俏麗的母狗珠胎暗結。公狗戰死後,為了躲避貓畜生的追殺,母狗含悲忍痛,遠走他鄉,一年後,產下一窩可愛的小狗崽子,分娩那天,狗媽媽面向西方(就是俺家所在的那個方位)放聲大哭(當然嘍,狗哭起來也就是汪汪直叫):他爹,我為你下了一窩小崽子,你九泉下可以瞑目了!那窩小狗長得稍大點就各奔東西了,其中有一隻小哈巴狗異常機靈,驍勇善戰,不多時就在江湖上闖出了名頭,後來被刀聖張傲寧收服,在協助張傲寧對付大魔頭平陽候夏侯榮的多年鬥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詳情請參閱我的胡說八道體武俠鉅著《大漠刀聲》,該書由子虛烏有出版社出版。
至於俺三叔,一直沒聽說他那出過啥事,估計路途太遠,雖然知道了地址,貓還是沒能找到他,到底是一畜生,道行再深,也能耐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