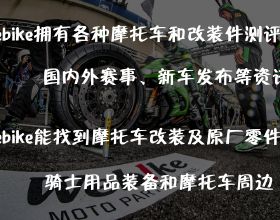今年是侯仁之先生(1911-2013)誕辰110週年。他是北京大學教授,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但人們更願意用這樣的雅號來稱呼他:“北京通”、“中國申遺第一人”。這也足以說明侯仁之先生在保護北京城歷史文化方面所做的貢獻。
侯先生是筆者的老師,他在學術上的巨大成就和貢獻已多見於著述或文集之中,這裡僅就講述侯先生鮮為人知的幾個生活片段,以表懷念。
受益終身的第一課
1955年7月,我以第一志願:經濟地理專業(後改稱“城市規劃專業”)考取了北京大學。這個專業是北大新設定的,主要是為國家經濟的發展與佈局培養專業人才和高校師資。到校報到之後,我才知道它歸地質地理系。
開學第一天,按慣例,地質地理系主任要向新同學致歡迎辭。這天早晨,我在飯廳(現在的“百年大講堂”)吃完早飯,便早早地來到地學樓101號階梯教室。
8點整,一位中等身材,身著青灰色中山裝,寬額頭,戴一副深色鏡框眼鏡的老師,走上講臺。他環顧四周後,說了一聲:“歡迎新同學!”他聲如洪鐘,渾厚有力。我們這才知道他就是我們的系主任:侯仁之先生。教室裡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
侯先生在對地質地理系略作介紹之後,便開啟了開學後的第一課:《歷史上的北京》。他從北京城的起源、城址的確定,講到了它的變遷以及在都城規劃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侯先生生動又富有激情的語言,深入淺出的內容,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聚精會神地聽著,生怕把其中的哪句話給漏了。從此,侯仁之的名字便和“北京”這個名詞一起,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堅定了我學好經濟地理專業的決心。
就在開學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侯先生又帶我們作了一次實地考察。他說:“我們學地理的既要聽好課、查閱文獻、作好筆記,也要作實踐考察,只有這樣,做學問才會是承前啟後、腳踏實地的。”
我們一行人,在28齋學生宿舍前集合。之後,侯先生帶著我們沿燕南園、勺園、西校門,再進入蔚秀園、西苑,然後沿圓明園西牆,過青龍橋到臥佛寺、櫻桃溝……侯先生邊走邊講,我們受益良多。正是這開學後的第一課和第一次實地考察,使我非常慶幸,覺得自己報對了專業,而且我下決心要為它奉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燕大的長跑冠軍
侯先生平時講課、作報告時,儀態瀟灑大方,而且說話非常有激情,令人百聽不厭。在一年的新年聯歡會上,我們還被侯先生一曲音色深沉洪亮的《伏爾加船伕曲》折服。侯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的魄力,不僅得益於他做學問的厚積薄發,更得益於他長年堅持體育鍛煉。
瞭解侯先生的北大師生都知道,他長年堅持環未名湖跑步,後來我才知道他堅持長跑背後的淵源。
1911年,侯仁之出生在河北棗強縣的肖張鎮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18年雖入讀小學,但卻因體弱多病,幾次輟學。1926年,他進入德州博文中學讀書。當時的博文中學各方面的條件都不錯,學生的體育活動尤其出色——幾乎每個班都有籃球隊,班與班之間常有比賽。對此,侯仁之羨慕不已。有一天,他壯著膽子去找班裡的籃球隊長說想參加籃球隊。可當時的侯仁之,個子不太高,身體也不那麼健碩,與那些人高馬大的隊員站在一起,顯得不那麼相稱。他請求了多次,可人家就是不同意。一氣之下,侯仁之就練起了長跑。就這樣,侯仁之堅持跑了一個冬天。
轉過年來,學校要舉行春季運動會,班上有同學鼓勵他參加1500米比賽。侯仁之報了名。比賽時,侯仁之居然得了1500米的冠軍,這讓侯仁之非常激動,也為他後來堅持鍛鍊打下了基礎。
1932年,侯仁之從通州的潞河中學畢業後,參加了燕京大學的特別考試,如願獲得4年的獎學金,進入該校歷史系學習。從此,侯仁之便與燕園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後,他不僅是燕京大學多屆運動會的長跑冠軍,而且還保持著燕大5000米長跑的紀錄,直到1954年才被打破。1955年5月,在北京大學春季運動會上,侯仁之先生仍獲得40歲以上老年組3000米冠軍。

1955年,北大春季運動會上侯仁之先生獲老年組(含40歲以上)3000米冠軍。
侯先生還經常教導我們:“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這與他的求學經歷有重要關係。在燕大學習期間,對侯仁之影響最大的是兩位先生:顧頡剛和洪業(煨蓮)。
顧頡剛是燕大歷史系教授,當時侯仁之報考燕大,就是慕顧頡剛先生之名。在燕大,侯仁之第一次接觸到了我國古代的地理名著以及對現代地理問題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還得到紮實的實地考察的學術訓練。
洪業先生對侯仁之最大的影響是把他引上治學之路:正是洪業先生,在侯仁之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提出了“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的至理名言,使原本要去哈佛大學的侯仁之轉而去了英國利物浦,並投奔在歷史地理學家達比門下。
1949年9月27日,侯仁之攜帶著已透過答辯,並因此而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北平歷史地理》,回到了北京。
老師給我寄來稿費
畢業後,因為工作的關係,我與侯先生有了更多交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為迎接“百花齊放,群芳爭妍”的科學春天的到來,侯仁之先生決定把自己二十多年來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作一個回顧,把自己發表的研究成果,作一番梳理和總結。但是,他正忙於去西北作沙漠歷史地理的考察,無暇顧及梳理工作,他便把梳理成果的任務,委託給了《光明日報》的金濤同志。約40萬字的書稿是有了,但書中需要70多幅插圖,一時無人繪製。我當時正從事《北京地圖冊》的編繪工作,得知此事,便自告奮勇地向侯師提出,由我承擔繪製書中插圖的工作。一來覺得老師遇到了困難,作為學生理應幫忙排解;二來,書中較為複雜的地圖,萬一我繪製不了,還可以求助畢業於武漢測繪學院的同事。對於我的請求,侯先生高興地答應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繪製插圖的工作完成。一天晚上,我騎車將繪製的圖稿呈送給住在燕南園的侯先生。不巧,在騎車回家的路上,趕上了瓢潑大雨。儘管臨行時,因為天色不好,侯先生給了我一件雨衣,但從北大到我家畢竟有數十里的路程,路上我還是被澆得如落湯雞一般。第二天一早,侯先生的小兒子侯凡興便到市規劃局辦公室找我。見到我後,非常關切地問道:“昨天雨下得那麼大,你挨淋了吧,還好嗎?父親讓我來看看你……”幾句話說得我心裡熱乎乎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好:“謝謝侯先生,謝謝侯先生!”
197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地理的理論與實踐》面世,我們都為老師感到由衷的高興。不久,侯先生給我寄來樣書,還寄來了繪製插圖的稿費。這是我壓根兒都不曾想的事兒。翻開書,侯先生特意在序言中感謝了我。作為師長,他如此愛惜後輩,讓我打心底感到敬佩。
“中國申遺第一人”
1979年夏,美國匹茲堡大學訪華團一行17人來到北京大學,並與有關專業的教授進行座談,氣氛十分融洽。席間訪華團的一位負責人用非常婉轉的話語表達了一個願望。他說,北京的確是一座舉世聞名、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現在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氣象,舊日的城牆也拆除了,想來一定有不少城磚留下來,能不能由北京大學贈送一塊給匹茲堡大學,作為兩校之間文化往來的一個紀念?
北京大學專門為此寫了報告,並得到上級的批准。經過一番努力,有關部門為學校找到了兩塊磚體相對完整,且儲存有燒製年代和窯戶名稱的城磚,還特意請琉璃廠的師傅製作了禮品盒。
恰巧此時,侯先生接到了加拿大和美國幾所大學的邀請,匹茲堡大學是其中的一個,於是北大就把贈送城磚的任務交給了侯先生。在贈送儀式上,侯先生告訴匹茲堡大學訪華團,這兩方城磚上刻著的“大明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也就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的第65年。說到這,全場掌聲雷動。匹茲堡大學在後來的感謝信中這樣寫道:
北京城具有歷史性的城磚,作為北京大學富有意義的禮品,已在大學董事會上第一次展出。今後還要儘早裝置妥當公開陳列,供眾賞覽。這兩塊和美國曆史同樣古老的城磚,正是我們兩所大學之間持久的文化聯絡和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友誼的一個象徵。
後來,這兩方北京城磚,連同文字說明,陳列在匹茲堡大學“東方圖書部”前面的兩個大玻璃櫥窗中。

左為贈送給匹茲堡大學的城磚,右為侯仁之先生再訪匹茲堡大學時與城磚合影
前不久,在福建泉州召開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將泉州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我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總數達到56項。值得一提的是,侯仁之先生是中國最早提出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教授。
1984年,侯先生應邀去美國華盛頓康乃爾大學講學,就在與外國的同行學者的接觸交流中,他第一次瞭解到,在國際上有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世界遺產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專家還問侯先生,中國歷史悠久,有無數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和風景名勝地,為什麼不參加這個公約,讓世界更多地瞭解中國。這給了侯仁之極大的震動。
回國之後,侯先生便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並邀請了國家文物局古建專家組組長羅哲文、城鄉部規劃大師鄭孝燮以及中國科學“人與生物圈”負責人陽含熙,共同簽名申請中國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這就是後來的“第六屆全國政協提案第663號”。方案引起高度重視,1985年12月12日,中國成為該公約締約國之一,並於1987年開啟中國的申遺工作。1987年12月,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1屆全體會議上,故宮、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泰山、長城、秦始皇陵(含兵馬俑)以及敦煌莫高窟等六處文化和自然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侯仁之作為“中國申遺第一人”而被後人牢牢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