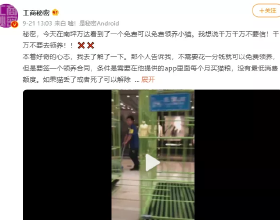《秦漢刑罰制度研究》(商務印書館2021年9月出版),既是日本學者富谷至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該書以出土秦漢簡牘結合歷史文獻資料研究秦漢的刑罰制度,選材嚴謹,持論精準,是學習研究法制史及秦漢史學人的必讀之作。
首先,作者認為,“秦代確立的是一種理論完備的刑罰體系”“漢代雖然從形式和內容上沿襲了秦刑罰,但最終還是經過脫胎換骨形成了自己的刑罰體系”。這不僅承認了傳統的“漢承秦制”說法,而且進一步肯定了漢代系統地發展了秦之法制大業。陳寅恪先生說: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於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漢承秦業,其官制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採入法典。富谷至在秦漢刑罰制度研究問題上建立起來的理論框架無疑是站得住腳的。
其次,作者系統地介紹了秦代刑罰中的刑、耐、黥、完、罪的概念,指出“刑”和“刑罪”是肉刑的意思;秦簡中的“耐”是不施肉刑,但要剃去顏毛;“黥”是指施以刺青的肉刑;“完”則不施肉刑髡鬄,保持顏面完整的刑罰,但還需服勞役刑。對“罪”字的解釋,則更有新意。作者指出,秦簡中的“罪”(辠)除了犯罪的意思外,還有刑罰的意思,因而至少在秦律中,還沒有把罪與罰加以區分的意識。秦代的刑罰體系,分為肉刑、勞役刑、貲刑(財產刑)、贖刑(另一種財產刑)和死刑。秦代的肉刑並不是單獨使用的,是與勞役刑合併使用的。勞役刑既不是無期徒刑,也不是有期徒刑,而是不定期刑。一般是透過“赦”免除勞役處罰。漢初沿用秦制,仍是肉刑與勞役刑並用,刑期不定。文帝的刑制改革後,廢除了肉刑,將勞役刑匯入刑期,確立了髡鉗城旦(五年)、完城旦(四年)、鬼薪白粲(三年)、隸臣妾(三年)和司寇(二年)等刑罰體系,從而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徒刑制度。在論述這個問題過程中,富谷至還就隸臣妾問題對前人研究的成果作了系統的梳理,如用新史料否定了沈家本的隸臣妾之名“是秦所無,漢增之也”的說法,用秦簡中的材料證明隸臣妾是一種對罪犯貶低身份從事勞作的刑罰的結論,並指出:“漢代,在隸臣妾納入勞役刑範疇後,它就不再附加於其他勞役刑了。”此外,富谷至還在緣坐制度方面從服制與刑罰的結合入手,考察緣坐適用範圍的變化,從而得出戶籍向服制轉化的規律,極有見地,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再者,關於財產刑制度,分為貲刑與贖刑兩種。罰貲是指犯罪後被判處繳納一定數量的罰金或勞役,其本身就是一種刑罰;贖刑是指中國古代法律規定的,犯罪人可繳納一定數量的金錢,或服一定期限的勞役而減免其罪,是對現有刑罰的易科。富谷至根據《韓非子》中提到秦國刑罰有貲甲,指出“這說明貲刑源於戰國秦”。這個說法不準確,相傳夏代即有“罰”。《路史·後記》:“夏后氏罪疑惟輕,死者千饌,中罪五百,下饌二百。罰有罪而民不輕,罰輕而貧者不致於散。故不殺不刑,罰弗及疆而天下治。”夏代史料雖不可盡信,但西周《呂刑》中有“罪疑惟罰”的原則,即對犯罪事實不明、證據不足者,釋放時加以“罰鍰”,按五刑標準,墨疑罰百,劓疑二百,剕疑五百,宮疑六百,大辟千鍰。在出土的西周銅器的銘文中也有“罰鍰”的記載。富谷至認為,漢代的“罰金針對官吏的時候比較多”“罰金刑不是對秦代貲刑的繼承”,罰金在最初沒有被列入作為正刑的律的體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漢武帝以後,終於作為正刑的一員納入了刑罰體系。富谷至對此論述甚詳。
贖刑的使用也很久遠,《尚書》中有“金作贖刑”的記載。《國語·齊語》有管仲與齊桓公的對話,齊桓公問管仲齊國的“甲兵不足如何?”管仲說:“輕過移諸甲兵。”具體辦法是“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齊國的贖刑制度還很原始,但可以肯定是實行了的。據歷史傳說在夏代就出現了“金作贖刑”,即用財產或金錢贖罪以代刑罰。據《尚書大傳》雲:“夏后氏不刑不殺,死罪罰二千饌。”商鞅也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上古社會的所謂“贖刑”,其本質就是以“侵權行為法”處理氏族部落內相互侵犯的行為,用賠償的方式,解決傷害甚至殺人行為的責任。這可從後世少數民族的史料來解析。如唐代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其法:劫盜者二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以納死家”。金之始祖定約:“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牸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鬥。”“女真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馬十偶,是說公母各十匹;牸牛,是指母牛。這可以看出,在各民族早期的歷史中,對本部族成員的保護,不是依賴“犯罪法”,而是依賴“侵權行為法”。而以肉刑、死刑為主的刑罰,則主要適用於對外部落(族外)侵害的“報復”。
最後,與勞役刑相關的是秦漢的監獄制度。富谷至利用洛陽出土的東漢刑徒磚考據,說明:“這個獄不僅關押未決犯,也具有關押既決犯的功能。”這一結論是十分精闢的。晉張斐《律序》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太平御覽》注曰:“罪已定為徒,未定為囚。”秦漢時期的監獄,也確實存在關押已決犯在獄中勞作的制度。晉幹寶之《搜神記》記載這樣一個故事:漢武帝東遊到函谷關,有一怪物擋道,百官驚駭。東方朔讓以酒灌之,而怪物消。武帝問是為什麼?東方朔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已決犯在獄中多從事管理其他囚犯的工作,往往成為獄霸。《戰國策·燕策》:“馮幾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可見徒隸在獄中之張揚。既決犯徒系拘禁之地,或為監獄之地,或為工役勞作之所。
富谷至對秦漢刑罰制度研究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但有些具體問題還是可以討論的。
一是監獄制度及與之相關的囚繫制度。《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周禮·秋官·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說明桎梏是非常古老的械具,是木製的腳鐐、手銬,加鎖頸之械,合稱“三木”。富谷至認為“釱趾刑的確立是在景帝后的早些時候——景帝元年左右”。如果說是用鐵製的械具禁錮犯人之足,我也沒有異議。但若考慮到早期鐵製品是十分稀缺的金屬工具,主要用於製作兵器,就連農具都很少使用,就更別說是用於械具了。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到械具,一次是說自己“關木索”,另一次是說魏其侯竇嬰犯事被“關三木”。這說明武帝時還普遍使用木製械具。釱濫觴於秦之“杕”,是以木具束足。桎是將囚犯的雙足束縛,使之動彈不得。先秦鐵的產量有限,加之戰事頻繁,鐵器主要用於鑄造兵器。漢初經休養生息,輕徭薄賦,鑄劍為犁,生產恢復,鐵器大量用於農業生產。“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冶鐵業也隨之發展起來,有了多餘的鐵器,就可以用於囚徒之身。釱開始用鐵為之。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事下廷尉獄,輸作左校,太學生數千人詣闕上書為朱穆鳴冤,提出“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唐人李賢等注:“繫趾,謂釱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釱也。”沈家本稱:“自曹魏易以木械,而鉗與釱遂不復用矣。後世之枷,即古之鉗也。但鐵、木及大小、長短不同耳。”因此,如富谷至所言,景帝初出現鐵製的“釱”,也是合乎歷史事實的,但使用範圍有限。
二是死刑制度。程樹德認為,漢代死刑應該有三種:梟首、腰斬、棄市。晉張斐《律表》雲:死刑不過三。又云: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以漢、晉二律證之,知所謂死刑三者,即梟首、腰斬、棄市也。而作者認為:“秦律中的死刑完全可以歸為腰斬和棄市兩種。”這個觀點我認為是正確的,梟首隻是對斬首刑後的加刑,不能說是獨立的死刑刑種。《史記·秦始皇紀》:“盡得毐等,皆梟首,車裂以徇。《集解》:‘縣首於木上曰梟。’”沈家本按:“此車裂刑之梟首。”《漢書·刑法志》:“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梟其首,菹骨肉於市。”沈家本按:“此三族刑之梟首。”沈家本在此認為梟首是車裂、夷三族的附加刑。故無論是秦還是漢,梟首都不能說是死刑的一種。
秦漢的死刑執行方式主要就是腰斬和斬首(即棄市)兩種。但對特別的重大犯罪行為,“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這樣表述,可能更完整一些。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