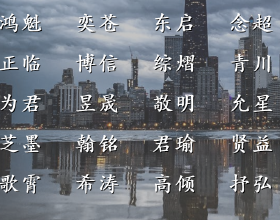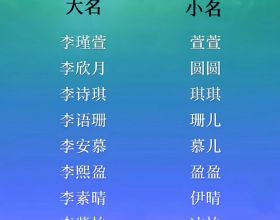媽媽講了一個道理:“農村的孩子,唯有讀書才有出路”
一輛核載十九人的中巴車在312國道的分差路口透過剎車做了短暫的停頓,汽笛聲還在轟隆隆響時,車門打開了,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少年,揹負著厚重的書包,手提黑色袋子緩緩的從客車堵塞的人群中擠了下來。售票員拉扯著嗓子:“小沙溪的下車啦。小沙溪的下車啦......”
少年抬了抬頭,望向頭頂下起顆粒狀小雪的天空,習慣性用手擋了擋眉宇,生怕天空中落下的雪粒砸中他中等高矮胖瘦的身材。他嘴裡嘟囔著:“該死的鬼天氣,早不下雪,晚不下雪,偏偏在我下車時下雪。”
平日裡中巴汽車是進村的,這幾天接連的下雪,泥濘的三四公里路堵住了汽車,人走在馬路上都得稍微留意,要不然你會在不經意之間摔一個狗吃屎。
從升學到縣裡高中,他很久沒有走這麼遠的路,何況還揹負著一大堆寒假複習資料和習題。實在沒有辦法,一邊走一邊休息,記不清走了多久,他從縣裡學校四點動身,到家時也是七八點。
媽媽提前為他準備了寒冬臘月的晚餐,這一刻,唯有大餐一頓才能解決他內心諸多的不快。他一邊烘烤著暖暖的煤火,一邊和家人坐在一起看著電視,不用說,你也能想象那是幸福美好的。
父母都是農村的,很少關心孟川墨的學習情況,反而是他回來,父母顯得憂心忡忡。今年下雪太早,爸爸沒有外出,很早就回家休息,下學期的學費仍然沒有著落,他回來多待一天也就離開學交學費的日子就近了一天。
其樂融融的氛圍下,媽媽始終還是沒有忍住:“川墨,下學期是幾時開學,今年的學費要交多少?”
孟川墨一邊看著電視,漫不經心的回答媽媽:“年初五就要回校補課,老師說,今年要交200元補課費,再加780元學費,大概要準備千把塊錢吧。”
媽媽打量一下他,然後望向爸爸:“嗯~...,那明天把家裡年豬殺了吧,趁著大雪未封路時,還可以到縣城賣個好價錢,半頭豬應該夠得上學費,至於生活費呢?我和你爸再想想辦法。”
“豬肝可以留點,其他就賣掉吧!”孟川墨一副喜歡吃豬肝的樣子。
媽媽會意地笑了笑:‘饞屁股。’(貴州農村方言,意思:饞貓)
孟川墨回了一個鬼臉,一心看著電視。
凌晨四五點,屋外吵得厲害,伴隨有煙火的氣味,狗的吠聲和豬的尖叫聲。媽媽把門敲了敲:“孟川墨,殺豬的師傅就要來了,鐵鍋裡的水還要加一點柴火才能燒開,你起來幫一下,我實在忙不過過來,要去準備殺豬飯。”
孟川墨起身下床,然後揉揉稀疏的睡眼,披了件看不到厚度的棉衣,佝僂著背藉著雪的反射光朝屋後的露天灶臺走去,寒風凜冽,冷得直打哆嗦。好在路不長,只見他蜷縮在灶臺的傳柴口,一邊往火堆裡傳柴,一邊倚著一旁的稻草睡意朦朧。
冬天的夜晚長是長了些,彷彿有一堆火的相伴,天空很快明朗了起來,殺豬的師父三下五除二就把一頭活生生的豬解剖成形狀大小規則的豬肉。
不大一會兒功夫,媽媽的殺豬菜也準備完好,香氣四溢,提前約好的親朋好友,三三兩兩,你催我邀,紛紛前來吃刨湯肉,滿院子裡一派祥和的景象。
熱鬧大概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早飯過後,爸爸隨著臘月趕集的隊伍去了縣城,孟川墨和媽媽在家裡收拾剩餘的豬肉,儘管這幾年過得很拮据,他們依然也準備點臘味。媽媽說,這才像農村裡的過年。
此時的小沙溪,別有一番精緻,從窗外望去,連綿起伏的山峰,被縈繞著的晨霧遮住下半身部分只冒出頭頂半個尖,近處的田園上被白雪皚皚的冬雪覆蓋著,不知是誰的功夫如此了得將這一片雪景剪下的平平整整,要不是一條河床蜿蜒穿梭在田野中,你幾乎以為這是裁縫店裡還未裁剪的一塊白色綢緞。
那條枯竭的河床上架著一座模糊了修建日期的石孔橋,兩個橋墩分割成三個橋孔孤零零的共同支撐著橋身,儘管匠家在修橋時刻意做了雕欄玉砌,索性的來說看上去也並不美觀,只是它毛骨悚然的叫蜈蚣橋,或多或少會讓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人有些不寒而慄,然而,小沙溪的人們進村出村時也對這個名字司空見慣。
約莫傍晚時分,爸爸又隨著趕集的隊伍回來,神采奕奕的,明顯在臉上寫著喜事兩字,見著人都笑得合不攏嘴,媽媽打趣的說:“你撿錢了?”
爸爸毫無遮掩:“撿錢了...,撿錢了...,豬肉賣了一個好價錢,幸虧前幾日沒有2500元整豬賣給豬販子。”
媽媽有些驚奇,但又平靜地說:“臘月的豬,價格是要好些”
爸爸:“你猜猜賣了多少錢?...”
媽媽:“猜不著...”
然後,爸爸比劃了一下雙手,接近2000元。
媽媽聽後並沒有表示出很高興,只是隨口一句:“川墨的生活費不用愁了。”
喜悅的氣氛瞬間凝固了,爸爸立刻收起了笑臉,附和著媽媽的話:“應該差得不多。”
“這些年,農村收入來源,實在太艱難,不是外出打工賺錢,就是在家裡靠一畝三分地苦苦支撐者一家人的開銷,遇到光景好的年份,年終可以過一個幸福的新年,運氣不好時,只能勒緊褲腰帶,東家借點,西家討點,再苦再累,也不耽誤孩子學習,不為啥,只盼有個前程,不再世世代代在大山裡種地。”媽媽接著說了一段這樣的話:
新年很快到來,農村裡的過年大抵相同,大年三十爆竹煙花,大年初一拜拜祖先,大年初二走走親戚,大年初三春分時節,各家各戶鐮刀鋤頭犁土,春耕播種,都忙著種下新年的第一粒種子。
而孟川墨新年第一粒種子則是考一個好一點的成績,文理分班時能選一個合適的班級。一大早,媽媽就催促他趕緊收拾好行李,趕村裡第一班車回縣城。昨晚他似乎又睡得晚了一些,媽媽從催促變成怒斥。
他躺在床上有氣無力的回答媽媽:“我定了鬧鐘,”
這可真是糟糕的一天,天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定的鬧鐘沒有在規定的時間內響起,之後的事越來越糟糕!
“起床!起床!昨晚我的話算是白說了,我希望你能趕在我後一班車去學校,先祝賀你能夠趕得上!”
睡夢中的孟川墨夢見一個陌生的女子,媽媽的大嗓門又驟然響起,掃興的攪了他美夢,媽媽尖銳的聲音足以擊碎窗戶上的玻璃,孟川墨想到前幾日窗上壞掉的玻璃一定是媽媽的聲音所為。他顧不上媽媽謾罵,全身心地投入盡力回憶起剛才的夢,想抓住夢裡女子緊緊摟住他一星半點的感覺...這種曼妙像雨後呼吸著新鮮空氣和泥土的氣息,清新又甘甜。孟川墨嘴角上揚,似有一股暖流瀰漫在心中微微盪漾開來,可是還沒等他在心理鎖住她的臉時,鬧鐘急促的想了起來,他嘆了口氣,努力的睜開眼,再次伸著懶腰,然後眯著眼看了一下鬧鐘,時間定格在七點半。
喔,天啊!鬧鐘又被定錯了,孟川墨在自己的小屋裡忙得團團轉,他趕緊把校服穿戴整齊。顧不上照鏡子,囫圇從床邊櫃子上撿了把木梳橫七豎八在頭頂上畫幾下,一邊下樓梯一邊往書包裡塞課本,提上幾件換洗的衣物,然後穿過客廳往村裡的中巴車站臺跑去。
小沙溪的清晨顯得格外寧靜,山間的雪壓得樹枝咯咯直響,孟川墨並不想聽大自然的奏樂,他躲進汽車裡塞上耳機(找同學借的MP3),沉靜在自己的世界,車窗外一排排優雅的景緻從身邊掠過,與他毫無關係,他也從不為之動容。從小沙溪到縣城的車程大約30分鐘,在乘客的上下車之間,汽車緩緩駛進縣城,孟川墨下車後直奔縣高中的出租屋。
年前放假孟川墨從學校的宿舍樓搬離,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宿舍關燈太早,同住的室友太多,他不適應這種群居式的生活,晚上也不能看書到深夜,用熱水也不方便,總之諸多的理由他不得不搬離學校宿舍。
那是一間離學校只有200米的當地人家的出租屋,大約10來個平方,房東需要50元/每月,因為有親戚關係,最後房東妥協到40元/每月租給孟川墨。房間雖說不大,但很規整,也很嶄新,像是剛簡單裝修出來的出租屋,屋內黃色的木紋地板孟川墨一眼就相中。房東只有一個條件,必須得愛乾淨,不允許在牆上塗抹任何畫跡,當然,是可以貼適當的可用於裝飾的明信片。
這樣的條件倒不像是房東要求的,孟川墨的秉性就是愛乾淨,他們不謀而合,房東愉快的把房間的鑰匙交給了孟川墨。
屋內房間靠窗戶的地方是一張用於學習寫做作業的簡陋書桌,配備了一把像是從學校順出來的寫著高二(9)班的椅子,還有一張木質結構約莫1.8米的大床。大的物件樣樣齊全,只需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可以入住。
床是靠裡屋的牆橫放著,正面是窗戶和窗戶下的書桌,房間的左右兩邊則為大面積的空白牆,左邊貼了一組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右邊貼的是香港女明星陳慧琳的半生照。看不出上一任出租的主人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房東也並沒有透露性別,只是略微的暗示這間房會給每一位入住的人帶來好運,住進這間房屋的還沒有考不上大學的。
孟川墨暗自竊喜,然後接著嘆了一口氣:“哎,想不到房東這張嘴如此厲害,天上的星星都能被她摘下來送給人。”
出租房的東南角是孟川墨就讀的龍崗中學,這所中學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明代大思想王陽明曾在龍場悟道,其潛心修學的地方是現龍崗中學的第一辦公樓,現在仍然有遺址。抗日戰爭時期,省城第一中學短暫遷移到龍崗中學,有過一段教學歷史,所以龍崗中學也被叫著龍崗第一中學,多半是為了懷念那段艱苦革命。
儘管這是一所山城裡面的普通中學,但能夠考上這所中學的也寥寥無幾,初中升學時,孟川墨班有四十幾人,而進入這所中學的不足5人。以他的成績進入重點班級輕輕鬆鬆,可是,總有一些陰差陽錯,考試的當晚他拉肚子了,早上起來為了減輕拉肚子的可能性他吃了幾粒瀉立停,在昏昏沉沉的狀態下考完了兩天的考試,也許這是原因,也也許這也是天意,中考成績公佈後,他未能進入重點班,這是一場失意,他希望在高二分班時能夠考入重點班級。
高一(11)班,這是一個富家子弟特別多的班級,多數同學父母都在政府單位,從穿著打扮上他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寒酸,他在班級裡只穿校服,不過這也是他能夠想到的他可以和這些富家子弟入流的唯一辦法。因為只有這樣,沒有人會懷疑他是因為沒有衣服穿而穿校服的。更何況學校有明文規定在校最好是穿校服。
和其他同學相比,他沒有什麼可以拿得出手的,他只能在學習成績上比別人更加拼搏。只有學習成績好了,自己穿得再破舊別人也不會注意到,因為好成績的光環足以掩蓋一切。
事實證明,他做到了,在上學期的寒假期末考試中,他考出了班裡第一名的好成績,也成為高一年級1000多名學生中少數進入前30名的學生。這樣的成績沒有優越的獎勵,大概就是一張獎狀,一支鋼筆,以及學習用的筆記本,學校會在全年級舉行一次頒獎典禮。
還記得領獎的那一天,孟川墨第一次站在全年級接近3000人參與的主席臺上,他顯得有些拘謹,緊張的不僅僅是要面對如此眾多的同學,而是他穿了一雙右腳後跟已經壞了一個洞的白球鞋。他高高的站在領獎人群的最中央,他不敢雙腳併攏直立的站著,為了不讓自己壞了的白球鞋暴露在同學們的眼前,他稍微把右腳分開,做出體育課上稍息的姿勢。這樣一來,左腳的側邊腳心正好擋住他右腳的腳後跟,有驚無險地避免了這場尷尬。
頒獎後的第六週,高一年級開始著手準備文理分科。毫無疑問,他會選擇理科,一位叫葉盼玲的要好同學,建議他選擇文科,還特意為他準備了文科分班資料表。但孟川墨拒絕了,在這所中學,18個高一班級中,升入高二時,只設4個文科班,其中兩個是重點班級,兩個為平行班,也就是說,剩餘的14個班級都為理科班,但14個理科班級中只會有4個重點班,剩餘的都是平行班,他想奮鬥一把,說不定能進入重點理科班。
文理分班後,班級裡兩級分化,上理科學科時,文科生矇頭大睡,上文科學科時,理科生寫數理化作業,總之,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只要在本學期結業考試時,結業學科考到60分就能拿到畢業證,他們都信心滿滿。
這樣的學習狀態持續了兩個月左右,真正的較量即將開始,為了高二分班都能夠進入好一點的班級,各科老師以及同學都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加幾分學習精力,當然也有些破罐子破摔的同學,他們作為群眾演員也參與了這場較量。
很快,一場決定文理分科的暑假考試到來,考試分為三天。第一天:語文和數學,第二天:化學和物理,第三天:英語。
其他科目他都考出了平常的基本水平,唯獨物理,他說不好,總有些題目解答得不如意。因此,在考試結束後,雖然如釋重負,可又憂心忡忡,有種不祥預感。整個暑假他都在猜測中度過,他渴望出現奇蹟。
南方的九月,已入中秋,村口那棵上百年的銀杏樹今年又是碩果累累,往年的樹葉都是十月開始變黃,今年來得早了些,滿地金黃色的扇形銀杏樹葉鋪滿厚厚一層,微風佛過,已成熟的果實隨著樹葉一起落向大地,它們也開始爭先恐後,誰能第一個到達地面。
孟川墨路過村口等中巴車時,刻意拾起幾片樹葉夾雜在複習資料中,當做標本也做書籤。他提前一天到達學校出租屋,路上遇到同班同學李萬明,才得知自己被分到到高二(9)班。這是一個晴天裡的霹靂,很遺憾,他再次落選,足足差了幾分,他鼓起勇氣去學校查了查自己的成績,其他學科都在正常範圍內,只有物理考了58分,儘管老師說今年學校整個物理學科都考得不怎樣,高一年級1000多名學生當中,達到及格的不足50人。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孟川墨最終還是沒有忍住,他歇斯底里的哭了一個下午,從學校出租屋跑到城郊的北門河畔,對著灣灣流淌的小河大聲吶喊:“他恨命運的不公,為什麼自己如此努力,換來的結局還是如此”,一個不想上學的念頭湧上心來。
臨近傍晚,孟川墨垂頭喪氣回到學校,在公用話亭給老家的媽媽打了一個電話,哭訴著告訴自己的決定。”
電話那頭媽媽感知到他的哭泣:“如果不上學,你還能做什麼?”
他不假思索地說:“只要不上學,做什麼都行。”
於是,他結束通話了電話回到出租屋,矇頭大睡,他很難接受這樣的事實,他想透過睡眠忘記這一切,此時此刻,他的天空是黑暗的,看不到任何的曙光和機會。
大概是晚上七八點鐘的樣子,天空飄起了細雨,雨聲滴答滴答的拍打著屋外的陽臺,細雨中,一位三十八九歲上下的女人撐著雨傘,慌慌張張爬上二樓出租屋,一隻手擦拭著額頭的汗水,一隻手敲響了孟川墨出租屋的門,一邊敲,一邊叫:“川墨,我是媽媽”。
媽媽敲了數次後,門緩緩的開了,一個蓬頭垢面的孟川墨站在媽媽的面前,他伸出雙手擁向媽媽,嚎啕大哭:“媽,我還是沒有考進重點班,我真的太累了,實在不想上學了。”
都說母子連心,媽媽能夠感受到孟川墨的傷心難過,她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淚:“如果真想去重點班,你舅舅這幾年有些關係,我託他找人看看能否把你送到重點班級。”
孟川墨繼續抽泣中......並沒有出聲.....
接著,媽媽說,她們那代人是沒有機會讀書的,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只認識一些簡單的漢字,她希望孟川墨能好好讀書,哪怕真如他說的那樣考不上大學,讀個簡單一點的學校,也能謀個城裡的事情做,不用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像她一樣做一輩子大字不識的農民。
這是多麼樸實無華的道理,很難想象一個農村婦女,而且是一個沒有文化知識的農村婦女,居然能說出這麼有哲理的話出來,他無力反駁媽媽,就算不為自己將來讀書,也應該為媽媽讀書。
那個夜晚,媽媽陪伴孟川墨一宿,他們聊到了很晚,那也是第一次,媽媽和孟川墨聊她自己小時候,聊她那個年代生活的各種艱辛。也就是那天晚上,媽媽教會了孟川墨一個道理:“農村的孩子,唯有讀書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