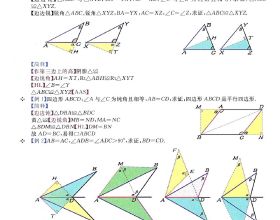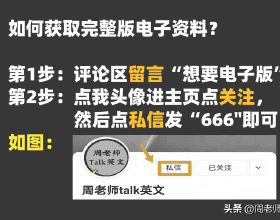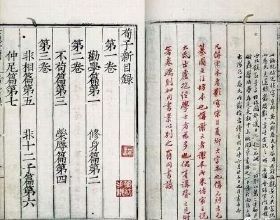小時候整個村莊,沉浸於節日的喜慶中,連空氣裡都飄滿了過年的味道。無論窮富,家家戶戶都準備了不少鞭炮。也有極個別的不買炮,像村西頭二兔子家,別人放炮,他不知從哪兒弄來兩三枚雷管,聲響特別震人。
小孩子是眼巴巴地盼天黑。後來,天就黑了。也沒見誰招呼誰,鞭炮就在村裡噼裡啪啦噼裡啪啦地響起來了,升起的黑煙猶如妖精,搖擺著,扭曲著,慢慢消失了。正在這時候,鱉孫二兔子在家放了個雷管,聲音驚天地泣鬼神。隔牆的老寡婦望著清冽的夜空,捂著胸口直嚷嚷,我的娘嘞,咋能響啊!
村子裡的親朋好友,三三兩兩相聚起來,熱鬧鬧炒幾個菜,吆五喝六地喝起酒來。酒場一般不長,酒盅一收,桌子一擦,便開始賭起錢來。
在誰家賭錢,那家的小孩立馬身價倍增,說起話來和往常不一樣。一兩個鐘頭下來,他就可以賺得兩三毛的“打頭錢”。於是,他把手一揮,我們就像簇擁著國王一樣,伴他來到村子裡的小賣鋪,他會很大方地買幾盒電炮。就他甩的多,年齡大點的也會得到一些,我年齡小,自然得不到他的重用。後來,他把一個甩了幾下都沒甩響的小炮給了我,我緊緊地攥在手心裡,心裡說不出的受用。
回來的路上,聽見當街咋乎乎的,我們立馬向那裡湧去。當街,已經圍觀了一群人。原來是一個叫翠花的潑辣娘們,為一點瑣事罵大街。罵的久了,她老大伯哥從酒場回來,剛好路過,有點看不下去了,就勸她回去。於是,這女人清了清嗓子,大聲說:“恁聽著,要不是俺大伯哥喊俺回去睡覺,俺就罵到天明。”眾人一聽,哈哈大笑。她大伯哥氣得二話沒說,扭頭就走。當年,村子裡的人,還有走親戚的,都在傳這個笑話,說時眼淚禁不住都流出來了。
回到家的時候,堂姐在我家串門。她剛訂罷親,穿一身新衣服,頭髮黃黃的,人前晃來晃去。我故意問她,新衣服可是婆家送來的。她頓時來了精神,連聲說是,邊說邊擼起衣袖,得意地說,這上海牌女式小坤錶,也是他家送的。站了一會兒,她心滿意足地離去,只是沒回家,不知又到誰家顯擺去了……
很多人從穿上新衣服的那一天起,便沒有脫下,一連得穿十幾天不換洗。很多人的領口和袖口都油光水滑,亦不在意。其實,那時的年,確實像個年啊。